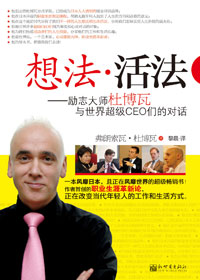活法-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着,我可以给你看,不知道可不可以上你们的镜头。上个星期刚生了一个小姑娘,我们生活得非常幸福。你知道,我对中国人的一些风俗习惯,越来越了解,我指的是大陆的中国人。她不断地告诉我,各地的中国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西方人老觉得中国人都一样,不管他们来自香港或是别的什么地方,而我的妻子不断地告诉我说,不是这样的。大陆中国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大陆中国人更坚强。
王 志:她到底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默多克:我觉得她扩大了我对人生的理解,我这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度过的,那是一个说英语的,西方的世界。而现在我则有了第一手感受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一个更大的、更古老的世界。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经历。她使我保持我思想的敏锐,保持年轻,每一天,这都是一个挑战。
王 志:那我很想知道,您是因为选择了一位中国妻子,才让你的中国战略,在整个计划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还是因为这个计划本身重要,才让你选择了一位中国妻子。
默多克:中国妻子在这个战略之后,而不是在这儿之前。我不断地到中国来访问,见到她,认识她,爱上她,然后和她结婚,过起了新的生活。
王 志:感情上的选择,会影响到生意上的取向吗?
默多克: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好的顾问吧,她在美国受过教育,上过美国的商学院,她处理很多问题,处理生意上的问题,有一种中国的风格,这一切现在正在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王 志:那她到底什么吸引你呢?从我们通常人的观念来看,你们俩的年龄差距,你们俩的文化背景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默多克:我的文化和我的年龄可能没什么关系,当然我妻子和我年龄比较不同,这是事实。我很幸运能够讨到这么一个年轻的妻子。
王 志:那回过头来说,您觉得郑文迪女士喜欢您什么,您对她的魅力在什么地方?
默多克:这个问题你问她吧。我觉得我也拓展了她的生活空间吧。
王 志:我从有关的材料中间看到,您原来的家庭生活,也是很美满的,而且您有很多很优秀的子女,那么这样的新感情选择,对你来说很困难吗?还是很容易?
默多克:生活中,所有大的选择可能都会是困难的,这是我走出新的一步,我很幸运,就是说我的孩子都很好,我对他们非常自豪。
邓文迪和两个小女儿的到来给默多克的生活注入了更多的年轻因素,他每天坚持锻炼,以保持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王 志:在我的想像中间,我相信默多克先生,你应该比我们有更大的工作压力,那你怎么舒缓你这种压力呢?
默多克:我有我的假期,但假期不长,只是正常的假期,五天,长周末,一个星期,离开正常的工作场所,最好是不要带电话,然后看一些书,可是这个通常不太可能。
王 志:保持活力最重要的奥妙是什么呢?对于你来讲?
默多克:我觉得是精神上要不断地挑战自己,要投入地做你的事情,对于身体来说,要注意经常锻炼,有些东西你得考虑到,就是说这个身体由自然退化的过程,你必须得接受。不是说什么非要工作多少时间,应该锻炼,应该保养身体。
王 志:在大家印象中,默多克先生是非常有钱,那我们很感兴趣,你准备怎么花这些钱呢,或者说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跟我们区别很大吗?
默多克:并不是跟别人有那么大的不同,没有那么多豪华的东西。当然我在纽约有一个很好的公寓,它处在纽约的艺术家区,不是那么特别豪华,还有一个我妻子刚刚找到的乡间周末的度假屋,我和我妻子周末带孩子到那边,洛杉矶还有一栋房子,因为我们的电影事业在那边,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农场,靠近堪培拉,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40年了,一直是我的农场,但是我很少去,一年去几天吧。我孩子喜欢去,那是一个我们家庭聚会的地方,也不是那么豪华。很好的老的石头房子,很普通。
我不相信做一个富人就应该张扬啊,住很大的房子啊,或者豪华游艇什么的,那套东西我不太相信,我觉得他对孩子们的成长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其他的家庭,有这种豪华的生活,我这样说可能不应该,但是很多,看见很多别人的孩子在这种生活中,没有能够很好地成长,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也走上那样一条路。
王 志:那您有几个儿子,我们很感兴趣,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新闻集团会不会像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家族企业那样,分成很多小的公司呢?
默多克:我的儿子们,我的女儿们,我的两个小女儿,他们会自己决定谁来当头。但是这个公司足够大,可以让所有的,愿意奉献的人,可以在这个公司中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在全球范围建立起庞大媒体王国的默多克今年已是72岁,在似乎永无休止的进军征途上,默多克最不能回避的就是自己逐渐老迈的年龄,但是,直到现在,“退休”两个字好像还没有出现在他的词典中。
txt小说上传分享
鲁伯特·默多克:中国引力(6)
王 志:你会选择某一个时刻退休吗?
默多克:不会的,我不想退休,如果我的思维能力不行了的话,我孩子会对我说,该退休了,老婆会对我说,该退休了,只要我的活力,我的这个思维能力,没有退化,我将继续做我的工作,我的想法是,还要工作很多年,然后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倒下,死去。英国人说穿着你的靴子倒下,这是一个英国的说法。
王 志:有人评价您说,有一颗永远也不停止的扩张野心,你这种野心源自何处呢?换句话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你不断地扩张?
默多克:是这样的,我们不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公司,但是人的视野应该不断地扩大,所有的员工,都应该能够有这样一种体验,这个对于他们的工作精神,工作热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是拥有这样一种野心生活的一个健康的表现。
王 志:你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或者你构想中间的媒体王国到底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
默多克:和我们这个企业目前的状况没有什么区别吧,把我们现在所有的事业做得更好,走得更好,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投入更多的创造力,电视或者是其他的创作,比如说写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永远可以做得更好,每一天对于昨天都是一个挑战。
王 志:让你来评价一下你自己走过的70年。你会对我们说什么?
默多克:我觉得我创造了一个有价值的实体,它还有可以改善之处,我相信在我之后,人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还想再活下去,活一些年,把我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默多克和我的英语强迫症
2003年11月1日清晨5点,天色开始渐渐发亮,出租车在长安街上疾驶,车后座上瘫着昏昏欲睡的我。司机大概是太寂寞了,不住嘴儿地说话,而我的反应总是慢半拍,接不上他的话茬。经过好多天的煎熬,这一刻让我有种大考结束之后的解放感,不愿再多想任何东西,只是脑子里有一些残存的意识,才做好的节目会不会有问题?尤其是字幕,可别让那些懂英语的人笑话!
这个老默,把我折磨成英语强迫症了。
开始准备默多克是在3月份,当时的背景是老默要在5月初访华。王志把题给我的时候,说这可是个大人物,我明白这个人物的分量,当时便开始兴奋。不过,去了趟新闻集团北京办事处之后,我的兴奋便开始增加了一些惶恐,对方时不时蹦出的外语单词让我心里总是咯噔一下,暗中翻译一下才能接着说。而我说话则是没有丁点洋味儿,就连鲁伯特、拉克伦、詹姆斯之类的人名都能让我说得是字正腔圆,甚至还让新闻集团那位媒体关系总监听出了我口音里的河南味儿,跟我攀上了老乡。于是,私下里开始打鼓,采访默多克,我那点“poor English”能行吗?
其实,我的英语底子原本还算可以,大二时候就把六级给过了。不过,毕业之后,从事的工作跟国际总搭不上界,于是,便把学校那点英语底子一点一点给扔了,时不时心里有些危机意识,告诫自己是不是要好好学一把英语,也让自己与时俱进一下,然而这种想法往往像上学时自己制定的晨练计划,被搁置的几率近乎百分之百,偶尔听一下英语,感觉比催眠曲都有催眠效果,暗地里向自己妥协:没办法,实在太忙了!
就这样遭遇了默多克,妥协的结果是自己尴尬。
大抵是因为“非典”,默多克原本安排在5月的访华被推迟到了10月。不过,我跟新闻集团那边的联系倒是一直没断,按照我的要求,新闻集团给我快递了一大堆关于默多克的资料,不过,一大半都是英语的。那边的小姑娘问:用给你翻译吗?我硬着头皮回答:不用——英语不怎么样,虚荣心还是有的。不过,可惜了快递费和小姑娘的劳动,那些英语资料我大多没看——网上关于默多克的中文网页多着呢,不用查字典,每个字我都认识!
默多克的空镜不可能让我们飞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去拍,只能让新闻集团北京办事处去找了。那天,新闻集团中国区的常务副总裁把一盘带子交给我,那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制作的一期节目《默多克家族》,副总裁专门告诫说:老外很注重copyright(版权)的,你们用之前最好给ABC的制作人发一封E…mail;或者打一个电话征得他们的同意。
我心里又一次打鼓,用英语给人发信,用英语和人通电话,这我哪能成啊?
当时因为手里还在忙着其他节目,于是我就找来组里的“海归派”吴宁说,我太忙,你英语好,干脆默多克你做算了。
“海归派”很爽快地答应了,这让我一下子心里放松好多。不过,刚想把这事给王志说,王志倒是给我打来了电话,说第二天中午要去新闻集团,要我抓紧做一个采访提纲,跟人家沟通一下。我连连称是,不好意思再做推辞。
老默终于来了,采访时,因为有了同声传译,我能清楚地知道他在说什么,这让我对节目有了底儿。然而,我在要求补拍他随身带的照片以及请他签名的时候,都不知该怎样措辞,虽然有翻译在旁边,但我仍然感觉自己非常尴尬——准备了半年的时间,上阵时却连一句“Hello!〃或者〃How are you!〃竟然都难以轻松说出!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鲁伯特·默多克:中国引力(7)
其实,我仅剩下的那点英语底子,也是仅仅停留在纸上的,现在想来,这笔账应该算在中国的英语教育方式身上。
因为自己的不自信,采访结束的当天,我就把那位做同传的翻译请到了办公室,让他听着带子把采访再精确地翻译一遍。那位翻译不停地夸我,说我做事太认真了。我当时心想,我要是像你这水平,何必这么认真地一遍遍问你?
在对默多克的编辑过程中,这位72岁的老人让我狠狠地练了一把英语听力。好在采访时间不长,总共才一个小时多一点,不至于有太多的剪辑点,要不然我会崩溃。
需要特别鸣谢的是我们组的实习生欧阳询,欧阳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曾经教过本科生一年的英语。上字幕的时候,她一直帮我盯到了早晨4点,小姑娘从来没有熬过这么晚,困得快不行了,还一直甜甜地叫我“张老师”,叫得我颇有些惭愧,在英语方面,我本应该叫她老师的。
节目播出的当晚,《中国周刊》的小才女杨梅给我发来短信说,短片剪得很眩,翻译有些地方欠妥。得,还是让人看出问题来了,那可是新闻集团请的很贵的翻译呀!看来真的是学无止境,当时就又一次下了学英语的决心。
可是第二天一醒来就把学英语的事给忘了。说句给自己开脱的话,我的10月份实在太累了,从杨利伟到默多克一连做了三期节目,这让我分外珍惜这几天没有节目的时间,倒是《空谈》的约稿又让我想起了英语带给我的尴尬,知耻而后勇,抽空学习吧,这篇短文权当就是自己的一份决心书!
张士峰
。 想看书来
杨振宁:大师别传(1)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1945年留学美国;1957年和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年加入美国籍;2003年底回国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所长;2004年因提出《易经》对现代科学的影响备受质疑。
清华大学专家公寓B栋,是杨振宁先生在北京的居所,从2003年11月回到国内,杨先生就一直住在这里,并把这里取名为“归根居”。回归祖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位80多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屡屡制造新闻而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王 志:我想从你回国的这件事情开始说。回来定居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杨振宁:我虽然在美国住了50多年,可是就像我的一个朋友所讲的,杨振宁你血管里所流的是你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我想这个话讲得是很对的。那么后来有更迫切的原因,因为本来的太太杜致礼从1996年、1997年开始身体不好,那么2001年我们回到清华。那个期间她去了301医院看病,我们觉得她的身体在国内比在国外照顾得更周到一些。当时我们就有意思搬回来定居在清华。所以2001年住了4个多月以后,我们又回到美国,就预备整理东西整个搬来了。然而她在2003年10月过去了,过了两个月,就是在年底,我就搬回来了。
王 志:那是为了完成太太的一个夙愿?
杨振宁:还有很重要的是因为清华大学当时的校长王大中在1996年、1997年就跟我谈了,说是希望我回来,帮助清华建立一个高等研究中心。那么我因为小时候是在清华园长大的,我对于中国的科技教育发展的前途是非常感兴趣,也有很大信心。所以王校长跟我这样讲了以后,我当然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