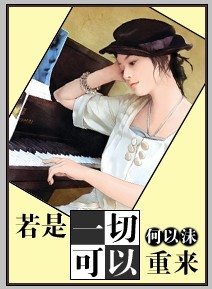优雅是一种选择-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认为职场着装即使不一定就是职业套装,也一定是在你个人的衣橱中你最能够穿着上班,而同时最有助于你的职业形象和职业能力形成的着装。
个人认为就是裁剪最为简单、装饰感最少、暴露最少的着装。
尽管我对许多人将职业着装与生活着装混为一谈表示理解,但我仍建议,如果在意自己的职业发展,请相信,坚持准确的职业着装,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定是有益的。
对于一个标准的职业女性,我认为进行上述衣服配置其实我发现,除去职业装配置以外,生活装的配置需要已经非常有限了,我们只需要购买一些休闲牛仔衣裤(两三件/条),T恤衫(三四件),毛衣(三四件),半截及膝小裙子(两条),短款薄厚外衣(各一件),如果再添置两条用于夜晚社交的裙子,真的就足够了。(前卫职业除外)是理性而实事求是的,覆盖了所有功能需要,如果再多,自己可以仔细甄别,一定就是同一功能的不断重复。
而上面我们已经提到,针对同一功能的衣服,我们最好坚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样我们不仅节约了开支,也不必为衣橱不够用而发愁了。
有人会问,同功能的衣服数量不多,会不会因为重复穿着而缺乏新鲜感呢。
我们仅以牛仔裤配 T恤衫为例,三四件 T恤与两条牛仔裤相配,我们已经可以满足四天的短假期需要,如果再有一条裙子作调剂,我们就可以有很漂亮很舒适的假期。如果假期再长,将这些衣服轮回穿一遍一点也不单调呀,说不定在别人眼里,你已经非常亮丽,非常漂亮了。
我之所以现在去商场的次数越来越少,是因为每年我都会在季节转换时仔细清理自己的衣橱。我发现,由于我购买衣服越来越符合自身的实际功能和气质需要,我的衣服的耐穿时间越来越长,所以我不用经常去商场。我有一个特点,我是一个无事绝不闲逛商场的人,要去一定也是想好了要买什么功能的东西,直接去该去的地方。
我的大衣、风衣、职业装,因为购买时坚持好品质,选择合适的款型(这些基本储备绝不能跟潮流走,谁跟谁浪费),这些衣服我有的已经穿了十多年,我只需要适时与不同的衬衫配饰搭配,就永远不会有过时的印象。经常有人夸奖我的某一个装扮好看,我便告诉他们,这件衣服我已经穿了七八年了,对方的表情通常都是不可思议。
这就是永远买适合自己东西的好处,因为适合,在自己身上永远漂亮。
第二,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双鞋子。
还是把鞋子按功能来划分吧。
与职业装配套的鞋子:这类鞋子我的主张就是不妨多买几双黑色船鞋,好用。同一黑色要有不同鞋跟高度和款型差异,以适合不同的裤装与裙装需要。此外,配备银色或米色、棕色及灰色船鞋各一双,够用了。
与生活装搭配的鞋子:这一部分鞋子较为自由,以舒适为第一考虑。我喜欢买牛筋底与坡跟便鞋,非常舒适,夏天的坡跟鞋能很好地与裙装搭配;另外我还买有一双米色的芭蕾鞋,穿这种鞋就是为了把自己彻底放下来。这类生活装鞋子只要分别买深浅两类颜色即可,轻易不买花花鞋,十分难搭配,除非自己想诚心玩儿一下,可以额外添置,但我不主张将它作为基本配置来购买。
靴子的用处:无论上班还是日常,靴子都是用得着的,我的主张也是深浅各一双,个子不高的人,不要买半筒靴,愈发地显得个子矮小和腿短了。
第三,我们需要多少包包。
我知道许多人有恋包癖,如同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小朋友,她买包不是为了实用,而仅仅是喜欢包包。这种爱好我不是太能理解,但确实有许多人就是无条件地爱包。
我为上班配备了黑、棕、白三色包包,造型都以上班为实际需要,方正简洁,做工上好。这三个包已经可以应对我上班的全部需要。
与生活装相配套的包包我配备了三个,两个颜色不同的属万能搭配的手提包,外出吃饭购物都可以,另一个就是旅行郊游时挎在身上的斜挎包,我选择了一个颜色鲜艳的花花包,非常漂亮。
再就是与晚装搭配的小手包,黑色与银色各一个。够了。
可以配备几条漂亮丝巾,一深一浅两条羊毛或羊绒长围巾,一深一浅两双皮手套,够了。
看到这里,是否许多人都发现,自己的配置远比我写下来的这些要多得多,一定是的。事实上,我们远不需要那么多,多的部分一定都在闲置,或者利用率极低。不利用就是最大的浪费,我们为什么要浪费呢?
最后的总结:无论是衣服、鞋子,还是包包围巾等,我们只要分清功能,依功能按实际需要配置,绝不多余,绝不闲置,坚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体面,优雅,漂亮,节俭,成为在家庭内外均受欢迎的衣着俏佳人。
序言
我主张女人尽量活得诗意些,少些物质和名利的追求,让自己更多沉浸于喜悦的心灵感受中。心灵的喜悦才是美丽的真正秘方。
对我而言,我为自然变换欢喜,为生命健康欢喜,为音乐悲喜欢喜,为读书养心欢喜,为独处静思欢喜,为餐灯下家人的团聚欢喜……为这一切的欢喜而欢喜。……我的一天是从早晨侍弄阳台上的花草开始的。起床的时间可早可晚,视头天夜里的睡眠而定,再晚也不过八点多。
严格地说,我只养了些草,而且都是些好养的平凡贱草,比如吊兰一类。我对花的兴趣一般,一是花开花谢总有个间歇的时候,没了花,花桩子也变得难看了;二来养花需要更多的仔细,那份仔细是我付不起的;再则,除了百合,偶尔还有玫瑰,让我真心喜欢的花类确实不多,不喜欢自然更懒得养了。
养草却是另一回事。我尤其喜欢那满眼蔓延的绿。从绿萝、白雪公主、滴水观音,到吊兰、万年青、凤尾竹,我家的整个阳台和客厅都被它们占满,一年到头绿着,生机着,从不懈怠。养草似乎可以粗心些,我有一盆吊兰,放在原先住处的阳台上,许久不管,偶尔想起只给点水,吊兰居然依旧生气,开着纤秀的小花,分出许多的枝条。搬来新居后,我试着把那枝条上长出的兰剪下来分栽,也只是给点水,分栽的兰居然活了,活到现在又分出了许多盆,家里的阳台、条案上摆得到处都是。条案上的吊兰分出枝条的时候格外风雅,枝条垂吊着,摇摆着,长长短短,显得有韵致极了。也许是把草养活了,现在看见新鲜的绿叶类植物我便想买,屋里已经无处可摆,这才想起凡事还是有节制的好。
阳台上除了绿草,还有一把沙发椅,给草们浇完水,除掉杂叶等,我便坐在沙发椅上晒太阳。秋冬的太阳正好切合了我起床的节奏,在我侍弄完绿草,太阳刚好走到我的阳台上。晒太阳的时候,一杯上好的绿茶必不可少,有时早餐就在阳台上吃,吃完了继续喝茶。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和晚上,上午的光阴对我最为紧要,没有特别的要紧事,上午是轻易不出门的。如果阳光不是很强烈,上午我通常就在阳台上看书,那时的心境一般很静,绿草们围绕着我,空气也被它们湿润着,家里也是安静的,几个小时下来,只觉得惬意。
上面这段文字不记得何时写的了,现在看来,当时竟有一种诗一般的心境。
我想那种记载,是为了留给将来的自己看的,使现在的我一想到那时的我,便能够历历再现。
我多少算个浪漫的人,我的浪漫在于我可以舍弃许多现实的诱惑与吸引,而选择一种我看来最为紧要的相对自由的日子。还是在青年时期,便记住了一个意思:心为形役。心想一旦心为形役,缺乏心灵的自由,活着便失去了生气和意义。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之一,便是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摆脱外在的羁绊。为了达成这个心愿,有些取舍是必然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又是相对超脱的。
超脱的代价,是自己与现实的相对疏离。这种疏离不一定人人都喜欢、都能承受,但对我却是个比较舒服的状态:活在现实中,却又随时可以离去。这里面并没有虚无和厌世的成分,相反我是那样地热爱生活,我只是在寻找一种让自己觉得舒坦的方式。
在我的表述中,多处用到了“相对”一词,说明我是一个了解自己的人,我确实做不到纯粹,我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曾经同一位著名的心理学教授座谈,他谈到在心理学意义上,人的成功就是人最自然的本性得以实现和满足。换句话说,人的最好状态便是遵从人的喜欢,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感觉愉快就是最大的成功。名画家范曾先生说过八个字,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一息尚存,从吾所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基本还是遂了自己的心愿活着的。
我主张女人尽量活得诗意些,少些物质和名利的追求,让自己更多沉浸于喜悦的心灵感受中。心灵的喜悦才是美丽的真正秘方。
对我而言,我为自然变换欢喜,为生命健康欢喜,为音乐悲喜欢喜,为读书养心欢喜,为独处静思欢喜,为餐灯下家人的团聚欢喜……为这一切的欢喜而欢喜。
行者无疆——行走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1)
书架上有一摞书是与旅游相关的,多是希望去的和已经去过的一些地方的人文历史。比如西藏,比如新疆,比如法国、以色列等。
许多人都希望此生不工作,却捡得了一笔意外的财富,让自己能够全世界行走。我也一样。
直到现在,我去过的地方仍不算多。有些地方去过,也只是蜻蜓点水。但是毕竟,看过一眼与完全没有看过不是一回事,对那些兴趣不高的地方,看一眼也许就可以了。
但是,真的还是走得太少。
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年的假期大多无偿地交还给台里,发了狠想休假的时候,都用来旅行了。
我一直留恋在法、德等国家开车转悠的日子。那是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久,我第一次体会到,换一个环境,人真的可以在另一个时空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心境甚至思维,而将自己的过去全部遗忘。那时我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我渴望从一个职场女性的身份,转换成另一个无所事事的看客。虽然异想天开,好比画饼充饥,但哪怕只是暂时的转换和遗忘,于心境都是极好的调剂。
除了那些人所共知的城市和名胜,更让我流连难忘的,是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农舍里度过的一周。每天早晨走上阳台,远处是皑皑的雪峰,近处是起伏有致,仿佛绒毯一般铺展开的草场。几头牛散落着低头吃草,脖颈下的牛铃远近高低地彼此呼应着,像是空谷间悠扬的乐声。那时租住在一幢三层别墅式农舍的三楼,一二层分别住着一位年老的农妇、一位年龄稍小的女房客,和老妇的儿子、儿媳。每天早晨天光刚亮,就听见小夫妻发动汽车和车轮碾过门前的卵石路面逐渐远去的声音。等我们稍晚出门时经过一楼客厅,总能看到老妇和她的女房客坐在沙发上吸烟、喝茶、闲谈。那一种平静、规律、自然的生活,和我们已经习惯的现代化都市生活,实在是天差地别。
从那以后我一直耿耿于怀,想象着每年都有一段日子属于另一个时空。后来幸运地做了一个绕着新疆走一圈的节目,走了一万六千公里,愈发把心走野了。
比如此时,阳春三月,我想象着江南的烟花细柳,池塘中悠然自在的水族家禽,漫山遍野望不过来的满眼翠绿,还有春天里随心播种的点点希望……我又想走了。
旅行,就是在一个于己完全无关的世界里,寻找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对比与联系。这种寻找并非有意,而是不知不觉,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对自我的体察与丰富,从而体验有别于习惯与日常的另一种人生。乐于这种体验的人,是对人生有更多好奇与想象的人,是能够因为精神体验而淡泊物质与利益诱惑的人。
人在旅途中会变得格外超脱、格外包容甚至善良,因为一切都与己无碍、与己无关;人在旅途中也会变得格外聪明、格外敏锐,因为一切都需要自己重新打开视界。为了这聪明善良的另一个我,以及这个我带给本我的惊喜与收获,多少人就这样着了迷似的不断上路,不断行走。
在这样的人群中,有人把行走当成了生命的一种形式,似乎生来就是为了行走;有人把行走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穿插,让行走成为间歇性的生活需要;有人对行走没有切实的需要,只是偶尔向别处看看,看到不同,便发出一声惊叹……想了想,我大概属于第二种,没有行走者超脱,却比惊讶者执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行者无疆——行走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2)
只要离开自己日常生活的小圈子,任何地方都是想去和可以去的。虽然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人总希望去些更远的地方,若世上真有那种连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地方,那便是最好的去处。不过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我看重体验,只要换个地方,与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我就高兴。
记得某年同先生一起在绍兴呆了两日,在那个空气中都浸满了黄酒味儿的小城,我俩终日在街头走走停停,走累了就寻一处酒馆坐下,然后喝酒,然后微醺而归。
碰巧,那两日正赶上越剧一百周年,去了才知道,印象中柔媚雅致的越剧,发祥地竟然是绍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无意中闯入一个民间剧种的老家,仿佛无意间自己也在寻根问祖。因为自小就喜欢看越剧听越剧,那种意外的惊喜让我兴奋异常。而更让我惊喜的是越剧名角茅威涛正在当地领衔主演《梁祝》,而且仅剩最后一场。实在是无巧不成书,平素想看名角演戏,除了演出机会,还得时间合适,在北京演出的许多好戏,大都也只是心里想着,看成的实在不多,这次是无论如何也要看的。费力找来了票,还是很好的票,坐在剧场靠前的正中央,等着名角登场。
一个名角常常救活一个剧种。我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