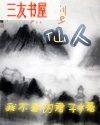上流社会知识竞赛-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瓶红酒,各自表述(2)
鉴赏师( 已经喝过、品过、吐过 ):“唔,有股地毯的味道。”
葡萄种植园主( 发怒了 ):“你是什么意思,‘地毯的味道’。你竟然敢这样说话!”
鉴赏师( 努力想要解释 ):“不是一般的地毯,我的朋友;那是一块非常古老,非常特别的地毯。”
吾等好色如好德,好酒兼好面子之徒纵使这辈子肯定干不成职业鉴赏师这行,但是饮酒之后必要的口头表达能力依然十分必要,其重要性可与饮酒之前对钱包支付能力所做的自我评估相提并论,虽然后者通常并不发出声来——话说在《 一年好时光 》里上过那堂品酒课的伦敦佬查利,回到诺丁山某餐馆,开了一瓶1982年产的Leoville Barton( 380磅 ),便开始教训他的初哥朋友来:“麦克斯啜了一小口,学着查利的样子将酒含在嘴里品味了片刻:‘没话说,没话说!’查利眼珠子翻到了天花板上,‘太粗糙了,朋友。你可不能这样来描述一件艺术品。你必须学一点专业的术语,掌握评论美酒的词汇。’”
查利建议的专业词汇,有“褪色的郁金香”,“沉思中的贝多芬”以及“最繁复恢弘的哥特式建筑”。照此标准,以下对话记录,几乎就可以认定为糙话了:“‘马高堡’( CHATEAU MARGAUX )姜文也很欣赏:‘这酒比一般的红酒浓厚些,要醇香些,喝起来格外顺畅。’又是一声赞叹:‘不愧是法国国宝,越饮越好饮,越饮越想饮。’”
上文引自旅法香港导演张潜先生的葡萄酒专栏《 酒色现场 》。张导在文中对葡萄酒的评价文字常有过人之处。有些时候,张导引用的他人评语却更有惊人之处。除了“越饮越好饮,越饮越想饮”之外,我还在《 酒色现场 》读到过吴镇宇对“飞耶渣堡”( CHATEAU FIEUZAL )的评语:“你没有介绍错,这酒口感很好,很顺畅。再来一支‘飞耶渣堡’吧。”
“浓厚”、“醇香”以及“顺畅”数语,甚是耳熟,更应该出自吃涮羊肉喝二锅头的现场。而在这个“二锅头现场”里,“越饮越好饮,越饮越想饮”和“再来一支”听着也就格外地入耳,不由得令人有大呼“好酒!”的冲动,接下来,顺理成章地,可不就是“干杯”了吗?
一、七碗说不得也
由于葡萄酒的话语权并不像高粱酒或绍兴酒那样牢牢掌握在汉语民族之手,故对于葡萄酒美味的口头表达( 甚至部分美味本身 ),肯定有相当部分 lost in translation 了。同样道理,一个喝着中国茶的法国人或许能够体会到什么是“喉吻润、发轻汗”,却永远也难以理解并且说不出“破孤闷、肌骨轻”这样的话来。不是“七碗吃不得也”,而是“七碗说不得也”。当然,这一切并不表明该法国人就不会喝中国茶,只是他无法令我们相信这件事情而已。
那么,为了我们的钱包和我们的面子,“汉化”可不可行?理论上,基于我们在历史上曾有过无数像把 Science 和 Democracy 汉化为“赛先生”和“德先生”那样的得手前科,那么,“黄鼠狼”以及“兔子肚皮”之类虽属冷门,毕竟这两种畜生不独只生在法国。就算是中国没有的松露之味,亦不妨取代以云南或东北所产的各种菌类。同理,从葡萄酒里品出来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为什么就不可以置换为《 黄河协奏曲 》、《 嘎达梅林 》甚至女子十二乐坊的任何一支曲子呢? 。。
一瓶红酒,各自表述(3)
实践上,汉化工作也一直有人在努力。例如,香港人就喜欢用瓶塞的“嘉应子味”来作为评判好酒的基本标准。我并不知道“嘉应子味”的法国术语对应为何,但是,把几块钱一包的嘉应子与数百上千元一瓶的葡萄酒相提并论,从情感到理智,似乎总有不能接受之处。
与其搞什么“嘉应子”这种令人不爽的飞机,我宁愿接受某中文葡萄酒网页上把因单宁在葡萄酒中作用而使喉间受到强烈刺激的感觉aigreur( 有“辛辣”之意 )汉化为“麻辣的”。当然,这个译名好就好在是全民吃辣的今天,要是时光倒退二十年,这种口感“麻辣的”葡萄酒大概也只有四川人甚至成都人才能心领神会。
由此看来,要对葡萄酒术语进行一如既往的汉化工作,是不能不“自带”一些“酒水”以及“口水”的。这件事与年初发生的“来一个,查一个”事件略有相似之处。几年前,《 中国青年报 》说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Thomas V。 Fuentes对该报记者表示:“对余振东这样的腐败官员,我们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消息一见报,Fuentes立即澄清:“联邦调查局只有在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才会对逃往美国、涉嫌腐败的中国官员进行调查,确定他们在中国的犯罪行为,把他们遣返回中国。”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我都觉得“来一个,查一个”很可能就是“嘉应子”或者“麻辣”的翻版。就语义学而言,与其说是来了以后被“汉化”,不如说是外逃之后被“遣返”。
无论管不管用,爱喝葡萄酒并且更爱让别人相信他们“会喝”的( 男性 )好事者还是不屈不挠地动足脑筋,想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解决方案。比方说,拿女人来说事。鉴于我一直相信地球上各地女人的整体差异性远低于地球上各地的男性,其次,大部分男人自己都相信葡萄酒、雪茄、高尔夫之所以会成为男人至爱,系因每一瓶、每一支、每一杆都很不一样,就像女人( 至少男人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也不得不相信迄今为止以此法最为得当。香港著名酒评家汤马士先生有一次在某品酒会上告诉我:以法国酒为首的旧世界酒,综合口感上就像法国女人的性格,两个字:世故。而所余大部分的旧世界酒,则大致上一如美国大妞的脾气:热情奔放,毫无保留,全部都给你。
彼时,我心中响起的是我的偶像叶玉卿的歌声:“来吧,我什么都应承;来吧,我什么都听命。”与此同时,还难以克制地联想起某专家对各国A片的评价:由于欧洲A片多以贵族、没落贵族和城市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为主角,故普遍散发着一种浓郁的文艺腔,并且略带忧郁、耽溺、慵懒及颓废的气质,文化得来矫情。男女主角,均是一副爱搞不搞的样子。激情过后,往往有一派荒凉虚无感挥之不去。美国A片,傻大妞,肌肉男,热情直白,一见面就开练,一句废话没有。
无论如何,成功的汉化虽然少见,但也并不是绝对没有。我的葡萄酒友赵胤胤,英文比中文流畅,上海话比广东话流畅,喝酒之后,沈阳话又比广东话和上海话更为流畅,就是这么一个家伙,在葡萄酒的汉语表达上却不时有惊人之作。有一次,在“意庐”刚点过菜,店主送了一支意大利酒。通常,意大利酒多少都带有极其鲜明的“兽皮味”( fourrure ),非大荤不能镇其暴。当然一个单词是远远不够的,只见赵胤胤狠晃了一圈杯子,把鼻子埋进杯里,抬起头来只说了四个字:血雨腥风。
一瓶红酒,各自表述(4)
虽然还没喝过最靠谱的意大利酒,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迄今为止所听到对于意大利酒最靠谱的汉语描述。
二、更像唐朝,而不是明朝
针对AOC( Appellation d’Origine Controlee,即法国1936年订立的“法定产区管制法” )这个令欧洲以外的酒商和消费者大呼头痛的障碍,香港人也做出了成功的汉化——应该是“港化”:外国人不明白法国人的AOC法,是不了解关于葡萄酒的历史和地理背景而已,正如外地游客到香港分不清“香港”和“香港岛”、“湾仔”和“大佛口”。若将AOC法代入香港人熟悉的地方名,事情就会一目了然:假设湾仔大佛口某茶餐厅的“大排档式奶茶”为波尔多红酒,则得出:大排档奶茶…波尔多红葡萄酒;中国…法国;香港…波尔多;港岛…梅铎( Medoc );湾仔…上梅铎( Haut…Medoc );大佛口…玛歌( Margaux );某大茶餐厅…列级酒庄第一级( Premier Grand Cru Classe )。
如果不介意今后在喝Medoc或Margaux时不小心喝出了港式奶茶的味道,以上“大排档奶茶AOC”法还是相当管用的。其实,以“来一个,遣返一个”的斗志对葡萄酒术语孜孜不倦的汉化工作固然精神可嘉,但是葡萄酒的话语权与其“夺回”,不如“重建”。梅尔在小说《 一年好时光 》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启发的参考:在巴黎的一场私家品酒订货会上,一位“显然对历史极有研究”的来自上海的买家发表评酒感言:“这酒的感觉‘更像唐朝,而不是明朝’。”彼时,按照小说的形容,作为东道主的法国人(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 )“只顾点头微笑,奉承客人们有敏锐的洞察力,品评到位”。很显然,葡萄酒的话语权一旦被另起炉灶,重建在中国历史语境之中,法国人能做的也只能是“点头微笑”了。如果那个上海人说的不是“更像唐朝,而不是明朝”,而是“更像反右而不是‘文革’”,我保证法国人一定会崩溃到当场嚎啕大哭起来。
从长计议,与其在话语权上下工夫,不如想办法一举夺取葡萄酒的“话事”权——比如全民努力喝酒,使中国成为法国葡萄酒的全球最大买家。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法国人已有“想开了”的迹象。法国葡萄酒瓶身标签上的说明文字,长期以来都以奥妙复杂著称,把欧洲以外的消费者看得一头雾水,故欧洲葡萄酒业者近年来已提出User…friendly的主张,以更亲和包装、更简洁酒标、更方便的开瓶来迎合酒类市场年轻化全球化的趋势,希望将来消费者开一瓶酒就像开一罐可乐那样容易。前几年,在波尔多举行的第十二届Vinexpo国际葡萄酒与烈酒大会上,法国酒Just业务总监Olivier Henry表示:“我们在酒标上对风味的描述,绝不超过两个字!”
事实上,德国人康德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率先想开了。1804年2月12日,康德饮下学生递过来的一杯葡萄酒,喝了一口,说了一句话,然后平静地死去,享年八十。他说了四个字:“味道真美。”甚至连“请你为我停留”这样更靠谱的评语也没舍得给我们留下。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厨 师 秀
不管你有没有留意,也不管你是不是中意,餐厅正在悄悄地变成一个活色生香的秀场,主持这场“餐厅秀”的那个明星,就是大厨。
厨师既是专业人士,厨艺又是一门技艺,任何一门技艺,便都有“炫技”的理由。查此事古已有之。《 庖丁解牛 》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见诸于文献记载的“厨师秀”:“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砉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 桑林 》之舞,乃中《 经首 》之会。”宰头牛也能宰得这样载歌载舞,有型吧。后面还有更酷的:“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当然,庄子故事里的寓言成分太高,《 庖丁解牛 》并非信史,而且,准确地说,那也不能算是“厨师秀”,而是一场“屠夫秀”;目的上,“屠夫秀”是为了启发文惠君悟出“养生之道”的真谛,今之“厨师”则完全是为了取悦食客( 或取悦厨师的老板 )而秀,但在“秀”的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
公开炫技,为了夺取并巩固厨师个人的江湖地位,而当一名厨师以炫耀的姿态在厨房里大演技艺,半是出于自娱,半是向下属所做的示范或示威。两者虽与厨房外面的吃客无涉,却也有助于节奏感的强化,舒缓异化劳动的压抑,无论如何,皆能使吃客们间接得益。除了上述场合,中式餐厅东主传统上通常都把此等制作过程深藏于幕后。与此同时,本着“喝牛奶不必认识那头奶牛”或者“即便认识了那头奶牛也不必目睹挤奶过程”的理性精神,食客们一般也不会有更多的非分之想。
在某种意义上,被藏在厨房里的厨艺可能被视为了房中术,学艺须精,精益求精,但技艺再精湛,也不可公开示人,可示人者,被严格锁定在技艺的成果——例如童颜鹤发,子孙满堂,等等。当然,这里面也不乏技术保护的考量。
由是观之,如果说吃饭是一场大戏,那么,把厨师从幕后厨房搬到食客面前大秀特秀,在消费层面相当于美国大片在正版DVD里加赠了“制作花絮”;如果说dinning out是一种社会行为,那么,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也许就用得上“公开”和“透明”这两个流行于冷战结束前夜的术语了——回归到我们去餐厅的本来目的。作为食客,反手包出的包子,也许吃起来也是不错的,起码不会比正手包出来的差。但是包子的好吃与否与包制的正手、反手之间有无必然的关系,却无人能提供答案。正、反手包子在味觉上所可能造成的快感差异,应该不会大于床上的体位变化。问题是:当餐厅变成一个秀场,我们的身份及行为也不能不随之而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比方说,按照“小剧场效应”,吃饭本身是否也变成了表演的一部分?
在这种意乱情迷的时分( 在你喝牛奶的时候,“那头母牛”突然手舞足蹈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每个人( 包括餐厅东主、厨师、食客 )都适时地需要一点娱乐精神。一起来重温一个美国老段子:一父有二子,长子生性乐观,但父忧其过分乐观;次子生性悲观,其父又忧其过度悲观,遂决定以圣诞礼物为工具,试图调控之,平安夜,悄然于长子屋里放马粪一堆,于次子门外置新车一辆。圣诞日一早,静观二子反应:次子醒来推门见车,非但毫无喜色,反因自己未到合法驾车年龄而忧心忡忡;长子醒来,嗅马粪则狂喜道:“老爸,快说,你送我的那匹小马在哪里?!”
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名食客,面对“厨师秀”的态度其实亦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