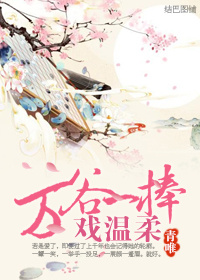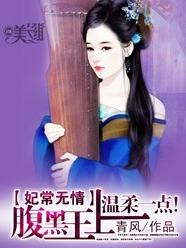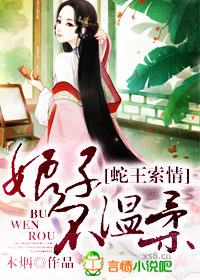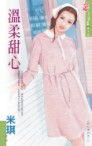我这温柔的厨娘-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火了,把刚端在手里的饭碗往地上一搁,对母亲说,“我不吃饭了。”
母亲说不吃就不吃,你让出地方来,让姐姐哥哥坐宽点。
我站了起来,走出房间。
“人这么小,脾气倒还不小。”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堂屋里没灯,没有一个人跟来。我出了院门,穿得少,外面冷极。院门外路灯被人用皮弓弹灭了,黑压压一片。对面朝天门码头的港口客运站大楼上的大标语在闪烁,似乎听得见隔岸稀疏的鞭炮声。我一路往公共厕所去,那个地方可避风寒,这个除夕夜不会有人。我小心翼翼走进满地是屎尿的厕所里,两只脚踩在两处干净一些的门背后的地上。尽量少吸气,避开一点浓重的臭熏熏的厕所气味。我就站在那里,浑身哆嗦,脑子十分清醒,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下去。
到天亮,家里人才找到我,他们找了一夜,上上下下几条街,谁?也没想到我会在厕所里,是大姐尿急了,上厕所才发现了我。
那个年夜经?常在我的梦中回返。一家子围坐在小铁炉边无论吃什么,其实都是温暖的。年夜饭家里有荣幸得到等待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大姐。大姐没从乡下回来,母亲脸上便没有笑容,她会走到堂屋,甚至到院门外看。
大姐会在半夜一身是汗赶回来,进门就大叫妈。母亲笑得合不拢嘴,上下打量她,给她递开水和热毛巾。难怪二姐说母亲偏心,三哥站在二姐一边。
我高兴母亲高兴,只要母亲高兴,父亲就高兴,这个年才过得高兴。在吃团圆饭前,家里总是打扫楼下房间和阁楼的尘埃,用父亲看过的旧报纸重新糊屋顶和墙壁。桌椅都要搬到天井去用洗衣服的水洗净,再擦干搬回来。公用厨房里有大小不一磨成粉状的汤圆袋子,挂在高处,因为滴水,下面接着盆子。由于彼此不放心,到年夜这天必然移回各自家中。这天父亲会从袋里取出些粉来,做馅,然后包汤圆。一部分为年早晨吃,一部分得先在年夜做油炸汤圆——家里的传统,用来祀典祖先。
父亲说一口浙江?话,与母亲低声说着自己不在人世的家人。我们几个孩子都不敢出声。房间里那扇小窗透出月光,邻居们都在各自庆贺新年,有放鞭炮的,有欢唱的,也有吵架的,孩子啼哭不休。
母亲年夜时说得最多就是外婆,讲外婆的故事,讲她怎么得病从乡下被送到城里这间房子。没钱坐船,走山路会是五六天,可是舅舅们连更连夜不睡觉地赶,两天两夜,他们到家,一身衣服没一处是干的。
流寓伦敦十多年,春节大都在无知觉之中度过。有时倒是英国邻居提醒,是你们中国春节了,祝节日快乐。我才过节。点亮蜡烛吃年夜饭时,我说得最多的也是母亲的故事,她怎么从家乡抗包办婚姻,逃到重庆城里。我做汤圆是想念那个曾经?让我存活下来的家。
写这文章,已能听见年夜的钟声在一步步靠近,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那个与我生命相连的人连挥挥手也不曾有,也走了。他不存在这个世上,这就是事实。今年年夜,我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我也会和粉拌馅,做一碗晶亮剔透的汤圆,对着一轮明月吃起来。
汤圆是甜的,月亮是残的,你不得不信,人心是会变的,变阴晴变圆缺都由不得你。周遭节日的气氛,会一寸寸浸透开来,嘲笑孤独者的魂。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将进“醋”
都知道我喜欢吃醋。没见过我的人,知道我醋劲十足,与我有一面之交的人,更觉得我是在醋罐子里长大的。
男人怕惹一身醋味,由此决定不必与我打交道;女人躲我更远些,以免不小心醋火烧身。
这样一来,我的生活清闲,冷观风花雪月,热对雷电狂雨,透过久远的历史,残酷的战争,重述心里一层层影像,在讲故事中度过平淡日子。写故事累时,给友人写写专栏,偶尔浇上浓厚的四川麻辣醋,让不爱我故乡之人,吱唔得一言发不出。
说起故乡,都说重庆人“口重”。哪怕一碗普通的担担面,也要放十多种调料,辣椒、花椒、麻油、蒜、姜、糖、花生酱等一样少不了,自然不可没有醋。重庆人做菜少不了醋,什么糖醋排骨、醋溜肉丝和白菜等等。每家小店铺里最占地方的,就是一个大酱油缸,一个更宏伟的大醋缸。
我小时几乎天天只能吃泡菜,吃腻了,还是得吃。母亲长年在外做工,父亲眼盲,摸着换泡菜缸沿的水,所以,家里泡菜较酸,夏天经常用来做酸菜汤。那时全国??济紧张,生活困难,凭票买肉,肉稀罕得要命,无肉的漂着几叶青菜的酸菜汤,久吃让我倒胃口,恨酸味。当时我是给酸怕了,决定逃离重庆,远走他乡。他乡再苦,至少可以与吃醋再见。
不料全中国人民都吃醋:北方人吃饺子,没有醋宁愿饿肚子;南方人宽容一些,吃馄饨,也要蘸着醋才香。到秋天螃蟹肥大,就非要姜丝和醋蘸着吃,不然对不起被烧红的螃蟹。真是祖国大地一片醋香。
我却坚持初衷,许多年,都拒醋而远之,若无菜,宁愿拌酱油下饭。后来到了西方,食品不一样,英国的辣椒酱带甜味,着实不好吃,也将就着混过去。欧洲好几国有特色醋,吹得好听,尝过依然是醋,我依然不敢恭维。
一个人阅历丰富了,才知道年轻时有叛逆心理,实在是缺乏大包容之心。觉悟有时候来得很奇怪:五年前的春天,到长沙签售新书《阿难》,出版社就在当地,对我照顾得很周到,美容足浴全套服务,吃饭每顿选不同的饭铺。
我当然非常高兴,胃口大开。况且每顿饭,虽然店铺不同,却必有一样,上好的红葡萄酒,比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名酿醇得多。赞美之余,我忍不住打听湖南人的职业机密:为何酒到湖南,就香味奇特爽口滑润,让我精神也好,睡眠也佳。说了不少好话,才听出了湖南人的秘密:酒里兑了一种醋,叫做贵妃醋。原来湖南人闹革命,理由总与别人不一样。我的拒醋决心,开始动摇。
回到北京后,竟然思之心切。查寻京城,竟无一店售之。在网上辛苦搜索半天,才找到一家店。只好打电话订了一箱贵妃醋,天天晚上当饮料喝。
后来与朋友一起到一家香港人办的饭店吃饭,首先端上来一种淡淡?的清汤,味美如天外之水。喝了,又要了一碗。一问,结果是饭店老板自家酿的醋。
到东南亚一圈,看见柠檬的多种用途,也尝试了各种用柠檬做出的菜、汤和鸡尾酒,都是恰如其分的好。回到家里,我试着用青柠檬和黄柠檬做菜,酸味完全不同,青柠檬更鲜,黄柠檬酸味中性。用柠檬更能消除鱼和牛肉的腥味,加入沙拉?或中式凉菜,更能提味,满嘴清香。
若是吃饺子或面条,加入柠檬汁,可保持饺子本来的美味。
为了试出柠檬的更多用途,我比较了一向受宠的贵妃醋,觉得柠檬味鲜,醋口感醇厚。
于是我下定决心,做个沾酸惹醋的女人。说到底,不在醋罐子里游泳的女人,不能翻?倒海般发醋威掀醋风的女人,肯定被男人看不起。世界秩序太乱,没有吃醋女人出来维持秩序,男人肯定弄得自己不想活下去。
因此,我还是借着那越来越浓的记忆,从厨房飘出的醋味,写了这文章。快哉此醋,可浮一大白。
母亲做稀饭的秘诀
母亲做稀饭时头很低,她的头发很短,眼睛不是太好,整个身体凑近锅。她手里握着长木勺,不时搅动米粒。母亲转过脸来,总是有笑容。
给母亲办丧事,最后一日在重庆,毫无胃口。姐姐问我想吃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冬汗菜稀饭。”
说完便知是想念母亲。那是母亲最喜欢的一种稀饭,稠稠的,带点糯。
饥饿年出生的我,最怕吃稀饭,但母亲做的饭,怎么吃都觉得香。印象中母亲做饭不多,我十八岁离家出走,有十年在路上,决心做一个孤心独胆女子。直到出国后,命运更加颠簸多劫,想到故土之根,才渐渐与母亲联系多了。九六年我与小唐回去看她,住的日子也最久,据小唐说有三个月。我记不得,只感觉那炎夏破天荒。
家里仅客厅有台空调,卧室只好用电风扇,我怕热,正在写《饥饿的女儿》,就在客厅里工作。
每天醒来,母亲已上街市买菜回来。她在厨房做稀饭。四川人叫粥为稀饭,蒸得水干的饭叫干饭。母亲做稀饭会加青菜,每日不同,或加绿豆、红豆,也加过红薯土豆,小火慢慢熬。她从客厅走到厨房,又从厨房走到客厅,看着我伏在电脑上工作,就一声不响地坐在我旁边。
小唐很喜欢吃稀饭。母亲笑着说,“小唐是渠县来的人。”
小唐不解。
母亲说,“那是个穷地方,缺粮,就只能顿顿吃稀饭。”
我流浪时去过那个地方,一个人在渠江边静坐,江水泛着斑驳的阳光,跟长江?一样,那时我对自己面前的路茫然失措。
那个夏天有好几日都是40度高温,而报道的只是38度、39度。母亲做好了稀饭,端到客厅,降温。她挟泡豇豆泡红萝卜,一家人围坐桌边,吃着饭,听母亲讲乡里旧事。
昨晚我在家里做小米红枣稀饭,做好了,却没有香味。母亲在我小时就告诉过做稀饭的秘诀:料得新鲜,菜要嫩,用瓦罐和山里泉水,最紧要是有好心境。
我差后者,悲伤充满了我的心。屋里飘浮着熟悉的音乐,母亲的背影忽近忽远,这一次她没有朝我转过脸露出笑容来。
最难忘的童年佳肴
父亲,也就是养父,每临近清明节,都会做清明粑。每年一开春,我就眼巴巴等着和父亲一起上山。
学着走路是一岁多,两岁不必大人扶,自个儿走。三岁就跟父亲上山。坡弯弯曲曲,不是特陡,沿途开有野花,五颜六色,晃着眼香。最喜欢豌豆胡豆花,嫩粉嫩白,女孩子的花。四五岁后,慢慢走,父亲不必时时背我,他不放心,就跟在我身后。站在家门前,抬头可见南山,连绵着黄山,奇异挺拔,酷似骆驼孔雀大象,山前临江,山后有山,云雾缭绕,怪是神秘。看似近,真要爬上山顶,却要花两小时。一般我们就在山腰上,沿清水溪走,不到一碗泉就止步。
父亲在家很少说话,到了山上,他也是一句顶一句,实打实。坡上潮湿地方,生有一种草本细叶,周身白毛茸茸。父亲蹲下,摘了一瓣,放在我手心里,说,灾荒年没吃的,都吃它,后来连它都没得吃,就吃它的根。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父亲说,在浙??老家叫“锦菜”、“米菜”,四川人叫“清明菜”。这么多名字,我记不住,但是记住了父亲说话时的神情,仿佛久远的过去,拉着他的脑袋。父亲吩咐我摘尖儿,留住根,明年还能摘。清明一刻最嫩,之前只嫩香,气稍弱,之后显老,端午节一过,老得不能吃了。
满满一网篓,父亲下山前用溪水洗净,回家后又用水清一遍。切碎,晾在竹箕里,准备面,通常是面粉,偶尔用糯米粉。加入清明菜,揉均匀,拍成巴掌那么大,薄薄的一个接一个,贴在铁锅周围,锅底放半木勺水,盖上锅盖焖。十分钟后,揭锅盖,锅底还残留滚烫热水,顺时针转,一直到个个粑透黄,用锅铲翻个儿,两面黄就起锅了。蘸些白糖,原本糯是糯,菜香是香,现在是饼黄、陷露点点碎白,吃在嘴里,有嚼劲,酥软软甜蜜蜜,香气妩媚,胃口大开。
上初中时,父亲眼盲厉害,夜里照样啥也不见,白天视觉更差,不可能到山上摘清明菜。我呢,各种书都乱看,看到清明粑居然是父亲老家浙南的传统佳肴,历史久远,溯至晋文公、介子推,清明菜,学名叫“鼠尾草”,也叫“艾草”或“陈艾”。我问父亲。
父亲说,同样名字,但不是端午节驱逐蚊虫、熬水洗澡、少长疔疮用的那种。
下年吧,我去摘清明菜,粑里可以放鲜笋芥菜肉丁?
父亲没有回答。边上邻居马妈搭讪,鲜笋芥菜肉丁?痴人说梦吧?美滋了,没天没地?
经她这一顿抢白,我脸红了。买肉凭票,大清早排长队,还可能买不着肉,就是节省了票,有肉,可到哪里去弄鲜笋芥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真是笑话。
回想父亲一年年做的清明粑,大都是甜的,偶尔咸,撒点花椒粉。他专心致志切菜和面,埋头在灶前转动铁锅炕粑,与邻居们八卦做菜,嘻笑怒?骂截然不同。父亲嗜叶子烟和陀茶,饭量不多,从不挑嘴。有一次,下乡当知青的大姐回城,她看厚厚的《红楼梦》。我也趁空看,边看边抄?在小本子上。红楼里有个丫头叫晴雯,盛了一碗火腿鲜笋汤,端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说:“好烫!”另一丫头袭人笑道:“菩萨,能几日不见荤,馋的这样起来。”一面说,一面忙端起轻轻用口吹。她教一旁的人学着服侍宝玉,别一味呆憨呆睡。口劲轻着,别吹上唾沫星儿。她认为那汤肯定好喝。我年纪太小,不太看得懂小说,倒是对里面的吃感兴趣。到走廊前,对着栏杆下堂屋的父亲问,过年时他做的咸肉和鲜肉汤,是否就是小说里的宝玉吃的汤?
父亲像是没听见一样,继续裹他的叶子烟。大姐从楼下房间一步跨入堂屋,快人快语:“那是爸爸的浙江家乡菜,腌笃鲜,若是用浙江金华或宣威的火腿,味才好。爸爸以前走船时买回来我吃过,爸爸还用来做过清明菜滋饭。”她得意地说。
我好奇地问怎么做。大姐一步步上楼来,嘴里卖着关子说,你得请我,我才说。
我请她说。她看看我半晌,才说,谁也不会告诉你,只有我。用清明菜和糯米,菜少一点,米多一些,放盐和葱花和猪油。菜切碎。米淘净。油锅烧热后,下火腿和清明菜炒,撒盐炒出味来,加适量水,放糯米拌匀,盖好锅盖,文火煮熟,出锅前放葱花,就是一顿香喷喷的饭菜。
大姐说得我馋极,口水都快流下。
大姐向来会说,不会做,一上灶,再好的东西一经?她手都变难吃。我羡慕她能吃到父亲做的清明菜滋饭。尤其是父亲再也不做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