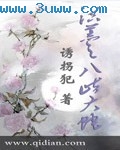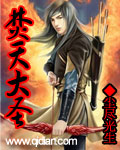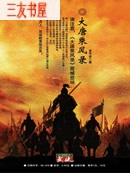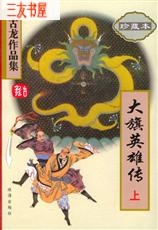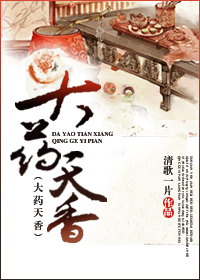论北大-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卷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73—74。。 最好的txt下载网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冷眼旁观的态度——他对“浅而清”的刘半农的“亲近”,对有“武库”的陈、胡的佩服,以及对陈的“不提防”和对胡的要“侧着头想一想”,都耐人寻味。特别是对于胡适,他要看一看,“想一想”,这一看一想之后,就引出了许多分歧,或者说预伏着此后的种种不满与分化。
(二)
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入正题,讲五四以后的“老北大的故事”了。——我想从一个不大不小的“讲义风潮”说起。张华、公炎冰先生写有《1922年北京大学讲义风潮述评》,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2期,以下讲述利用了该文的材料,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致谢。
风潮是由讲义引起的:蔡元培主掌北大后,对老师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上课必须发讲义。——而发讲义,鲁迅和胡适的风格也不一样。据学生回忆,鲁迅的大纲非常简要,没几个字,而胡适的讲义总是开一大堆书单,非常详细,这样的讲义当然受学生欢迎。但是日子久了以后,校方就发现了两大弊病:有些学生以为反正有了讲义,到考试了只要一背就混过去了,这就给一些偷懒的学生有可乘之机;另外北大上课都是敞开的——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甚至形成一个传统:该听课的不听,不该听的(即不在籍的)听课反而更积极。蹭课的学生来得早,把讲义全拿光了,正式的学生来了,就没有讲义了。只得不断地印,讲义费用就吃不消了。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北大经蔡校长提出,校评议会通过决议,要收讲义费。不料却引起了学生的不满,1922年10月17号下午,就有几十个学生涌到红楼前请愿。当蔡元培先生赶来时,学生已经散了。第二天上午,又有数十学生到校长室要求学校取消讲义费,人越聚越多,最后达到几百人,秩序大乱。蔡元培解释说:“收讲义费是校评议会做的决定,我只能把你们的要求转达给评议会,由评议会作出最后决定。”并且答应暂时先不收费,将来评议会作出最后决定再收,这段时间的费用由自己个人支付,这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年轻气盛的学生不听,坚持要他当场作出决定,而且话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极端。平时温和的蔡元培勃然大怒,将写好的字据撕掉。据在场的蒋梦麟回忆,蔡先生拍案而起,怒目大叫:“我跟你们决斗!”校长要和学生决斗,这在北大,以至中国教育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第二天他就宣布辞职,并在辞职书里指责学生“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行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止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并自责“平时训练无方”,“惟有恳请辞职”。紧接着总务长和其他行政负责人都纷纷辞职,全体职员也宣布暂停办公辞职,事情就闹大了。学生召开大会商量对学校局势的态度。当时有三种意见:有的认为我们学生是有点过激,但校长要走,我们也不挽留。有的则认为应承认过失,力挽蔡校长。第三派主张有条件地挽留,条件是取消讲义费、财务公开。这三派辩论了一个多小时,毫无结果。——这也是北大“传统”:好辩论而无结果。于是就有学生建议,大家都到操场上去,分成三队,每派站一队。当时学生还不懂民主的程序,没办法就站队,结果秩序更乱。不过,看起来主张挽留和有条件挽留的占多数。于是赞成者又集合起来派代表去见蔡元培。但蔡元培当天就走了,到西山去了,找不到了。
而且校务会议已经作出决定,将此次风潮定性为“学生暴动”,并认定学生冯省三“唆使在场外学生入室殴打”,“应即除名”。同时宣布“兹为确知暴动责任者之姓名起见,要求全体学生于本星期内各以书面向系主任声明曾否与闻;如不声明,认为与闻暴动,应请校长照章惩戒”。
在校方的强大压力下,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据说有人出主意将责任推到因劝袁世凯称帝而声名狼藉的杨度身上,说他想来当校长,当天鼓噪的人群中就有杨派来的人起哄。这样的无端诬陷显然不够正大光明。最后学生一致通过决议,说是“二三捣乱分子,别有用意,利用机会,于要求取消讲义费时作出种种轨外行动”,因此同意将冯省三除名,并称“如再有捣乱行为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蔡元培和评议会对此结果表示满意,蔡校长又回到了学校,这场风潮也就在皆大欢喜中结束了。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5)
今天我们重看这场“讲义风潮”,或者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蔡元培、胡适、周氏兄弟对这场风潮的不同反应和态度,就很耐寻味。
蔡元培是当事人,他的态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在激愤之中宣布要与学生决斗,这就很能显示他的独特思想与个性。后来,他在全校大会上,曾把这次风潮称为“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的“暴举”。可见他之提出要与对他非礼施压的学生决斗,正是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在他看来,他与学生,不仅存在着校长与学生的不同身份,更是独立的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彼此是平等的,学生绝没有权力因为自己是学生,或者凭借人多势众来围攻自己,他也绝不能屈服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即使是自己的学生。蔡元培的这一态度是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的。但是蔡元培毕竟不是普通的个人。当他和校行政方面把学生的过激行为宣布为“暴动”,并加以“借端生事,意图破坏”等罪名,不但未经充分调查,即以冯省三作为替罪羊而除名,还要求所有的学生声明“曾否与闻”,并以辞职相威胁,显然是运用校长的权力对学生施压。据说他曾对校长室秘书章川岛说,他所以要辞职是因为“纸老虎哪能戳一个洞”,这时他所要维护的就不是个人的人格,而是校长的权力与权威了。
胡适的反应很有意思。事情发生时,他不在北京。但事情发生后,他马上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文章,认定这是“少数学生”的“暴乱”,并且提出“几十个暴乱分子即可以败坏二千六百人的团体名誉,即可以使全校陷于无政府的状态,这是何等的危机?”《这一周·43》,《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38—439。但私下在日记中,又表示校方“用全体辞职为执行纪律的武器”是“毫无道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卷3,页856。在###平定后的全校师生大会上,胡适又进一步批评“这次风潮,纯粹是无建设的”,因此他希望从此“趋向建设一条路上,可以为北京大学开一个新纪元,不要再在这种讲义费的小事情注意了”。《在北大###平定后之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页445—446。他显然希望把###引向制度建设。据说后来他曾建议学生组织自治会,由各班代表组成众议院,以每系一人、每年级一人组成参议院,在北大内部实行西方民主实验,对学生进行民主的训练,以防被少数人利用。这是典型的胡适的思路。但他的主张遭到了实际主持校务的总务长蒋梦麟的反对,说搞什么参议院、众议院,学生就更要捣乱了。冯省三被开除后,曾经找到胡适求助,要求回校当旁听生,但遭到胡适的拒绝。胡适显然不喜欢冯省三,把他看成是暴乱分子。有的研究者说,胡适可以容忍弟子思想上的异端,却不能容忍行为上的过激,这大概是符合胡适的思想实际与处事原则的。
最有意思的是周氏兄弟的反应。我们说过,鲁迅和周作人无论在《新青年》内部,还是在北大,都是“客卿”,讲义事件本跟他们无关,在风潮发生过程中,他们也未置一辞,与胡适“非表态不可”的心态完全不同。但风潮过去,几乎所有的人——校长、老师、学生——皆大欢喜,以为没事儿了,鲁迅却提出了问题。他在1922年11月18日,也即风潮结束一个月以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即小见大》,抓住这件已经被人们淡忘了的“小”事情不放,追问不止: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这次风潮难道真是冯省三一个人掀起的吗?鲁迅提出了质疑。其实,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冯省三不过是一个替罪羊,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大家——从闹事的学生到宣布辞职的校长、教职员——都可以下台。这本是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鲁迅却偏要点破:这正是鲁迅不识相之处,也是鲁迅之为鲁迅。而且他还要进一步追问:“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其实,校方也得胜了——钱注),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就是说,你们大家都满意了:校方满意了,维护了你的威严;学生满意了,达到了你们的要求;但是你们就没有想到那作为牺牲者的冯省三,他个人的处境与痛苦。这正是要害所在:“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即小见大》,《鲁迅全集》卷1,页429。“散胙”,就是中国古代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为群众牺牲的人,最后反而被群众吃掉——“即小见大”,鲁迅从北大讲义风潮所看到的,正是这血淋淋的“吃人肉的筵席”。这样的历史悲剧在辛亥革命中发生过,鲁迅因此写有《药》;现在,又在被称为五四发源地的北京大学重演了,鲁迅的忧愤也就格外的深广。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6)
与鲁迅站在一起,关注被牺牲者的,仅有周作人。周作人关注的是在整个事件中被忽略与遮蔽的作为真实的个体存在的冯省三。他后来专门写文章为冯省三这个“人”作辩护。他介绍说,冯省三是“爱罗先珂君在中国所教成的三个学生之一,很热心于世界语运动,发言最多,非常率直而且粗鲁,在初听的人或者没有很好的印象”,但是接触多了,就“知道他是个大孩子,他因此常要得罪人,但我以为可爱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他是山东人,据他说家里是务农的,五岁时,父亲就给订婚了,他是到北京来逃婚的,靠打短工读书,在北大预科上法文班,因为没有钱交学费还没有毕业。就是这么一个苦学生,闹讲义风潮那天,他还在教室上英语课,下课时听见楼下喧吵,去看热闹,不知不觉地就卷进去了,还以山东大汉固有的激烈,说了几句“我们打进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这样的带有煽动性的话,后来真谋事者都溜走了,他还在那里大喊大叫,就被校方与群众选作了替罪羊。周作人回忆说,冯省三曾很热情地问他:“周先生你认为我有什么缺点?”周作人回答说,你的缺点就是“人太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太相信性善之说,对于人们缺少防备”。《世界语读本》,《周作人自选文集·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18—119。无论是在蔡元培,还是在胡适的眼里,冯省三都是一个“暴徒”,但在周氏兄弟眼中,他却是一个有缺点的可爱的“大孩子”。在蔡元培将其开除,胡适将他拒之门外的时候,周氏兄弟写文章为他辩护是很自然的:他们重视的是个体的人,对于学生,即使他们犯了错误,也是抱有理解与同情的态度的。后来冯省三办世界语学校,周作人为他编的《世界语读本》作序,鲁迅不但应允担任学校董事,还免费教书达一年之久。有意思的是,蔡元培也担任了冯省三的学校的董事:当年他为维护校长的权威,将冯省三开除;现在大概是了解是非真相,又对他表示同情与支持,这也同样是很能表现蔡元培的为人的。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再深入一步:本来讲义风潮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为什么蔡元培和胡适都看得这么重,认为这是“暴动”,非要用这样的非常手段(从以辞职相威胁,到向替罪羊开刀)将其压下去不可?这需要对蔡元培的基本教育思想及其内在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五四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校内矛盾这两个方面来作更深入的考察。
大家都知道,蔡元培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来北大的,所以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首先谈到的就是“大学之性质”。他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打破做官发财思想”,“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在大学期间“植其根,勤其学”,打好基础,刻苦学习。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163—164。从这样一个理念出发,他当然反对学生参与政治。1918年5月,北大和北京高师等校学生为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决定游行请愿,蔡元培即竭力阻止,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派代表到我这儿来陈述,我会转告政府。你们不能随意上街”。但是学生们不听他的,还是去了。蔡元培于是宣布辞职。——在他看来,大学里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不要去管政治;现在学生不读书上街游行,校长管不住学生,是为失责,就应该辞职。
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存在着矛盾的,一位外国学者分析蔡元培对北大的期待就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期待北大成为一个“献身学术研究和自我修养的一个封闭的圣地”,与社会隔绝,静心做学问;但同时他又希望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能够担负起“指导社会”的责任。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金安平、张毅译,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