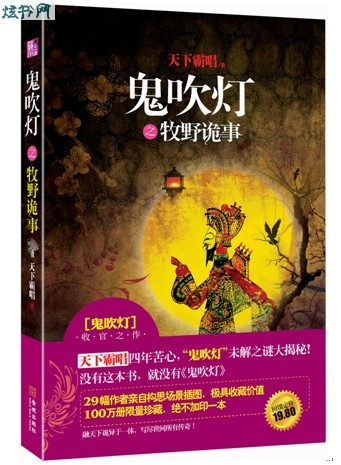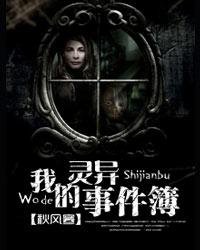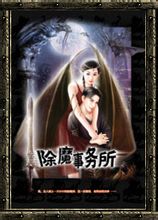二流堂纪事-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字台,我则排起四只木板椅。
一个早晨,我还睡在木板椅上未起身,阿咪拿一根竹子在石板缝处挑了一条蛇皮在我的面前逗乐。我生平怕蛇,吓得大嚷大叫,阿咪却为此受到老夏一顿大骂,可能还轻轻打了几下。这阿咪,是老夏最宝贝的女儿,终老人一生,除抗战中的六年,阿咪去苏留学几年,在秦城监狱九年,其他时间,父女一直是在一起的。
但那条小蛇皮却促成四德村依庐在二十天中迅速建成,依庐分左右“两单元”,每单元有一客厅,一卧室兼“书房”,靠老夏屋旁有一厨房(我不用),一厕(共用)。那时他儿女都已上学,老夏怕他们在学校跟国民党子弟搞阶级斗争,凡有人找他谈问题,他就使用我的屋子。
阿咪喜爱宠物,她养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兔子,兔子死了,她给它埋葬,砌了一个小坑。可是大头颇有英雄豪杰的气概,捋起袖子,用一口四川腔:“杀来吃掉!”也是用四川腔对我尊称“唐老人”,后来他妈和阿咪一直以唐老人叫我几十年。那时我是三十一岁。
有天,白杨穿一件黑丝绒旗袍来看老夏,大头瞪大眼睛,靠着我的房门又用四川腔自言自语说:“哪里来NUN个(那么)好看的女人。” 老夏轻声说:“糟糕,将来会不会是一个好色之徒。”
如今,五十余年过去,他只娶了一个苏州美女,阿咪则配上了我们的好友才女赵慧琛的弟弟。
老夏坐监,必然要牵连家属,苏州小媳妇带着婴儿被打发到唐山一个矿区当矿医。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这个婴儿异乎寻常地大哭,他母亲只好起床喂奶,正在此时,她发现土地在微微摇动,她连忙抱了小孩往屋外跑,到了空地上,一个轰雷之声,房屋倒塌了。
俗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九八一年我与叶浅予、浅予的孙女、龚之方、我女儿结伴经苏州乘船到杭州,转富春江,过浅予的老家桐庐画院,再到千岛湖旅游。过苏州时,我与女儿、浅予孙女到大头的岳母家去看老夏这位有后福的孙子,他警惕性很高,只有在小妹把照相机给他做抵押之后,他才让抱。
我和夏太也有过一点小矛盾。我这人患贱,爱穿破衣服。五十年前花六百港元缝制一套西装,穿了几次就让蛀虫啃吃了。十多元一件衬衣,一穿十五年。有一回我在依庐屋前空地上晒衣服,夏太看到许多新衬衣,就悄悄用小指头在我背后衬衣的破小洞中一勾,顿时衬衣裂成两爿。我大吼一声,把她吓哭了。
解放后,我每次去看老夏,只见她都专心一意在画画,画仕女图。夏太啊,在这暴风急雨的时代,你怎能画这些东西。在红卫兵抄家那天,她吓坏了。她曾经陪着老夏经过悠长的岁月,但她几时才曾看到这样的大阵仗。她全身战栗,坐在她平时暗藏私蓄两根小金条的床边,抄家者一看,料有蹊跷,于是连这东西也被抄去。(我在打扫厕所时,听到了两位抄家者的得意谈话。)
这地球似乎变小了。三年前,我们到隔开美国与加拿大的底特律河的中间一个小岛上的儿童乐园,遇到一位来自北京的白白胖胖的年轻姑娘,一谈之下,知道她是北京一所工科大学的学生,她的老师中,有一位便是大头,我才知道他是工科大学的教师。老夏留日学的是工科,现在儿子接了他这方面的衣钵,女儿则接了他另一方面的文学衣钵。
老夏的信终于偶然找到了,它夹在一本照相簿中,作为永久纪念的意思,信封则只有等待第二次偶然了。
睹物思人,惆怅不已。
回忆“左联的日子”(1)
记不清什么时候起,我几乎每夜都做梦,连午睡、在电车上、渡轮上打盹也做起梦。有美梦,有恶梦,也有连续梦。绝大多数梦境在一醒转时便忘得一干二净,也有一记便记住几十年的。在做恶梦时梦里曾经催促自己快醒;在做美梦时却告诫自己赖着,想极力留住美梦,但总是留不住,追不上。有两个记得最长久的梦:在一座万丈高山上,这山像一颗椭圆形大石蛋,水从山上奔流下泻,我便斜躺在水面往下直冲;在清澈的海水中,我傍着一艘大轮船而行;五彩缤纷的鱼群也在我身旁游弋,轮船过土坎不能前进时,我便帮助推动。
梦境,不论是美梦还是恶梦,几乎是轻抚我心灵的一双温暖的手。
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们也有过梦的追求,那时,你在前面紧追,我也紧跟着你的身影。我们终于追到了一片绚烂的光彩,我们正在雀跃欢呼的时候,那光束却碎裂成一堆堆败絮。
前几天,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帮助人家搬进一排排新颖的小屋,我力大无比,一手抓起一只大箱子,健步如飞。正在干得欢时,我的糖尿病的尿频折磨着我,我醒了。待我从浴室回来,躺上床,我的梦又继续。如是者四五次,我仍是做着同样的梦,就像电视连续剧。我曾经多次做这样的梦。
昨夜你来入梦了!你坐在床边一只大躺椅上,我则坐在你的床沿,我们在轻声聊天。但这地方很生疏:一长排大房间,空荡荡,没有墙和门,只有一长列矮门坎,外面是一条宽大的长廊,有十六七米长,另一面是一列长窗,你的床和躺椅就在这过道上。我们谈着谈着,你抬起头来,似乎有什么悄悄话要说,忽然从你床边走过一个人,你便把话头转移了,等那人走过,另一阵脚步声却把我催醒了。
躺上床,我想再做那连续梦,却一直不能入寐。刚才那个梦怎么追也追不上了。
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重读你的《懒寻旧梦录》,我把时光拨回六十六年前。一幕幕往事如梦如烟,凄凄迷迷,惊险、紧张、欢乐、振奋、幻灭、悲伤都交织在这六十六卷长剧中。
那时,一个刚刚踏进社会的无知青少年,仅凭血气方刚,热爱文艺,经印度洋、太平洋,万水千山,闯进了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并且蓦然之间拜识了一群文坛精英,恍惚一场美梦,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一、结识大批文化名人
就在热闹的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更新舞台”的后楼上,这里是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总部。我结识了大批当时名闻全国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华汉(阳翰笙)、冯乃超、沈雁冰(茅盾)、钱杏(阿英)、郑伯奇、戴平万、周起应(周扬)、沈起予和你等等几十位,其中和你、潘汉年、阳翰笙、阿英、田汉、孟超、杜国庠等一直深交数十年直到你们故世。如今你们都在天堂聚会了,将来我能不能也到你们那里再为你们打杂呢?
那时,我从一个炎热的地带来到上海,迎接我的竟是一场罕有的大风雪,我怎知这场风雪是预卜我的一生。
你以“福将”知名,我可能也沾了你的“福”光。我到达上海三天,一位翩翩小开——潘汉年,便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为我安排了生活、工作,我便住到老西门周全平老板的西门书店阁楼上,当起书店小伙计。当年周全平和潘汉年、叶灵凤是创造社的三位有名的小伙计,现在周当起老板了。
半年之后,“左联”成立,潘汉年把我带到这个新地方,那时我的心情是多么兴奋和激动。另一位也和我一起到这地方当“盟徒”的青少年丁锐爪,他的兴奋也不下于我,我从他眼眶里的泪光可以看得出来。(这“盟徒”是我从学徒套出来的,有别于“盟员”,我们的任务是打扫卫生、整理文件、抄抄写写。)这里充满活泼,紧张,祥和之气。每个人都显出慈祥的笑脸。我们很愉快地工作,有时一直到深夜。我们依旧住在西门书店阁楼,一早匆匆用开水泡了小半碗泡饭,吃完便走。周全平倒没有什么,只是他老婆每天都瞪着眼睛送我们出门。
不久,火热的“红五月”来了,这个月从“五一”到“五卅”有几个大纪念日,每次都规定要全体参加。机关内也更热闹了。本来平时你和阿英、汉年等就比别的人更多露面。这一时期,就更多出现了。
二、“五卅”示威被捕
在南京路上的“飞行###”,有过大损失,也有安然收兵,喊几句口号,一开始就散了,四边都是大公司商店,人群拥杂,红头阿三再高大也看不出谁是谁非。到五月尾,上得山多终遇虎,这次是“五卅”,必须到杨树浦工人区示威。可是当我到达集合地点,脚下尚未站稳,威未示出,号未出口,领子已被一只大手抓住,还是印度阿三,路旁排着几辆黑色囚车,满载而归。
我们这一车人在看守所卸下时,那间临时大牢已经有七八十号人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彭康也来了!”只见一个高大的人,昂首阔步,被押上大楼梯,此时,全监响起了雄壮的《国际歌》,歌声震荡着整座监狱,彭康的脚步也似乎在为歌声拍板。
在牢狱中示威竟是最安全的,那些在一旁观看的巡捕、红头阿三也傻了,他们也不想把这些示威者赶出去。
上法庭了。那时我既不会说上海话,也不会说普通话,在海船上半个月向一位同船的四川人学了几句川话,在法庭上也用不上,我只能一问三摇头,有时说一句法官听不懂的潮州话,于是从被告栏里被赶下来,有人写个条子告诉我:判决关六个月。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回忆“左联的日子”(2)
我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剃光头、洗大澡、换新衣,关进了一个三四米左右的铁栏“笼”里,同住的人叫左戈,从名字大概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在地板上刚坐下,饭就送来了:是一只又窄又高的薄铁饭盒,这伙食比我在外面的好多了。据左戈介绍,饭是红米加油蒸,菜是一块红烧肉、卤鱼、焖蚕豆、青菜,每天一换,四天一转。
左戈先教我听上海话,然后向我宣传革命。他对彭康被捕,起初认为大人物不应如此轻易牺牲,他又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似乎是天经地义,义不容辞。
三、坐监六个月出狱
六月很快就来到。我的上海话可以和他对答如流了。他千叮万嘱我绝不可以立刻就到机关或熟人家里去,要注意身后有没有人盯梢:为了保护同志,也为了保护自己,免得马上又回到原地——监狱。
我没有去“左联”机关,我在南京路踯躅,入夜,我到北四路坐在一位同乡的靠街大梯口,深夜的冷风把我一层层地吹上去。第二天睡了一个上午,下午到光华书局去投信给潘汉年,第四天我便和他接上了头。他叫我不要到“左联”去了,又吩咐尹五在四川里为我租一个亭子间,接转文件、宣传品。(柔石所住的一个楼下,是我每天必经的地方,我们在他家里偶然一次相遇;在你进入电影领域之后,我们又有一次在胡考的编辑室意外的邂逅。此后便各自走各人的羊肠小道或者是独木桥,但是我们总是互相呼应着,我知道你的来踪,你知道我的去影。)柔石被捕,潘汉年叫我丢下东西离开,这一年,我换了四五个住处。你在与潘失去联系的同时,我也和他断了联系,他本来想带我去苏区的,后来说交通有麻烦便吹了。
这时候我住在一位同乡郑应时处,他是郑正秋的亲人,也是蔡楚生的同乡,于是我便获得一些电影消息,我把它写给袁殊的《文艺新闻》,他很高兴,我也不时去《文艺新闻》坐坐,但我没有遇到你。
我在逛旧书店时买到一本英文《电影小辞典》,我试着翻译一些寄给一本小刊物叫《银幕周报》,被采用了。这就鼓起我写作的勇气。时报辟电影版,柯灵、尘无和我大概是最早一批为它写稿的人,可能是出版的第二天,我以“抗战意识”严厉批评刘别谦的《深闺梦里人》是一部和平主义的影片,当时这部片因为技巧高超,是很吸引人的。其后又评过一部片,于是我便获得一顶影评人的桂冠,但从此我却不敢写影评了。你恐怕也被懵住了,一九四七年在香港为《华商报》组成 “七人影评”时,却把我拉进了。七人:夏衍、于伶、洪遒、华嘉、韩北屏、陈残云和我,我却总是请假溜号。解放后在北京,钟惦和凤子搞影评小组又邀我参加,我仍借故婉辞了。不过,我却歪打正着,我们在这被称为黑暗的电影圈又碰上了。
四、辣面书生 若隐若现
我想提一位被你封为“辣面书生”的孙师毅,除了左联之外,他的名字总在你的许多活动中跳跃:在你被牵入袁殊、王莹事件;在你与潘汉年的会见中;在“怪西人”事件中;在你的“隐居”时期中…… 他都若隐若现。潘“失踪”后,有一天,他约我帮他抄写一些东西,说是潘的好友姓周的要的。我当然马上就答应了,他在爵禄饭店(我在忆念孙一文中写成“一品香”,前几年我去上海时在西藏路观察了一下,才知道错了。)开了一个房间,要了一个鸦片烟盘、两只烟枪,当有人敲门时,两个“洋场恶少”便躺到烟铺上。他从他的江西老表那里搞来了一批剿匪军事材料。我们便夜以继日地抄写,然后便有人来取去。井冈山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似乎都是天兵天将把他们赶跑了。一九五八年周总理招待孙住了一年半新侨饭店,大概就是对他的报偿吧!
在抄写工作结束后,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以后的工作,他通过一位朋友介绍我去见《中华日报》老板林柏生,三言两语,我便在那里编起《电影新地》、《银座》、《电影艺术》周刊,我又在你的麾下,跟随你向前行进,时间长达四年余,只可惜没有和你配合得好。
“左翼”十年,你的功过是非,举世昭昭,连那三个月的隐蔽生活就是到二十余年后的“文革”,当年许多活着的人都是了然的。可是蓝苹仍是穷追不舍。我有一次在“牛棚”接待外调时,听到隔室另一起外调的表演,仿若春节探亲访友拜年:“首长让我们向你问好!”“你要注意保重身体”,“你不用担心”。然后有一阵轻声:“为什么要隐蔽几个月,大胆设想,好好分析一下。”这人大概受到启发,啊啊连声。其后我看到造反头头桌子上成叠的材料,不过不知道所写的内容。后来我看到你活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