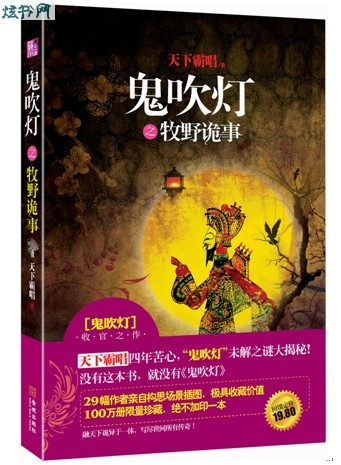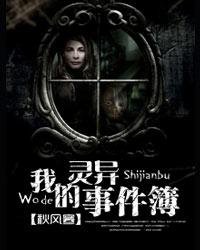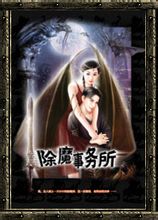二流堂纪事-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电影史学家是无可非议的。他有十几箱“文化档案”,朋友们开玩笑说你给孙师毅写一张条子,他也存入档案了;他的脑子就是一只大档案柜。某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李进的仙人洞照片,附着毛泽东的诗。人们都在猜测此李进是何许人,孙师毅马上就举出此人乃江青。
然而,老师有这种积累资料档案的习惯,他的学生当然是熟知的。江青费很大气力在上海查抄销毁她过去的历史资料。孙师毅家里这类资料当然不会很少,因此他的家也抄得特别彻底。学生对他的恩宠是严格审查;他的严重的心脏病对她说来,正是一件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在他弥留的时刻,他问妻子:“阿唐会来吗?” 这时候,我正在上斗争的第一课,我也不知什么人在耳边嗡嗡叫,我只顾点头哈腰,我只祈祷有谁吼一声:“滚下去!”
握着一只冰凉的手,我想着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在我和他抄写东西时,学了一点他的笔法,特别是他的签名。我在他的女朋友的门上留了一个字条,“孙师毅到此一游”,引起他们吵了一架。——这是我欠他的。
他也欠了我的:他曾夸言我的墓志铭非他写不可。但是他却先走了。就此互相抵销吧!
一九八四年六月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和金焰相处的日子(1)
我和金焰熟悉起来,是以一篇骂他的文章作为敲门砖的。
我之成为影迷,是从二十岁才开始的。一经入迷,就迷得不可收拾。我那时候看电影,就和现在国外在举办的什么《某人电影回顾展》一样,我专挑选某人主演的影片,一部一部地赶着看,哪怕是在远郊区,我也无一漏去。我首先是看阮玲玉的,其次是看金焰的,他们有不少是合演的,碰上了,我又再看一遍。
从报上,我又知道金焰是南国社的人,是和田汉有关的,这是一个进步演员,益发对他起了敬仰之意。
他演过不少好片,也演过一些宣扬封建道德的影片。岂有此理!我当时已在报上写一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有此特权,就批它一通。
是事出偶然还是有意的安排,我的一位好友郑应时(也是金的好友),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一经介绍,金就指着我的鼻子,眯缝着眼皮,笑得像个孩子,他说,“你就是在报上骂我的!……”这就是那个当年风魔着万千电影观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电影皇帝”!那时,我虽然也向往革命,但还没有觉悟到要打倒明星制度,更没有想到一切的光荣要归于敬爱的啥啥同志,要用某某集体创作演出的名义,因之,批他一下也是很皮毛的。
从此,我们相交了整整五十年。
我得到老金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因事在深圳特区。我去不去上海呢?!去上海,我必然要参加遗体告别。所谓遗体告别,这是新增的栏目,因为那些年时兴毁尸灭迹,所以存有尸骸的就让亲友们告别了。但在过去的追悼会上环行过遗体,也就包括在内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一个遗体是陆丽霞,那是在阮玲玉死后不久,当时她刚刚从病房送到太平间,还没有盥洗、化妆,满脸血迹,状极可怖。自那时起,我就不参加任何遗体告别,即使告别是和追悼会同时举行,我也避而不视。
为什么要告别,何必不在脑里保存一个美好的印象呢?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为到广州之后又忙着其他的事,我只好和广东影协几位朋友打了个吊唁电报。
除夕前一天我回到北京,女儿在打扫卫生迎接节日。突然,一阵悠扬的《魂断蓝桥》的乐曲响了起来。
这是一只德国古老的大啤酒杯底下的八音匣“弹奏”出来的。当你擎起杯子时,就发出乐声。它是老金一件心爱的外国“古董”。我在这只古董上“丢了脸”。
那时他住在徐家汇西北远离喧闹的市里一座小洋房中。这一天为了老金的生日,屋里挤了一二十人,三个人的打“亨”;四个人的打五百分;五个人的打麻将加做梦;我和老金、吴永刚等五六人在喝啤酒。
吴永刚眯着眼朝我说:“今天这箱啤酒,我想应该是你或我请客。” 他指着玻璃柜上那只古董酒杯:“我们把杯子倒满了,在音乐结束前喝完了,谁就算获胜,对方请客;如果没喝完,就算败了。随便你挑选哪一方。”
我已经喝了两瓶,看着这个杯子,去掉一节八音匣,充其量装上一瓶,我举起手表示应战,由我喝酒,郑应时给我做表情,劝我不干,我装没有看见。随后,八音匣上了发条,灌进啤酒。
第二瓶倒完了,杯子里的酒还未满,我立刻阻止倒入第三瓶。“行了,我请客,大家来,喝酒!”我倒出一小杯。
“你请客也得装满了,再喝上一口。”
满屋狂笑。我的脸在熊熊燃烧。
转眼已经五十年。青年时代的豪情呵!不过,我此后也不再赌酒了。
如果光阴似箭,那有多好。可惜的是,光阴也似乎随着原子时代进入超音速、超光速……
三十年代末的抗日战争,结束了老金的黄金时代。四十年代是各人的生活最颠簸的十年。
一九三九年初春,我们在重庆黄桷桠山上夏云瑚(《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制片人)的别墅中见了面,一夜之间在壁炉中烧掉了七八棵树根,大家都睡在炉前的地毯上。此后,他去香港,我也到了缅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回到昆明,听说他在桂林,王晋笙通过一个在电台工作的朋友,约好白天在无线电台上和他谈话半小时。
抗战结束,我以为可以从昆明的西南公路再到缅甸,但是此路不通。老金此刻住在昆明南屏戏院附近一个公寓的四楼上,我和他在这里同住了几个月,由于没有任何工作,终日悒悒寡欢。一九三九年他曾在这里拍摄过孙瑜的《长空万里》,认识一些飞行员,他们就常请他去玩、喝酒。
有一个深夜,老金一直没有回来。凌晨三时左右,人声嘈杂,四个人抬了一个周身血迹衣服撕烂的人进来,我不禁一惊。只是从衣服和轮廓上,我才认出是老金。
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三十年代,他一年就演两三部片,如今将近十年了,成日晃晃悠悠,他有不少计划、设想,他唉声叹气和我谈他的心境。这一天,几杯入肚,酒下愁肠,他感到难受,他走出屋子,看到一辆汽车,心中发狂,伸出拳头,向保险玻璃泄气,猛力一击,玻璃片片碎裂,但不掉下,他痛极缩回,比那一击更痛彻心肺,血花四溅;他往回奔走,直冲入铁丝网中。
等到人们四出找寻时,在铁丝网内看到他卧倒血泊中。
没有待完全愈合,因为一个友人的关系,我们搭乘了一架英国的运输机到了香港。
和金焰相处的日子(2)
香港,满目疮痍,市况萧条,飞机场上杂草横生,小船舶零落静寂停泊海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孤岛。但不久,英国人陆续回来了,商人回来了。我仍准备由香港搭乘海轮去仰光。但那时没有正规的船运,我的叔叔和家人二十余口为了赶着回香港,与其他乘客四百余人,搭乘一只小火轮全部葬身海底。我只好暂且住下,等候其他机会。
离开昆明之前,我们尽量把多余的东西都处理了。现在每人随身只带一只小旅行包,但老金却外带一只小铁工具箱,约莫有三十公斤重。
我们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是能工巧匠,有一刀切的斩肉高手,有抓鸡偷狗的。现在,这位“电影皇帝”,也是一位精巧的铁木匠。但在此时此地,即使他真的改行当铁木匠,也还是难以糊口。
于是,他只得蜗居于一个友人的地下室;我则回到内地另寻别路。
解放了,春回大地,举国欢腾。这时我在广州,他给我写过两封信,从字里行间看来,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怂恿我回上海,但我已确定去北京。
一九五三年,我们都参加了赴朝慰问团。他一到北京就来找我,仍是和我们第一次相识时一样,眯起眼睛,笑得像个孩子。他把一包东西塞在我手上:“给你。”我拆开纸包,叮叮当当地响起了《魂断蓝桥》的曲子。我推还给他:“不,这是你的宝贝,我不能收。”他说:“它对你来说,是愉快的纪念,因为从那时以后,你没有喝醉过,我却在你从香港走后,和杜宇又喝醉了一次,倒在小便沟里睡了几小时。”我说那个杯总是我的失败的见证。他说:“你怎能和吴大海逞英雄呢?” ——吴大海是吴永刚的绰号,那是装酒的大海。
随同酒杯包在一起的,是一包这巧铁木匠自制的多用刀——精制的木柄,可按照需要安上各种小刀和锯子,刀刃锋利无比,我至今未敢拿出来使用。
我们在慰问团中分在同一个组,我除了和摄影队研究工作之外,经常都和他在一起。我们约了几个人一同到他在平壤郊外的老家,他的老迈的妈妈身体还挺硬朗,每天都要在一架木制的机器上编织草绳,他的小妹我们已十几年没见到了,她现在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文化机关中工作,也赶来会面了。
离开他家走上大路时,金日成的汽车正开过去。美国飞机的嗡嗡声布满天空,甚至飞临屋顶,甚至脸庞清晰可辨,它也无法阻挡地面人民军队胜利的进军;它也逃不出失败的命运。
他和我谈过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抗美援朝影片的计划。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过。那时运动像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特别是文化界,而我所从事的那个小小的幻灯工作,更是几丝浪花就把你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东西湮没无踪。几年见一次面,有两次还是去华东医院见他的,谁有空闲的心情问东问西呐!在那个天愁地惨的十年浩劫中,又有谁敢串门,谁敢写信?一九七六年初,我的岳母去世,她家所有亲属都到上海奔丧,只有我没有去。那时上海正是另一批冒险家的乐园,如果到这块是非之地,看不看老朋友呢?
从那时到现在又是七八年过去了,我也只是到上海三四次,每一次都是来去匆匆,但,每一次我都去探望老金。
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中昏昏噩噩过去;五十年代又在阳谋运动中、“三面红旗”飘扬中颠颠簸簸中度过了,老金已经越过了“小生”的时代了。
有一次,一位长辈和我谈起老金,他说:“金焰怎么多年来没有看到他演的什么戏,是不是人家怕‘封建’——不敢惹他这个‘电影皇帝’,还是为了彻底打倒明星制度?!”其实,我也毫不了解,也听有人说他挑肥拣瘦,可是,他不也在《母亲》等几部片中演过一些配角的戏吗?他还演过被人们称之为“跃进片”的电影——这是一种嘲讽的提法,是和当时的形势配合的一种劣等片。
其后是面黄肌瘦的几年,等肚子好过一点时,又有什么《红楼梦》批判,又是什么假整风,大换班……事实上这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
这几年中,我很少去上海,老金也没有来北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我们一直没有谈起过。不过我早在“文革”初起时,由一些年轻演员造反派来京在审问我的时候,从口中就透露了老金的信息。
——这些老混蛋,从三十年代占住了舞台、银幕,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还想占领我们的舞台、银幕,继续放毒;现在该给他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了。
一个稚气的青年,得意地给我看一张老金、吴永刚穿着美军剩余物资的服装的照片。在他看来,这大概是一桩绝密罪证。
我最后一次看到金焰是去年的夏天,我在客厅里坐等了一刻钟,他还没有出来;我站起来踱步时,偶然从他卧室门口一看,他仍坐在床沿喘大气。我心口感到一阵不好受急忙缩回身子。大约再过十分钟,他才伛偻着身子走出来。
他每天要忍受多少次这样的痛苦啊!
如今,他是解脱了。
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他才算是“蒙主宠召”,飞升天堂。
老金,你安睡吧!现在,你不必再为睡醒后的长时间喘大气而痛苦了。如今,你是千真万确地解脱了。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和金焰相处的日子(3)
谁又在拨弄那只八音匣?! 此刻,那《魂断蓝桥》的乐曲在我听起来已不是那么悲怆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
夏家的故事
半月前,我接到一位小姑娘的信息,问我身边有没有夏公的片纸只字。你道这小姑娘是谁?
四五十年前,曾经接到三两封短笺,写什么,现在毫无印象。记得四五年前在加拿大曾收到他一封言辞恳切,情意绵长的短信。信封上的中文,是端端正正的仿宋长体字,我记得连信封也收藏起来的。但这一次为了找这封信,我采用“文革”的抄家法,半月来毫无所获。难怪当年七次抄家,专案组十年寒窗苦编,也编不出一个名堂。
一九七五年老人从秦城监狱赶出来后不久,在一次小茶会上,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等会一起走,去看我的漂亮小孙女。”如今,这小孙女已在一家出版单位工作。前年底,我抵京不久,她给我送来两本王尘无的书:“爷爷说,‘其中不少文章都是在你所编的报刊发表的’。”这位要片言只字的小姑娘便是老夏的漂亮小孙女。
说起老人之家,除了他那一辈有七八个兄姊之外,可以算是计划生育之家,他有一男一女,儿子女儿生的也都是一男一女。现在政策改变,第三代只能生育一男或一女了。
老人对他的姊姊是很尊敬的,他以八十余岁高龄,为了他姊姊的生日(另一次是什么?忘了。那时我正在上海。),他拄着拐杖去的。
我认识夏太、阿咪、大头(夏子,沈旦华的小名)的时候,是抗战后期在重庆临江门顺昌里。那时我和盛家伦、小丁住在一间约二百尺的房间,我们睡在一张六尺宽的大床,三人盖一条被,早晨把被一提便是大袋棉花。有一天夏太母、子、女三人来到,小丁正好要跟剧社远征成都。于是我们让出大床,家伦改睡写字台,我则排起四只木板椅。
一个早晨,我还睡在木板椅上未起身,阿咪拿一根竹子在石板缝处挑了一条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