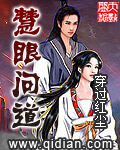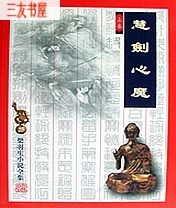生命的智慧-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凡熟悉中国武侠小说的朋友大都知道,新武侠缘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它是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写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后来又有台湾的武侠文学作家古龙入伙,于是将他们并称为“新武侠三大家”。但用新武侠,主要是为了与三四十年代的旧武侠有所区分。回眸遥望,新武侠文学已经走过了50年。而孙先生在做出版人期间,也与梁羽生和金庸两位大侠,结成了忘年之交。下面我们欢迎孙先生演讲《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开新篇——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
新武侠文学,又称新派武侠文学,这是指发韧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香港,以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流派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后来有人又将台湾武侠文学作家古龙也归入此一派别,俗称“新武侠三大家”。其实,这个归纳不大准确。梁、金二位比较接近,古龙的风格与前二者基本上不同,但因为他们三人都出现在五、六十年代,古龙其实是受到二位前辈的影响的。只是为了区别于三、四十年代的旧派武侠文学,所以就将之称作新派武侠。本文所论的则主要是以金、梁为代表的新武侠文学,但也兼及古龙的小说。
去年十一月底,梁羽生先生由移居国澳洲返香港接受岭南大学颁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校方撰写的《赞辞》中,有这么一段话:“从1954年初在《新晚报》发表的《龙虎斗京华》,到1980年在《大公报》连载的《武当一剑》,他一共写了35部小说,合计160册。其中《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已跻身武侠经典行列。”同时,《赞辞》中又引用了梁羽生先生的处女作,也是新武侠文学的第一本小说《龙虎斗京华》开篇时梁先生写的一首词《踏莎行》:
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
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五十一年前,连作者也没有想到,这一首词就拉开了新武侠文学踏足中国文坛的序幕,这一写也就让梁先生写了三十年,正应了“卅年心事凭谁诉”的词意,从《龙虎斗京华》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写就写了三十五部作品,洋洋洒洒上千万言;而金庸在一年多之后继之而起,也写作了十五部作品。一时,梁羽生、金庸在海外中国人中闻名遐尔。梁羽生的本名陈文统,金庸的本名查良镛反而不为人所知。时至今日,人们仍以“梁大侠”、“生公”及“金大侠”、“金庸先生”来习称这二位武侠文学的大师。金、梁并肩,崛起于香港岛上,成就了一番新武侠文学的名山事业,迷倒了千千万万的中文读者。流风所播,各路群雄竞起,台湾的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也连袂而来,但此三人其实都属于旧派武侠文学的写法,有别于此一路写法的古龙未出道时对金、梁二人甚为敬仰。据古龙的朋友,台湾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先生告诉笔者,在古龙六十年代崛起于台湾,渐成气候时,他收到金庸给他的复信时,有“惊喜万分”的感慨。古龙自1960年开始尝试写武侠小说,初期的《苍穹神剑》等都十分幼稚,及至1964年才以《浣花洗剑录》等声名鹊起。古龙一生写了61部武侠作品,其部数比金梁二人的著作加起来还多。笼统而言,将这三者都算作新武侠文学的话,则新派武侠文学有116部之多。此三人的武侠文学作品先在港台海外流传,后又传入内地,印数以数亿册计,又改编成电影、电视,风靡海内外,读者遍天下。曾有人说,宋人柳永以词名世,遂有:“有水井处必有人吟柳永词”之说,今则应改为:“全世界有华人居住之处,必有金庸小说在流传。”当然,当今世界已成地球村,进入IT时代,新武侠文学更以新的形式变体进入人们的娱乐、审美世界,恐怕将来飞船登天,宇航员在太空舱读新武侠小说、看新武侠电影或电视剧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举这些事例是要说明,新武侠文学已征服了海内外亿万中文读者。
然而,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中却存在着无视或歧视新武侠文学的倾向,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或文学史的研究中,也对旧派武侠文学有否定与贬低的批评,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武侠小说等一类的“通俗小说”归入批判的对象,在现代文学史上或略而不提,或横加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罪名。究其实,武侠小说在现代文坛上一问世就被人们赋以又爱又恨的角色,爱之者,喜其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济弱扶倾,着迷于其扑朔迷离的江湖恩怨,儿女情长的侠骨柔情,扣人心弦的惊险传奇;恨之者,谓其社会影响恶劣,误导青少年,鼓吹暴力,血腥残杀,冤冤相报,复仇手段残虐,更有甚者,指其怪力乱神,仙魔荒诞,盅惑年轻一代。
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2)
距梁羽生先生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已整整51年了,今年也是金庸涉足武侠文学界五十周年的纪念之年。半个世纪以来,新武侠文学已成中国当代文学百花园中的绚丽之花,有必要对之作一个回顾与评价。
武侠文学之源流
我们不妨来看看新旧武侠文学的出现、进化及其同异的发展历程。台湾武侠研究家叶洪生曾就“武侠”之称作了一个考证,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侠’与‘游侠’之称屡见不鲜,但并无‘武侠’一词。最早将‘武’、‘侠’二字相提并论,复加以必然之关联者,厥为战国时代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子·五蠹》篇有云:‘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所谓五蠹,乃特指学者、言论者、带剑者、串御者、工商者“五类分子”而言。其中“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即前法家为‘侠’所罗织的罪名,必欲去之而后快!”①(叶洪生著《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学林出版社,上海,页4。)他不同意钱穆在《释侠》一文中所断:“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的论见,而赞同汉学家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书中所说:“游侠并非属于任何特殊社群,亦不具有某种阶级成分,不过是拥有若干理想的人物而已。”将“重仁义,锄强扶弱,不求报施”列为游侠八特征之首。梁羽生先生也认为,“武侠”不在于武,而在于侠义。唐代人即认为:“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李德裕《豪侠论》) 换句话说,武侠文学作者最看重的正面人物还是有正义感之侠,而非武艺高强,但道德品行不好,为虎作伥的江湖人物,譬如金庸《书剑恩仇录》中的张召重。
自司马迁《史记》中《游侠列传》入史籍记载以来,侠士在社会中就成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它与后世的日本武士成为一个阶层又有不同,与英国等欧美国家的绿林好汉罗宾逊或西部片中剪径的、抢火车的强盗也是大有区别的。武侠者,应指那些身怀绝技,代表人间正义的义侠之士。但“武侠”这一名词并不见于中国古籍之中,反而最早出现在与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近代文学中。明治时代的小说家押川春浪(1876…1914)曾以冠以武侠之名的三部小说风行日本文坛。当时的中日之间,文化讯息传播较快,因为许多中国学人注重日本的维新成功,“武侠”之词遂传入中国。而有些中国人则也以文言文武侠小说为始作俑者,据樽本照雄等编撰的《中国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收书目,可以看出已有以武侠小说面目出现,林琴南俨然是一大家,钱基博亦为其一,他们均以文言文写作武侠小说,钱氏更与恽铁樵于1916年合编《武侠丛谈》。在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未登场前,文坛为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等霸踞,武侠小说也入于其中。
现代旧派武侠小说的异军突起
现代白话武侠小说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当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向恺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等作家为代表。向恺然《江湖奇侠传》更与刚传入中国不久的电影艺术相结合,在数十年时间内拍成十八集的《火烧红莲寺》而风靡全中国。这其实是当今流行的武侠长篇电视连续剧的滥觞。武侠小说也因此鹰扬于中国现代社会,造就出一代代的作家和读者,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
二十年代是武侠文学由文言走向白话的嬗变的时期,它与五四新文###动中的新文学一样,从文白夹杂到渐以白话文为叙事语言,从以短篇为主转向长篇,当然,在内容上仍以古代传奇为主体,以侠士为主角,可说是与宣扬新思想、新文化的五四新文###动分庭抗礼,与之争夺着读者。二十年代武侠文学成行成市,有了其职业创作的倾向,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杨尘因等都为武侠文学界一时之选,其出版物又以绣像武侠小说为其特征,这是袭自明清小说的旧衣钵。三十年代则是旧派武侠文学蔚成气候的年代,出现了一代以专职写作武侠小说的作家,可谓群雄并起,将中国武侠文学推到一个高峰,这与中国新文学在三十年代中的大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不由人不感到奇怪。当然,武侠文学有其局限性,在文学体裁上,它只占了小说界一隅,而新文学则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上百花齐放,投入新文学文阵的作家与日俱增,新秀辈出,同时他们又与家国命运、政治、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积极参与启蒙、救亡与抗日活动,因而成为文坛主流。武侠文学则免不了被讥为“鼓吹神鬼不经之说”,宣扬歪门邪道,背离现实社会,乃误导青年的坏书,与救亡的主调不免有荒腔走板的不谐调之嫌。这一代的武侠作家构成了旧武侠文学的主力,尤以北派五大家:宫白羽、郑证恩、还珠楼主、王度庐、朱贞木为其中的佼佼者。白羽的《钱镖》系列,还珠楼主的《蜀山》系列、郑证恩的《鹰爪王》系列、王度庐的《鹤剑珠龙瓶》五部曲、朱贞木的《神龙》三部曲及《边塞风云》等,各呈异彩,蔚成大观,拥有大量的读者群。
然而,随着四十年代后期的国共的政治军事斗争日益白热化,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兵祸不断,温饱、生计都成问题的民间社会中,谁还有心去读武侠小说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热情的高涨左右了文化界的动向,严峻的意识形态更蜕化为严厉的思想管制运动。在台湾,败退到台澎金马的国民党政府也以###为总动员,一切的文宣都要为此服务,武侠文学难逃其厄运,在海峡两岸都被视为毒草或不良读物,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位。留在大陆的武侠作家纷纷辍笔,还珠楼主入戏剧界服务,不敢再写武侠小说,晚年撰写了八十万言的《杜甫传》却未能付梓。宫白羽是一个最为努力上进的武侠文学家,他早年有志投身于新文###动,并曾得到鲁迅先生的鼓励,且在武侠文学界首次创造了“武林”一词,解放后却未敢再写武侠。当梁、金的武侠小说于香港双星并耀之时,香港《大公报》曾邀请其续武侠之缘,他也重作冯妇,写作了《绿林豪杰传》一书,却因为当时政治气氛所囿,全篇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放手去写,自然大失水准。他在阅读了梁羽生等的作品后,也自认自己已力不从心,故从此不再写作武侠小说。
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3)
新武侠文学的诞生及早期状况
新派武侠文学为何在香港诞生,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说其偶然,确是因为一场武术界的打擂台引起的。五十年代初,香港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与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的门派之争愈演愈烈,双方唇枪舌剑,先打了几轮“口水战”之后,未分胜负。遂依武林之旧俗,约定来个竞技,一决高下——上擂台比赛。当时的香港不准进行这类武打,只得改到澳门去比赛,结果不到五分钟,就以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的鼻子而告终。比赛之前,香港报刊大做文章,赛后人们余兴未减,依然众口喧腾,当时的《新晚报》总编罗孚遂“忽发奇想”,要他的广西老乡、平时喜欢填词作诗的陈文统马上写一篇武侠小说。吴、陈一月十七日比武,《新晚报》十九日就登出预告要连载武侠小说,陈文统被赶着鸭子上架。一月二十日,以“梁羽生”之名写作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开篇的楔子就是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首《踏莎行》。至八月初,该部长篇连载完毕。
这一篇小说以十九世纪末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历史背景,梁羽生想写一部历史的悲剧。他未曾料到,这个恍如急就章形式赶出来的武侠作品却立即成为流行小说。《新晚报》因此销量猛增,赶上了老对手《星岛晚报》。而《龙虎斗京华》居然马上成为街谈巷议、人人争读的流行小说,其锋头竟然盖过了唐人写的《金陵春梦》,颇有“到处逢人说项斯”的现象,连梁羽生的好友舒巷城也向他打听梁羽生究竟是何方神圣?而盗印本则在书未结集正式出版前就已泛滥于市场。同时,国外的中文报纸也争相转载,首先是泰国,其后是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最重要的是,在香港吹起了“武侠文学之风”。许多大报一看如此,马上跟风增加武侠小说,参与写作的人越来越多。一年多之后,金庸终在罗孚、梁羽生的动员之下初试啼声,结果一炮而红。《书剑恩仇录》为他的成名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以致时至今日,梁羽生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虽开风气之先,但金庸后来居上。可是,我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他会写武侠小说而且一定会写得好的人!”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作于一九五五年中,也是采用旧式章回体的写法,用回合,下文之前有诗词,作为开篇词用的是辛弃疾的一首词《贺新郎》。这一部长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