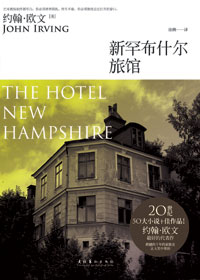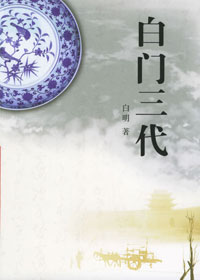白门三代-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创业导游
然而梦璋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倔强,不信邪。
几年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及广泛的市场调查,他重打鼓另开张,又轰轰烈烈地干起了一番事业,这个“事业”让他不仅对家族,而且对社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梦璋开办的京师第一家私人旅行社——北平义导员事务所。
中国正统的旅游业应该说是始于上海,二十世纪初,上海银行的总经理陈光甫首创中国旅行社,旅游之风在大江南北流行开来。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国都虽然迁了,可这些名胜古迹迁不走呀,那些著名的国立学府如北大、清华,还有像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及朝阳、民国等私立学校都是原封不动,因此相当多的官员便把家眷留在了京师,所以不管是叫“北京”也好,叫“北平”也罢,这里仍旧是历史名城、繁华都市。况且北伐战争胜利之后,市面上也出现了一段少有的太平景象。于是梦璋便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
义导员事务所先是设在六国饭店,后来因为有一位军阀在这里被人刺杀,商家们嫌此处“不干净”,于是梦璋把事务所又挪到了旧北京饭店,一住进去就是好几年。
说起来这个饭店还和八国联军有关,庚子之时这一带曾是洋人的兵营,出现了不少的饭铺、酒馆儿,外加妓院。1901年,一个叫傍喳的法国人和一个叫贝朗特的意大利人合资办起了这个饭店,起名“北京饭店”,后来这俩洋哥们儿因为利益分配不均翻了车,结果被中法实业银行给买下来了,成立了“北京饭店有限公司”,一直延续到1940年。据梦璋的笔记说,当时饭店为平房,属中式旧建筑,里边布置的是中不中洋不洋,点得都是煤油灯。
梦璋成立“事务所”时,曾得到过不少外国朋友的帮忙,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恐怕算是乔治。莫里逊了,这位英国《时代报》的著名记者酷爱照相,和梦璋有过一些往来,据说梦璋亲自做导游,帮他成就了许多关于北京名胜古迹的精彩摄影。
我小的时候还见过一本“老照片儿”,都是莫里逊送给我爷爷的作品,像明陵的石人石马啦、颐和园的西堤啦、孔庙里的牌位啦,还有什么二闸、满井儿等等,有很多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的古迹,大约有个百十来张片子。我爸将它和我爷爷的其他遗物归置在一起,从来不许别人碰,每次我都是偷着看的,所以记忆特深刻。
可是这个莫里逊名声不太好,袁世凯搞“洪宪皇帝”的时候,他曾经拍马屁帮着筹款并在《时代报》上大做文章,把袁大头的屁股给摩挲舒服了,袁世凯就把王府井大街的名儿都给改了,一度叫“莫里逊大街”。
我爸老早就把梦璋和莫里逊的通信烧光了,那照片上凡是有“老莫”的签字通通剪掉,只留着画芯儿。“文革”的时候把它藏在了天花板里,一搁就是七八年,老房子漏雨时给泡过,加上虫吃鼠咬,再把它们请下来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包“出土文物”,都快拾不起个儿啦。
然而,躲过了十年浩劫却没躲过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有位领导听说了这东西便托人向我爸“借”,说是“对开放了的北京旅游做贡献”。我爸立刻激动起来,连夜将这些照片修补好,用漂亮的蝇头小楷逐张做了说明,末了还写了份介绍我爷爷的“创业经历”,一并送上。结果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后来那个中间人实在过意不去,就以“某领导”的名义送了我爸一本新出版的字帖,我清楚地记着是一本八开的《怀素草书》。说是那位领导十分欣赏白纪元同志的书法,遂送此帖,以资鼓励。我妈战战兢兢地埋怨了一句,我爸顿时就翻了脸!说:“你们懂个屁呀,这是组织上的需要!”
可是以后一提及这件事,我爸的脸色就特难看,我敢肯定地说,他准保比吃了一盘儿苍蝇还难受。
培养人才
梦璋创业导游,是有章有法、有进有退。当时外国人也看好北京的旅游市场,于是争相抢滩。先后出现了几家国外公司,像英国的“通济隆公司”、美国的“运通公司”、日本的“观光局”等,都是很有名的,竞争自然是非常激烈。
梦璋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在京师创出了特色和名分。其一,培养人才,建立专业的导游队伍。其二,组合人力车行,大大方便了旅游交通。其三,广泛接触前清遗老遗少及宫中太监,搜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掌故奇闻,再改编成英文加以解说。把个北京的古迹名胜、宫闱逸事讲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于是在这个领域里,一提到“”便是没有不知道的。
旅游业在旧北京刚热起来的时候,社会上曾经一度游荡着不少的“野导儿”,这些人大多是饭店里的侍者,不学无术,只是会说几句洋泾浜便带着外国人瞎转悠。把民间传奇和一些道听途说串起来,再搁自己肚子里一搅和,就编出了一大堆“着三不着四”的故事,大抵这就是当时流行的导游辞儿。这种状况极大的损害了古都的形象,也未必能让游客满意。我想,西方国家多少年来对北京名胜古迹的一些“误解”,恐怕和当时这些粗制滥造、以讹传讹的“导游”有关。
梦璋认为:导游人员的文化素质以及修养,不仅决定着是弘扬还是歪曲故都文化,而且是直接影响着游客的兴趣和心情。因此,梦璋率先提出了旅游心理学的理念。在培养人才上,不墨守成规、不偷斤短两,尤其是在英语的教授方面,更是全力以赴。有人劝梦璋:“三爷,老话儿说的好,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您可得悠着点!”老爷子只是微微一笑了事。
梦璋的邻居家住着一位姓赵的后生,此人很有些心计而且十分刻苦,常在梦璋家的门口或窗跟儿底下读“洋文”,我奶奶听着觉得挺可乐,说:“这孩子嘴里一天到晚‘嘚儿不嘚儿’的,是唱给谁听呢?”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赵嘚巴儿”。
但是梦璋却没拿这事当笑话儿,而是敞开大门把他接了进来,潜心教习、恩惠有加,日后这个“赵得巴儿”便成了梦璋最得意的门生之一。这位爷的大号叫赵颐权,梦璋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于是我们家又多了一门儿亲戚,论辈分我应当叫他们三姑妈和三姑父。
还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爸带着我拜访过赵老先生,记得这位年事已高的导游界前辈,一张嘴说话就全是你从来没听过的北京历史故事,严谨之中带着幽默,听得叫人把钟点儿都忘了。
回家的路上,我爸曾捅着我的脊梁骨说:“小子,你要是有心,就应该把你爷爷他们的这些故事都记下来,将来对你会是受用无穷!”
可惜呀可惜!那时候的我不是块材料儿,把我爸的忠告和我爷爷那辈人留下这些珍贵的故事,都就着炖肉烙饼给吃啦。现在几近知天命的我,回想起这些往事,怎能用一句“后悔”了得?只好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抽自己嘴巴!
建立自己的“洋车队”
交通是开展旅游的重要工具,旧北京用于旅游的汽车少得实在是可怜,梦璋也曾尝试着用汽车来服务于他的导游业,就从某位旧军阀手里“盘”过来一辆据说是靠烧煤或木炭产生动力的破汽车。
司机是个姓张的小伙子,不仅老实能干,而且长得也帅气,特别是一身的腱子肉,很招人喜欢。于是他开着这辆破汽车,再挂上义导员事务所的牌子,每日里吱吱嘎嘎地招摇过市,曾吸引着满大街的小孩追着看热闹。
这破车抛锚是家常便饭,修巴修巴就接着走,有一回司机在修车的时候不小心把脚丫子扎伤,当晚就染上了破伤风,梦璋把他送到“德国医院”救治。怎奈当时医疗条件有限,纵然钱花扯了也是回天无力,梦璋眼瞧着一个棒小伙在床上抽搐了几日,最后一命呜呼!
人们在哭了个天昏地暗之后,开始对这个“自动化”的破玩意儿深恶痛绝。据说梦璋以后在给国外贵宾或国内大员导游时,从来拒绝汽车接送,坚持骑驴或坐人力车,可能是刺激受大了。
但是梦璋没有像他父亲白松岭那样,当年因为“雪里站”被累死就挂鞭了。
那时候市面上到处是人力车,这种车不仅租用方便,而且价位低廉,即便是跑上一整天,包金也不过两元钱。车夫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个个跑起来脚底生风,游人坐在上边可以左顾右盼,很是过瘾。于是梦璋就琢磨着把散落在饭店、路口、商肆甚至是妓院附近的人力车夫“组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旅游人力车队”。
中国的人力车是由日本引进的,所以又叫“洋车”或“东洋车”。北京是在全国最早出现人力车和最晚取消人力车的地方,据说清光绪年间老佛爷坐过的一辆铁轮子车,算是当时所有人力车的“祖宗”了。后来袁世凯当政,在中南海给自己组织了个洋车队,把铁轮子改成了胶皮轱辘。那车夫们的打扮也很有特点,穿官衣戴大檐儿帽,身披绶带外加一双雪白的手套。老远一瞧,还以为是哪儿来的督军呢,走近了一看,官衣上不挂衔儿。咳!这才知道是给大总统拉洋车的。
以后,人力车的制造业在北京曾兴旺发达,出现了不少的洋车行,如“西福星洋车行”、“东福星洋车行”、“起顺车行”、“德顺车行”、“双和顺车行”、“悦来车行”等等,人力车这种廉价的交通工具便得到了很大的普及。车厂子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京师,有名的大厂子如朝阳门大街的“马六车厂”、“繁华车厂”、崇文门外的“五福堂车厂”等,都是拥有数百辆洋车。
人力车夫是靠卖力气吃饭的,其中有失业工匠、赔光了本儿的小商小贩、被开除了的小差役、小职员,甚至还有“下岗”的警察。虽然也分个三六九等,但终归属于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靠玩儿命和出汗挣来的钱不够糊口,常常是朝夕不保。看过电影《骆驼祥子》的都知道人力车夫的苦,我这儿就不多说了。
北京出现了法国人控制的当当车(即有轨电车)之后,拉洋车的生意更是雪上加霜,于是在1929年10月的某一天,人力车夫们组织起来,把停放在天桥、前门、东单、东四、西单、西四、西直门等车站的当当车全给砸了,这就是北京历史上有名的“人力车夫暴砸电车事件”。
梦璋适时地将一些衣食无着的穷车夫们组织起来,为他们开拓新的生活出路,他的“旅游人力车队”一下子就聚集了近百人。梦璋为车夫们每人置办了一身崭新的行头,上身是白布长褂子,下身是蓝布肥腿裤,脚脖子上系着根细绑腿,足登双开脸儿的千层底黑布鞋。到了冬天,梦璋还在前门外鲜鱼口的黑猴帽店,给每位车夫定做了一顶“三块瓦”毡帽。这队伍一拉出来,嘿!倍儿精神。
梦璋又教授了人们一些简单的英语和导游常识,于是这些吃旅游饭的车夫们的收入比先前可就翻了番儿啦,个别用心的主儿,从游客手里一次就能挣几十元小费。日后,有人不断提高就做了导游,也有人通过积蓄开了自己的小买卖。这些人对梦璋恭恭敬敬,感恩戴德。
到了1934年,梦璋的导游业做得已经是红红火火、享誉京师。于是三百○三名人力车夫联名为他送上了一块硬木玻璃框的光荣匾,框内牙白色的绫子布上工整地写着“白玉三先生雅正——盛德无疆——民国二十三年古历三月初六日恭颂”。
由当时的北平市政府牵头,各大饭店的职工还赠送梦璋银牌一块,上刻“爱众乐群”四字。数百人敲锣打鼓放鞭炮,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一条街,挨着盘儿在梦璋的家门前道喜,据说这曾经是当时北京城里一个不大不小的热闹儿。
那块“盛德无疆”的牌匾一直就挂在我们家的正堂,我小的时候从幼儿园一接回家,我爸就先得按着我的脑袋,对着这块光荣匾鞠仨躬,说是给爷爷“请安”。
“文革”的时候可是就出了大麻烦啦,首先这“无疆”二字就犯了忌讳,即便是劳动人民“恭颂”的,导游怎么可以跟导师比肩?
砸了吧,舍不得。留着吧,怕惹事儿。我爸费了好大的心思才想出了个高招儿,于是把匾的内容给换了,玻璃框里的白色绫子布变成了一张大红纸,上书: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那凝聚着梦璋一生功德的“盛德无疆”,就藏在了“文革”时期这段儿最流行的“妈妈令儿”的后边,方才能够保存至今。
和太监交朋友
民国十三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派警备司令鹿钟麟“逼宫”,末代皇帝溥仪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紫禁城,先移銮醇亲王府,后来又逃到天津张园,就此清宫之中最后的一批太监也被打发了。
那时候,这些毫无生存能力的“废人”呼天抢地,与其说是哭皇上,不如说是哭自己。他们不仅断了钱粮,而且是无家可归,有的漂泊于街市,有的寄宿于破庙,有的搬到恩济庄附近的太监茔地给老辈看坟去了。
然而太监们也并非这辈子都是一无所获,甭管是以前主子赏的还是自己个儿偷的,出宫的时候每人多少也带出点家当,特别是他们还都有一肚子的宫闱故事。有人就将他们介绍给了梦璋,太监们原本是想通过梦璋帮助把自己的家当出手,换俩嚼谷钱儿,梦璋则借此机会和这些没人看得起的太监们交上了朋友。
有一段时期梦璋曾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和财力救济他们,很不为人们理解,只是梦璋自己心里有数。据我爸说他小的时候,梦璋经常提溜着几瓶“莲花白”,领着他去拜访这些太监,尤其是逢年过节。我爸说他那时候最害怕干这事儿,为什么呀?看着这些不男不女的人 得慌呗。
梦璋教育儿子要尊重他们,进门先叫“姥爷”再磕头,我爸小的时候长得白白净净,五官没挑儿,用长辈的话说就跟个江米人儿似的。这些个不长胡子的“姥爷”们也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