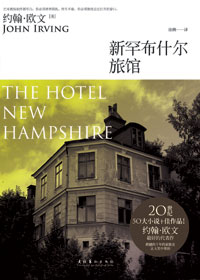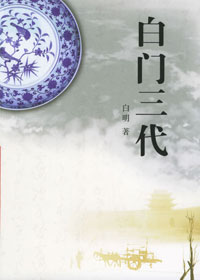白门三代-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了这两位要命的大爷。看着这箱连封条都没碰过的银子,哥俩倒头便拜,这个哭哇,用感激涕零来形容恐怕一点都不过分。
事后两人请白松岭喝酒,酒桌之上这俩大爷又喝高了,结果是“酒壮松人胆”,却津津乐道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这箱子库银是变戏法一般偷出来的!
在清朝,银库直接归户部管辖,是总汇天下财赋的要地,就跟现在央行的金库差不多。按说这里是戒备森严、层层有关,况且阅事多年、官非一人,制度不可谓不严格。可是到了晚清时期,从大小官吏到库丁差役,通同作弊。因此银库里便是盗银成风,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儿。
按规矩库丁进库必须脱光官衣换上“库服”,这种装束连裤腰带都不能有。出门的时候要从门口一条横着的板凳上跳过去,表明身上没“动静”。可这也挡不住偷呀,有人发明了“谷道藏银”的绝招儿,就是把银子塞进肛门里带出来。
然而,“谷道藏银”也绝非易事,这功夫是靠一点点练出来的。
据说先用煮熟了的小鹌鹑蛋往肛门里塞,习惯了以后,再用鸡蛋、鸭蛋、鹅蛋,讲究一“憋”就是一天一宿,没有些毅力是得不了这个“道”的。当然,也有人想投机取巧,于是东四牌楼有一家药铺就配出了一种“开谷秘方”,甭问,这药水儿一灌进去,那地方“松快”得就跟个口袋似的。但是此药水一辈子只能用一回,用多了人就“废”了。
您信不信?有人最多就能憋着一抛八十多两的“银恭”出来,回家再慢慢拉去,都快赶上特异功能啦。于是有人考证,说北京俗语中的“你偷着往外‘鼓捣’什么呢?”此“鼓捣”即彼“谷道”也。
您说这哥俩邪行不,不到一年的工夫“吃白面拉白银”,居然就能“拉”出这么一大箱子来,还假装给上边贴了个“封条”……
白松岭听罢吓得差点尿了裤子,“咕咚”一下子就给这二位爷跪下了。劝道:“这都快赶上灭门的罪啦,看在咱们仨都是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份儿上,趁着还没有东窗事发,求爷赶紧给送回去吧。当本分人过本分日子,咱半夜出门儿都不怕撞见鬼,图个心里头干净!”
这哥俩还真就被感动了一回,把白松岭搀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谢谢兄弟,我们知道深浅了。”
没过多久,有人替这哥俩给白松岭送来了一幅“帐子”,大概有点像现在的“锦旗”之类。上绣八个大字:“功等解悬,德如救溺!”反正是救人于水火的意思,只是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哥俩。
至于那箱子库银是交了还是“秘”了?就没有下文了。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灵性的牲口“雪里站”
白松岭是个勤快又精明的人,不仅活儿干得地道,就连他套的牲口都与众不同。
他有一匹大骡子,全身通白,只有四只蹄子是黑的,行里人给这牲口起了个大号叫“雪里站”。白松岭这个爱呀就别提了,人有多利索,这牲口就多利索,都快当“儿子”养了。天儿热舍不得套,天儿凉舍不得赶,只有到了啃节儿上,才舍得把“雪里站”给“请”出来。所以,凡是赶上大场面的时候,“雪里站”总是跑在最头里。快到地方了,白松岭甩出一串清脆的鞭花儿,长喝一声:“驾——喔嗬——!”
嘿,这喷口儿,就像京戏开场时的那一嗓子“闷帘儿”,明白人都知道,“角儿”要上场啦。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雪里站”被人偷跑了,白松岭急得抓了瞎,上吊的心都有。托人报了官,好在“雪里站”长相特别,很快就把案子破了,结果是被门头沟的某个矿主指使一家“驼户”(拉骆驼的)给偷的。
白松岭气不忿儿,非要把官司给打下去,朋友劝道:“门头沟矿上的人黑着呢,连下窑的煤工都是从口外诓来的。你没听说过吗?康熙爷的时候,直隶巡抚于成龙微服私访到了这儿,都被当叫花子给赶下井去过,偷你匹骡子算个屁呀……”白松岭只好作罢。
“雪里站”被找回来的时候已经受了内伤,没调养过来,不久就死了。白松岭心疼得大病了一场,从此心灰意懒,“挂鞭”不再做赶大车这行儿了,这才开始在四王府一带做别的营生,慢慢儿地、悄悄地竟发达起来。
做的是什么“营生”?是怎么“发达”的,谁也说不清。反正我们家的“发迹”好像就是从京西四王府一带开始的,这里还有过我们家几亩坟地,白松岭死后就葬在这儿。后来他的小儿子在这里连看坟带做买卖,挺有些“势力”,人称白四爷,在京西颇有一号。
被洋人看中的穷小子
白松岭生有子男四人,其中大爷、二爷、四爷叫什么?有什么“事迹”,现在都说不上来了。唯有那位三爷我最知根知底儿,他是白家后来真正的“发迹”之人,围绕着他的故事挺多的。他就是我的祖父白梦璋,字书田,号玉三。
这位三爷从总角之时起就寡言少语,但是颇有主见。白松岭四个儿子中,梦璋是他的最爱。不论是做生意,还是拜高朋访名友,梦璋从来不离白松岭左右。
某年,白松岭不知因为什么事儿,在“北堂”就是后来的西什库教堂认识了一位天主教会的英国神父,名字叫登莱普。这洋和尚一眼看中了“白把式”膝下的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登莱普就对白松岭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吧。”
白松岭一听就急了,“什么?把孩子给你,姥姥哇!我还没穷到卖孩子的份儿上。”
那神父一听乐了,说道:“密斯白,你误会了,我不是要买你的孩子。我是希望梦璋能留在我这里,一边干活一边接受教育,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孩子日后可能会出人头地。”
白松岭虽然出身贫寒,但是一谈到教育还确实让他动了心。白家在京城一无亲戚二没靠山,有这么个洋朋友帮忙,梦璋兴许能混出个模样儿来?想到这里,白松岭再回过头来看这位神父,嘿!怎么看怎么觉着面善。
“得嘞,就是他吧。”
白松岭同意了,可是要有约法三章:一得给饱饭吃。二得按时让他回家探母。三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回族穆斯林,是穆罕默德的子孙,不能强迫孩子入你们的“洋教”。
登莱普一边在胸前划着十字,一边都答应了。
就这样,白松岭把儿子梦璋送上了一条在当时京城里的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的路。
在“藤公栅栏”教堂当花童
神父把梦璋领走之后,没有安排在“北堂”做事儿,而是去了“藤公栅栏”附近的一坐小教堂。“藤公栅栏”是当时京师有名的洋人传教士墓地,大约就在现在北京百万庄一带,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就葬在这里。
这“藤公栅栏”一带满是苍松翠柏,小教堂的附近有一处挺大的花园子,专种西洋人喜爱的玫瑰花,梦璋在这里主要的工作就是摆弄这些花草。别看岁数不大,梦璋对种花可并不外行,以前白松岭做生意的时候常带梦璋去城南的崇效寺看牡丹,一来二去爷俩就学会了几手儿。
提到崇效寺的牡丹还真有些说道,这座京城里最不起眼儿的小庙,位于牛街往西的白纸坊附近。
原本是外埠商贾客死京城停厝灵柩的地方,平日里山门紧闭,鲜少游人。可一到了每年的三四月份,庙里的那十几大丛牡丹花绽开,这里就会热闹几天。庙里的老住持用煮烂了的黄豆做肥底子,养出的花不仅花期长,而且是朵朵硕大。园子虽不算宽敞,但各色杂陈。这里曾和当时法源寺的丁香、极乐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并称“南城四景”,也算是远近闻名了。
梦璋如法炮制,居然就把“藤公栅栏”里的玫瑰花儿伺候得像他这位翩翩少年一样的“鲜灵”,惹得个登莱普喜上眉梢。
以后每到时令梦璋便要领着他逛崇效寺;去比较玫瑰和牡丹谁更艳美、谁更绚丽。
逛厂甸儿,去品尝那跟铜钱一般大小的“豆馇儿糕”和足有五六尺长的冰糖葫芦。
逛白云观,去用铜子儿“打金钱眼”,抚摩那个能消灾祛病的“石猴”……
登莱普也挺大方,他带着梦璋去参观由法国传教士兼生物学家达米德开办的“百鸟堂”,那是当时京城里最早的“自然博物馆”。这里展示着上千种昆虫标本,还有风琴、自鸣钟、琉璃器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洋玩意儿”。指着这里登莱普曾神秘地跟梦璋说:“你们大清国的慈禧皇太后都悄悄到这儿来过。”
他还时不常带梦璋去前门打磨厂的“天乐茶园”看西洋电影儿,什么《克林德科学侦探案》啦,什么《爱克司光线》啦,什么《黑人吃西瓜》、《白人骑自行车赛跑》啦,等等。别看片子最长的也不过半个钟头,这可是那个时候在中国能看到最早的外国“大片儿”。
末了他领着梦璋到东交民巷里法国人开的“阿东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相”,这张照片保存了许多许多年,“文革”时才被烧掉。就这样,慢慢地两个人成了“忘年之交”。
登莱普把他送进“同文馆”
登莱普是个“中国通”,汉话说得满地道,而且凡是中国的玩意儿他都喜欢,就连梦璋嘴里的儿童歌谣都不放过,于是梦璋就教了他一段用北京西边地名编排的顺口溜:“蓝靛厂儿,四角儿方,宫门口对着六郎庄。罗锅桥怎么那么高,香山跑马好热闹。金山银山万寿山,皇上求雨黑龙潭……”
这神父居然喜欢得不得了,咿咿呀呀地跟着念,生把一个金发碧眼的半大老头子给变成了个不嫩装嫩的洋娃娃。
一天登莱普问梦璋:“我从你这里学了这么多东西,现在我该教你些什么呢?”
“我要学你们嘴里说的洋文!”梦璋不假思索地说。
登莱普答应道:“好吧,那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启蒙老师了。不过我要纠正你的说法,这不叫洋文,这是我们大不列颠的语言,叫英语。”
登莱普先把梦璋教他的那段“顺口溜”改编成英文,再一字一句地教给梦璋。于是从这段中西合璧、不伦不类的“顺口溜”开始,梦璋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己的语言天赋,几年之后,他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据说梦璋到了寂寞晚年的时候,常常独自遥望天际,叽里咕噜地说上一段英语,连他身边最得意的门生都听不太明白。问他:“老爷子,您说的这是哪一段呀?一会儿‘宫门口’一会儿‘黑龙潭’的?”梦璋淡淡一笑,从不回答。那一定是在回忆当年的登莱普。
1864年,在北京出现了当时中国第一家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叫“京师同文馆”,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培养“通事”和“译员”的地方,地点就在东堂子胡同。
原来这里规定只招收十三岁左右的满族八旗子弟,1867年,“同文馆”增设了“天文学”和“算术学”,并放宽了入学条件,三十岁以下的满、汉学子皆可入学。登莱普通过当时的英国公使维妥玛,认识了“同文馆”的一位叫鲍尔腾的英文“教习”,并把梦璋介绍了过去,并亲自当“保人”。
于是在1886年,已经是进入青年的白梦璋便夹着一个小布包走进了“同文馆”,开始接受正统的“英文教育”。登莱普还告诫他,这里多为满族达官显贵的子弟,你比不得他们,只有更加刻苦的学习日后才可能出人头地。
这话对梦璋的“刺激”非常大,他当然明白自己的身份和这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由于没钱,生活条件异常的艰苦,梦璋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一猛子就扎下去了。有人曾说,自“同文馆”成立以来,作为回族学生,白梦璋可能是第一人。
从“同文馆”学出来以后,登莱普又把梦璋接回到自己的身边,继续着两个人的忘年交。
“洋和尚”原来还是个古董商
神父登莱普,应当说是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冒险家”,他除了怀着一颗对耶稣的爱心之外,还发了疯似的爱着另外一个“上帝”——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玩。
从瓷器、字画到竹、木、牙、角等杂项,他无不精通喜好。“收藏”的玩意儿,更是车载斗量。高兴的时候他会把它们一件一件都摆出来,絮絮叨叨地、不厌其烦地给梦璋讲,讲这些宝贝有着怎样的故事,讲“追寻”这些宝贝时在他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说到唐英,他能列数出这位跨越过雍、乾两朝的清代著名“督陶官”,当年是如何为乾隆爷烧出了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讲起郎世宁,更是从他的家乡背景到绘画艺术风格,信手拈来。公平地说,他应该是个“不可多得”的鉴赏家。
登莱普博学强识,能在万马群中选良驹,垃圾堆里掏宝贝,用句行话说这叫“眼睛里不揉沙子”。于是乎日后有人就总结出了个“经验”,说这外国人呀,要么是个傻×,你蒙他什么是什么;要么就是个真行家,比谁都明白!
可不是吗,前几年我就听说过琉璃厂有个主儿,曾用一块老北京的蜂窝煤当“古董”,愣赚了洋鬼子“秃憨坠死刀勒儿”(二百美金)。但也有人拿着高仿的北魏石佛造像蒙事儿,连行里的师傅都打了眼,却被老外“一枪给毙了”。
说起来,这叫丢人现眼。可多少年来,古玩行儿的这个大千世界里,什么样的人和事儿都有。
耳濡目染识古玩
随着年龄略长,阅世稍多,加上“同文馆”里学到的一口熟练的英文,登莱普一步步地把梦璋领进了他的“古玩世界”。
登莱普接触古玩的门道非常多,从旧京师的“鬼市”到沿街“打小鼓儿”的,从琉璃厂林林总总的古玩店铺到东交民巷的外国洋行,他无所不通,无处不去,不知不觉中便让梦璋开了大眼。
“鬼市”就是半夜三更“撂地摊儿”的买卖,从晚清到民国在京师很是有名,地点可不是现在的潘家园,而是在崇文门外的“东晓市”、宣武门外的“夜市”和德胜门外的“晓市”等等。发生在“鬼市”里的故事和传奇,历来是京城街头巷尾、饭馆茶肆里人们的笑谈。
比方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