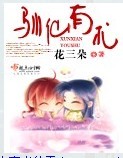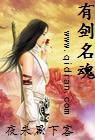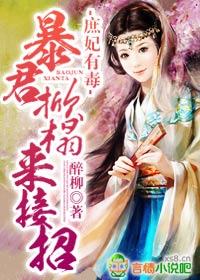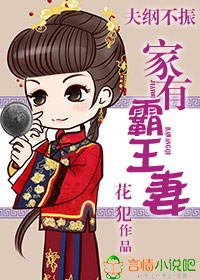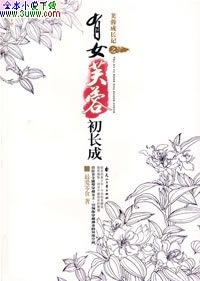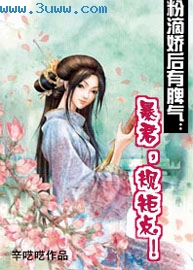���¼�ʱ��-��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㶣�̾������������������̫���ˣ������һ�ˣ���
���������Լ�����IJ�����������Ȼ�Ƿ߷߲�ƽ�ģ�������ij����ǰ���¼�֧�����ĵ������ҿ�һ�������и���͢������ز��������������ң��˿���������������������ïʢ�����������õ�Щ����ο��
������������һ�ס�̤ɯ�С��Ĺ�Թ�ʣ���д�����ٸ�˼����ˣ��Դ��������£��������ϸ�壬����Ӣ�価��÷С��֮�����¶���ع���ʧ�����˳�ĺ����ꡢ�¼�֮�飺
��������ɫ������ݺ�����ϡ���Ӣ�価��÷С��
���������˾����������ɽ������������
������Լ�������������á��⻨����㼽��ա�
������¥���������꣬�������������ݡ���
�������������糯¶�����ѿ���Ӣ����ȥ�����˳�ĺ���Ŵ����˳����������������п����˳�ĺ���Dz��ǽ�˸п��Լ�Ӣ��ĩ·����������أ�
�����������о٣���ͷ���졣����Ϊ�࣬λ���˳�����ÿһ�θɵ�ʱ�䶼��������ÿһ���������࣬��˵�С��鳼���硱�����أ���Ҳ�����ѲŰ����ͬ�¹�ϵ�����йء�
������������ʮ�£���Ԫ994�꣩���Թ��彫�����ʮ��ͷ�Ŀ��������ߣ����Ϊ��֪���£������ࣩ�������˺�����������ȡ�˿�������̫�ӵĽ��飬��������������˵��������������������ߪ�ã����澡�ġ������������겻���������������ͬ���ֵ�����ˮ���Թ�����е���ʱ���������������������ȴ�������飬�����Բ��ѣ��������˵�����ʵ�ǿ�ʶ������Թ���ʮ�ֹ��ҡͷ̾Ի������ȸ��֪���⣬���˺������콫�����࣬�������ݡ�
���������������Ҳû���ס��Ը�������ˡ�ϸ�ھ����ɰܡ���������ɣ�
����������������������������ж����ˣ��ܹ������������⡢���������С��أ�
��������
��������961��1023������ƽ�٣�������ߞ��������μ�ϣ��ˣ���̫��̫ƽ�˹����ꡡ��980����ʿ��������ʱ�o����ͬ��������ƽ���£�����������������ᣬ�ֺ����������С������������߾�����ȫ�δʡ�¼������ס���ȫ�δʲ��������ӡ�ʫԨ������һ�ס�
����
���ͣ���ɽ�࣬Խɽ��
���й���ʷ�ϣ�һ����;��˳��������Ҫ�����������кܶ࣬�������������ģ�ȴ�����ȼ��ˡ���������������֣��Ǵ��۶�ڬ����ߺ������ܴ�ü������Ȩ��ʹ�Ҳ��ÿ����ա���ȴ����ͣ�ر�����Ȩ��֮�䣻��������¼���Ҳ��˵Ҫ������ֱ�����˸߹ٲŰ��ݣ�ֱ���˼�������Ȼһֻ���кף�������ȥ����ҡ���˵���ף������϶���Ӫ��֮���������ӡ������ǹ����������ֶΣ���ʵԸ�������ߡ����Ͻݾ��������������Ǵ�ҹ��ϵ���ʿ��һ������������Ԩ������һ���DZ���ǰ�ڵ����͡�
��������ʷ�����ݴ������أ����͡����ùţ���������������ϲ�ö��飬ͨ���ټң��Ż����ˣ�����ʱ����һ����������IJ��ӣ������Ҳ�������ڽ������У����Dz�ϲ���У��ص����ݣ�����®����֮��ɽ����ʮ���㲻�����С���
�������֡�Զ��������������������ܻ��ʳ���ա��������ġ��г����ֵļֱ�������ɷ���ѣ������������ף��������ƶ���̶ȣ�ʵ��ũ������졣��������ĸ˫��������ƶ��ʳ���㡱����˵�����ڹ�ɽ�������ٶ���÷���������Լ��������Ͷ�������÷����÷�ӣ�һ��һ�ε�ȡ����������IJ����״ס��ֲ����¡�
������Ͼ����������Ͷ�����ʫ����÷����������Ϊ������Ӱ���룬��������÷��������������Ϸ��Ϊ��÷���ӡ������͵��鷨��ʫ�����輫�ߣ�����ʷ�������������飬ϲΪʫ����ʳ�Ͽ���أ�����䡱�����͵�ʫ����ӽ÷���ƣ���ɽС÷���������һ�ġ������ļţ�Ϊ��������Ϊ��ӽ÷֮���䡱��
�������ڷ�ҡ���������ռ��������С��
������Ӱ��бˮ��dz�����㸡���»ƻ衣
����˪��������͵�ۣ��۵���֪�϶ϻꣻ
������������������̴�干���𡣡�
������������һ�ס�˪�����ǡ����䲻�硶ɽС÷��Ϊ���������̣���Ҳ��ӽ÷����ʣ��㷢�Ķ������������ʡ�������ŵ���ʿ�黳��
����������˪�࣬��ҹ÷������
��������������Ū����ҡ����֦ͷ�£�
�����������������������
����Ҫ���������ͣ���Īɨ����ǰѩ����
��������ϲ��дʫ����������֮��������֮����������ϧ������Ȱ��������˺�ʫ��Ϊ�β���¼��������֮�����������͵�����������ҵ�־����ǻ����֣����ڽ�����������ʫ�������ο������������Ͼ��а�ʫ�ĺ����ߣ��������Լ�֮�����������������300��ƪ��
�������͵�ʫ�������������ˣ��������ٲ���ī�͡�����־ʿĽ���ݷá����Ͳ���������ߣ��Ծ��������Ӳ��Ե�������߿���رܡ������ڡ���Ϫ��̸�����������أ�����������ֻ�ף�����֮�����������������֮���������С������ͳ����Է�С�ۣ��������������£����ɮʫ�������������зÿ͵��һ����ͯ�������ţ��к����ˣ��ٿ����źף���һ�ᣬ���;�ҡ��С�۹���ˣ����dz��Ժ�Ϊ��Ҳ����
�������ݷ����͵����У���Ѧӳ�������������������С���ˣ�Ҳ���緶���͡�ŷ���ޡ�÷Ң�������Ĵ���ӣ���ÿ����®����̸���ն�ȥ��������һ��ͬ�ʣ�������˱��ˣ�������֮��ʫ�ʳ��ͣ����²��ٻ���֮��������筴�����һ���ͱ�ʣ���ž����������ѽ���֮��Ĵ�����
������������꣬������ɫ˭Ϊ����
������䴦�����غ����ꡣ
����������裬һ�׳�ͤĺ��
��������ȥ�������������ϱ�����·����
������ȣ�ָ���������������ʯ�����������ݻ����������Ϳͽ�ȡ���������ѵ��ͱ��ʡ�ȫ�����¿��飬����˸������龰���ڣ�����ӽ����֮���ݣ��㷢����֮������ӽ����еļ�����
�������ܸ�ի��¼����ʮ���أ�÷Ң�����˴������״ʺ�Ϊ��̾����Ҳ��֮�ģ�������һ��ӽ���Ϊ����Ļ�ڡ��ݡ�����ŷ���ۿ���ŷ�����ˣ�Ҳ�ǺȲʲ��ѣ����ڳ��ͣ�
������¶��ƽ�������á�
�����ұ����£����������
�����������������١�
�����@�ش��ۣ���ɫ�����ա�
�����ӳ�ͤ����Զ����
������Թ������ǹ����硣
�����価�滨�����ˡ�
�������ز�������ɫ�����ϡ���
��������ʿ֮��Զ���������ʵ��������Ժ�Ҳ֪���������������������ڲ���گ������ʱ���ʡ������ͳ��費����̹Ȼ�����˻ʵ۵Ķ��ͣ����Ȳ���дʫ�ʸм����ʶ��Ƶ�����Ҳ�����Ļʵ۵���ƨ�������Ժ�������˲Ƶġ��������������Ϊʫ����˵�Լ�����ϲ���ޡ������顷������������Ȱ���û��̸��߹٣�������Ȼл���������ԣ�����Ҳ����ְ��Σ��Ҳ�������������϶����У�һ���α̶����С�������Ȱ��Ȣ�����ӣ����͵���һЦ����������������־����־֮���ʣ���Ϊ���
�����������ֲ����ٻ����ʹ���������������٣�һֱ�ܵ����˳��̡������ں�����ְʱ����ΰݷ�����֮Ĺ������δ������ͬ��һʱ��Ϊ��������������8�꣬�����Ŵ��Ĵ�����������������ʫ���ϣ���ʫ����Ի����ʫ�綫Ұ���Ͻ������Ժ���������̨����У������⡣���������������ס�ɽС÷������Ϊӽ���㻳�ķ����ö���ѧϰ����������Ѫ����֮�ˣ�����;�ϼ����䣬�����������ʿ�������������������ã���Ȼʮ����Ľ������ݵ���������
������Ϊ�ѵõ��ǣ������Լ�����ʿ�������������ף����ָ��������ˡ����Ͳ�Ȣ���ӣ�����̻���Ķ�����嶡����������;�����Ľ����ϲ������������˽�ʿʱ������Ҳ��ֶ�Ӹ��ˣ������ˡ�ϲֶ嶼��ڡ�ʫһ�ף���Ϊ��ء�
������˵������ȥ��֮��Χ�����ķ�Ĺ����������ҹ��Ҳ��ʳ��������ɽ�ϵ�÷���������ؿ���������������������൵����ѡ����ش��衰�;����������ֺš����������������϶ɣ��Թ��������ݣ��ڹ�ɽ�����ʼ�����������ɽ��������Ժլ��Ĺ�ض�����Ǩ����ȴΨ�����������͵ķ�Ĺ������ʷ��֮��ʿ�����������ܹ�ע�̶���ߵ��ˡ�
����������Ȣ��������ŵ����Ϳ������Ŀ̹ǵİ��龭�����γ�����ʷҰʷ�����ء�����������ڡ�������Ѱ����˵���������������е�Ĺ����Ϊ�����Ǵ���ʿ�������������ᱦ��������ڿ����͵ķ�Ĺ����ֻ�ҵ�һ�������һ֧��������ʧ��������������֧СС�����������˺��˵�������ʡ��²�����롣
��������������һ�ס�����˼������Ů�ӵĿ����������飬�����ػ�������һӽ��̾���������������˶��ˡ�ȫ�����£�
��������ɽ�࣬Խɽ�ࡣ
����������ɽ���ӭ��
����˭֪����飿
��������ӯ�����ӯ��
������ͬ�Ľ�δ�ɣ�
�������߳���ƽ����
�������������y�����ġ����ڴʻ����������������͡�÷���ӣ��ɳ�ǧ�Ÿ߷��ӡ���˵���ס�����˼�������εȷ��£�����һ����ڪ���������Ү����
�������ڽ��˿�������ϵ����Ĺ�еĴ������������ͼ��������������˵ġ�����˼��ʱ����Ų����ǡ�����һ�����գ�������ȷʵ������һ�Ρ���ͬ�Ľ�δ�ɡ����������飬�š���������Ϊˮ����ȴ��ɽ�����ơ�����־��Ȣ�����±��������˵������������Ȫ�ӣ�
��������
�������ͣ�967һ1028�����־���������Ǯ���ˡ����Ӻ���������ɽ����÷���ף��������ˣ�Ҳ����Ȣ�����˳�֮Ϊ��÷���ӡ�����ʥ�����䣬���ڴ��֡��;������������¼�����ʷ�������������ԡ������������������������д������������飬ϲΪʫ����ʫ���Զ���С��ֺ;�ʫ�����ľ��������š�һ������ȫ�δʡ�¼������ס�
����
���������Ӵ��ˣ����ǰ�������
���˽�֪�������δʴ�ң����ij������������ڵ�ʱ��������Ϊ�����Ͽɣ����ʮ�ֿ�������Ϊ�˷ŵ���������ʵ��������˵�ʫ�ʼ���û�й������IJ��ϣ�����ʷ��û��Ϊ����������ֻ��ͨ��һЩҰʷ���˽������¼�������Щ���ǵļ��أ�Ҳ�Ǹ��鴫����ǡ�֧������ġ�
�����������п��ţ�Ϊ�˷��ţ��ɹ����£��˳ơ�������һ֦�ʡ�����������������ǣ���������¥��Ժ���˻죬�˵ò�����������¼�������أ����̷��ֹ�ÿ����ǻ��������Ϊ�ǣ�ʼ����������������һʱ�������������ˡ�ѧ�������ˡ����뷨һ������Ҳ�����μӿƾٿ��ԡ���һ���������������ں�����ʫ���������������ˣ�ʱ���־��ꡣ��
����5���ڶ��ο��ƣ�����û�п��ϡ��Կ�һ����������������������ϹҲ�ס�ˣ����ߡ����֮��һ��������д�����������ġ��׳��졷��
�������ƽ���ϣ�żʧ��ͷ����
�������������ͣ������
����δ����Ʊ㣬��������
���������۵�ɥ��
�������Ӵ��ˣ����ǰ������ࡣ
�����̻���İ����Լ�������ϡ�
�������������ˣ���Ѱ�á�
���������˺����䣬�����¡�ƽ������
�����ഺ��һ�á�
�����̰Ѹ���������dz��ͳ�����
������ɧ����ɧ�����Ի��ü������������ֲμ��˳�͢�ĵ����δ���ʱ�����������ʮ�ˣ��ʵ�Ҳ�Ѿ��������Ժ㻻�����������ˡ�
�����⡰������ˡ���������������İ���ʿ��������緶���͡�˾���⡢���⡢�ն��¡�ŷ��������˲ţ����������������������������쵼�����ݵ�����������š��ѶϽ�����ջ������������һǬ�����ķ���ʫ��Ҳ�ݵ��˴��Ƕ��Լ�������Ůɫ���ļ���ָ�𣬻��ݵ��˰�������ʥּ����ĭ�����Լ����ϵ���Ϊ��ȴ��֪Ϊ�Σ�ƫƫ�������Ǿ䡰�̰Ѹ���������dz��ͳ��������������������������Ŀ��Ծ��ӣ�����˼�������־���������ȥdz��ͳ�����Ҫ���������������һ�ӣ��Ͱ����������ˡ�¼ȡ����һ���������˷׳�Ц���������Ӵ��ˣ��������ࡱ������ȥdz��ͳ�����Ҫ��������ҭ����������˵��������
�������������˾٣������������ܸ�ի��¼��˵�ǡ��������ţ�����������⸡������֮�ġ�����ϲ������֮�ʣ���ϲ�������о��ŵ������Ҳ²⣬��Ī������������ͷ̫�����ǹ��ʵۡ��ǵĻ��գ���ʱ���������ֿ��ȣ���Ͼ�ձ��μ˹ݣ����������߰����д��������ƹ�����һ��Ʒ�⣬����ʮ����������Ƕ������÷���Ժ��˳�����ǣ�����Ը�����٣�Ը�����߽У���Ըǧ�ƽ�Ը�������ģ���Ը���ɼ���Ըʶ�����档�����Ĵ�Զ�������ȹ���Ҳ���빬�У���ʦ������ɽʫ�����ƣ����������ζ����ϱ���������ָ�������ӽ֮���촫���С������ĺ���ʣ�ÿ�Ծƣ���ʹ�̴Ӹ�֮���������������϶�����ϲ����˳���˵�������е�Դף��������գ�������֮�£�Ī������������֮����Ī����������С��������������ͷ�ʣ�����οƾٿ��ԣ��˻�����һ��Ҳδ��֪����Ȼ�����������ԡ�С��֮�ĶȾ���֮�����Ķ�㣬��������ġ�
������������һ��ʧ������֮��ͻȻ���������Ц����ȥ���ұ����ǿ����������ǡ�����ּ��������䡱��������̥��������ʶ����糤�����ݽ�Ƭ�����ѳ�����м���˳������Ҳ����˸��������������¡���������ռ�ʳ������ǰ������ࡱ���˴�����ү��������ү�������������Ӵ˳�������;˵byebye��������¥���ݣ���Լ������Ϊ潹ݾ�¥��ǻ��������Ը�������ﳤ�������ѣ�
�����������Ͼ����������ŵڣ��游�������ֵܶ�����ѧ��ʿ����ͥ�������ˣ���������ϣ����ѧ�������գ���������ҡ��ġ�Ϊ�˸ı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