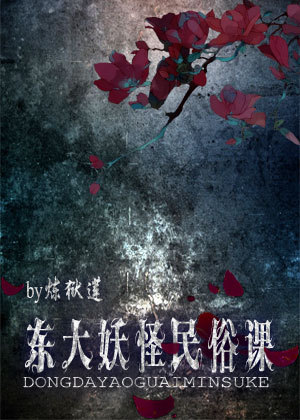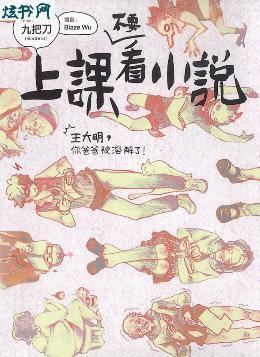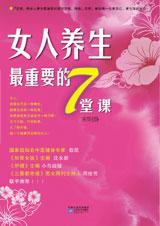沉思课-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分别询问四个人今天街上发生了什么,得到的回答会各不相同。一个刚从列文斯顿酒店的扶轮社 午餐会归来的商人会说:“ ‘戴夫尼’那边挤着好多人,那家伙很会促销。”
年长的教师会说:“哦,有件好事!戴夫尼先生的外甥乔治现在在店里做工呢。”
十几岁的女孩会告诉你:“戴夫尼在促销,真棒!”
而十几岁的男孩答道:“哇,你看见从戴夫尼的店里出来的那些姑娘没?”
这四个人都陈述了自己所看到的;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各自感兴趣的方面。
等我们经过沉思的训练,学会对欲望加以控制,将注意力引导向我们希望注意的对象上,这时候,世界在我们眼中就会显得跟原来很不一样。我们将日益清晰地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的视线将不再受制于强迫性的吸引。我们不仅能更清楚地看见事物的色彩、质地、形状,还能觉察到眼前的对象及情势中的和谐与秩序——觉察到人类对于和谐与秩序的可悲违反也未可知。总之,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会经历显著的变化,十九世纪孟加拉的神秘主义者室利?罗摩克里希那称之为长出“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
英国神秘主义者托马斯?特拉赫恩 曾以勃发的激情,将一个睁开双眼的人所见到的神奇景象形诸笔墨:
街道上的粉尘和石块像金子般珍贵……放眼望去,大门内的树木郁郁葱葱,使我陶醉狂喜;它们的甜香、它们难得一见的美丽,都让我的心脏怦怦直跳……男孩女孩们在街上翻滚嬉戏,搬金挪玉……日光昭示着永恒,眼前的一切都蕴涵无限。
因此,注意力是极其宝贵的官能。我们的运用方式也至关重要,因为但凡注意力所及之处,无论善恶,都会勃发出生机。假如某人在公众聚会上迟到,别人都转头注视,那么骚动就会放大——这是众人的注意力使然。如果大家的注意都能集中在主讲人身上,那么迟到者引发的喧哗就会降到最低。同样的道理,假设有人失手掉了一个玻璃盘子,那么停下手里的活盯着它看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各位不要在沉思中和干扰对抗的原因。那样就等于把注意力和精力分给了它们,它们将因此膨胀,变得更加难以驱逐。
非随意注意
我们偶尔会发现几个天赋异秉的人,他们天生就能做到专一,根本不必下工夫接受大多数人必须接受的感观训练。这非常好,能省下许多力气,但其中可能有一个潜在的缺点。这样的人,他的心灵或许会对感兴趣的事物充满热情,全情投入,就算在必须放手时也无法脱身。身为教育者,我不由想到了那些沉湎于古代苏美尔文明或塞缪尔?佩皮斯 晚年日记的教授们。他们不管走到哪里心中都装着学术,专一是专一,但不能收放自如,于是在人际交往方面一团糟,小灾小祸也时常拜访。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故事有许多,尽管我不确定它们是否都能得到证实。据说,他有一次收到了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那样一张支票正好用来做书签,他也的确把它当成书签用了,结果还是一位图书管理员在归还的书中发现了它。有一次,有人问他是否吃过了午饭,他答道:“我这是在往哪个方向走?如果是往家的方向,那就没吃过;如果是在来的路上,那就吃过了。”还有一次,一个路人看见他的外套下肩膀的位置有个巨大的肿块,原来是他穿外套时忘记把衣架拿走了。
爱因斯坦对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些沉浸于研究的逸事在我们看来纯粹好笑,无伤大雅。但如果换了别人,后果可能就严重了。我记得读到过一个男人和几个朋友一起从卡梅儿开车回家的故事,男人在半路上发觉照相机忘在了沙滩上。于是他掉转车头往回疾驶。这时候,他的心灵完全聚焦在照相机上,他一定得把它拿回来——悲剧发生了,他在车祸中送了性命。因此,在训练自己专注于一点时,我们应该同时加强自己的鉴别力和意志力,这样才能知道把注意力放在哪里,以及在必要时如何转移。
一次注意一件事
假如我们的确心灵涣散(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那么该如何养成专一这种可贵的品质呢?第一步就是有步骤地进行沉思练习,那是学会专一技巧的绝佳途径。此外,还有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即避免在同一时刻做一件以上的事;同时着手几项工作的习惯要彻底抛弃。
这一点我在十几岁的时就已经深有体会。当时,我的叔叔(也是我的英文老师)刚向我介绍了华盛顿?欧文 ,我也读了伊奇博德?克瑞恩 被自己的想象吓得半死的故事。一天,我刚读《瑞普?凡?温克》 读了一半,早饭时间到了。我带着书,在盛着米粉蛋糕和椰子酸辣酱的盘子边上坐了下来,然后一边心不在焉地咀嚼蛋糕,一边读着可怜的瑞普从长眠中醒转返家,村里的儿童前来相迎的情节。蛋糕是我祖母抱着极大的爱心制作的,她悄悄走了过来,将我的盘子轻轻抽走。当时我沉浸在书中,食而不知其味,有那么一会儿,想必还把一只空空的手举到了嘴边,因为我听见祖母说:“你的手里可什么都没有哦。”我低头去看盘子……盘子不见了!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这叫书也读不好,饭也吃不好。”后来,我学会了在华盛顿?欧文和米粉蛋糕之间拉开点距离。
要在地球的这一边目睹同样的景象,只需造访一次旧金山金融区的蒙哥马利大街即可。
看看那些今天的金融家和未来的大亨们,他们最喜爱的午餐不是凯撒色拉,不是三层三明治,而是一大份《华尔街日报》。他们的餐盘上盛着食物,可注意力却完全集中在股票指数上,他们吃下去的其实也是这个。当然了,你还可以在饮水机边、快餐店中、咖啡屋里见到同样的情景——只是人们手中的报纸不尽相同而已。
诸位可能认识这样的人:即便是在跟家人或朋友一起用餐时,他也要分神去读书读报。这么做显得有欠妥当,因为这样会把别人挡在外面。实际上,我还见过几个故意把报纸像盾牌一样竖在面前的人,他们躲在报纸后面,不用看见别人,也不被人看见,不用跟人交谈,也不会被人搭讪。但对那些爱你的人来说,相比“红眼航班飞明尼阿波利斯省73美元”的整版广告,他们不是更愿意看到你的面容吗(尽管某几天早晨你愁眉苦脸的)?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专一和学习
在任何一所大学的食堂走上一圈,你就会发现,学生们都在同时参与几项活动。其中有一位可能正念着一本教科书,同时还在喝着一杯咖啡、听着音乐,每过几分钟还要抬头看看有谁走过身边——这些都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这种现象不限于某个学生,所有学生都在这么干。心灵的力量被完全分散了,让人专心致志、乐在其中的事已经没有了。我甚至还见过一场杂耍表演:有个年轻人一边叼着根香烟(快要掉了),一边从杯子里啜饮咖啡!
有些学生会买一大袋子薯片,在房间里边学习边吃:读一两句,吃一点;读一两句,再吃一点。由于课文中的逻辑被不时打断,他们只得时不时地回头重读。他们在清空薯片袋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却在掌握课文上进展甚微。我得承认,我也见过有些教师以同样的方式分割注意力:他们将一大摞学生作业带入会议室,一边开会一边批改。还有些老师在办公室里边读书边听收音机,而他们本该在这时候向学生们示范如何当一个负责的教师。
蓄意分割注意力的人都了解,要纯熟掌握某事会比较困难。学习需要专注,这个道理还不够清楚吗?真正聪明的学生自然而然地会明白这一点。当他坐定身子开始阅读,准备边读边喝的咖啡会渐渐变冷;烟灰缸上搁着的香烟会冒着青烟自行燃尽——这也是它最好的结局;如果边上放着音乐,他也会充耳不闻。这样的学生是一心一意的,对环境是不知不晓的。就算触碰他们的身体,叫他们的名字,他们或许都不会觉察。
你可能还记得毛姆 的小说《刀锋》中的男主人公拉里。小说的叙述者告诉我们,一天早晨,他走进俱乐部的图书馆时见到了拉里,拉里正坐在那里专心地读书。他离开图书馆时已近黄昏,拉里仍然坐在原处,全神贯注,连坐姿都没有变。这显然是一位天赋出众的人,参与任何活动都能出人头地。读着读着,我们发现,只有灵性的苏醒才能让拉里觉得满足,后来,他以惊人的专一开始了对目标的探寻。
专一和享受
凡是热衷艺术的人都会谨慎地避免分散注意力和一次干两件事。就拿音乐爱好者来说吧。多数人都说自己热爱音乐,但这件事不能听其言,而要观其行。真正的爱乐者在聆听音乐时会本能地闭上双眼,因为他们不容自己的意识有分毫闪失。要是坐在音乐会上不停地左顾右盼,你的意识就会涣散;要我说,你这不仅是在听音乐,还是在看电影。
另一方面,我曾在书店和阅览室里听见音乐。这样的场所应该彻底安静。出于对所读书籍的尊重,应该保持安静;就算出于对音乐的尊重,也该保持安静。这类场所使用背景音乐的初衷是使人放松。音乐或许是能使人放松,但阅读时无此必要。佛陀用他一贯朴实的语言对此做了总结:“行走时行走。站立时站立。坐下时端坐,别摇晃。”
我以前去看过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剧是上文提到的叔叔在我念中学时介绍给我的。演出一开始,我就完全沉浸其中。男女演员都很出色,他们的仪态,以及剧中的语言和动作之美,无不强烈地触动了我。
接着就到了观众无不为之感动的阳台对话。无论你是多么心灰意懒或铁石心肠,这一幕都会将你带回感情仍旧鲜活的那些苦涩而甜蜜的岁月。朱丽叶走上了阳台;罗密欧伫立在下方,因为期待而呼吸急促。“嘘,轻点!那边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演到这里,剧场一片寂静。
接着我听到一句“麻烦你,糖在哪儿”?我对莎剧算是相当了解,可“麻烦你,糖在哪儿”还真没读到过。我心说一定是读过而忘记了,或者他们演的版本和我熟悉的那个不一样。可能是朱丽叶想要考验罗密欧的诚意吧——想追她就得带糖。
可那句台词又被急切地重复了几遍——“快点快点,糖在哪儿?”朱丽叶的心思还真是奇怪!突然之间,我觉察到了台词里的加州口音——原来是坐在我旁边的两个女中学生正和两位主角抢戏。她们正应了我祖母的评价:这两位姑娘是莎剧也看不好,糖也吃不好。
凡爱上帝者必能全神贯注,历代圣人和智者的行传已经证明了这点。在祈祷、敬拜、深入沉思时,他们的注意力都会彻底铆在受人爱戴的神明身上,没什么能强行让他们分神。即便仅仅是对神圣者的暗示——一个圣名、一座祭坛、一处遗迹、一个让人联想到上帝化身的站姿——都会将他们引向更高的意识状态。据说曾有个意大利神秘主义者在安放圣衣和祭器的收藏室里藏了一小本笑话集,好在做弥撒时保持一定的世俗性,让听众能理解他的布道。
我们还读到过一则室利?罗摩克里希那的故事:一次,他去看门徒吉里什?高斯制作的宗教剧。他很喜欢高斯,也很喜欢这剧目,于是就坐在了戏院前排。大幕拉开,一个角色唱起了主的赞美诗。室利?罗摩克里希那旋即进入了意识的高层状态:舞台消失,演员退散。这个当口,他做了件只有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才能办到的事——他抗议道:“主啊,我来这里是为了看我的门徒制作的戏剧,您却让我进入狂喜。我可不想这样!”接着,他就一遍遍重复着:“钱,钱,钱,钱……”好借此维持对于世俗的觉知。
对我们多数人而言,问题恰恰相反:我们的专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然而,通过按“一次做一件事”的原则勤加修习,我们可以学会让专注增加。学习时将自己完全交给书本,看电影时将精力完全集中在影片上;不要吃爆米花,也不要和人交谈。听音乐时要仔细听、单独听。这样就能从这些活动中得到更大的收益;而你的沉思也会愈发成功。
我相信,在工作中混进外来的事物,效果一定是负面的——它对我们自身、我们的雇员、我们的工作,都会带来妨害。充分调动现有的一切是启动深层资源的唯一方法。在工作时吃零食、看杂志、听音乐、聊八卦、填字谜、画星图,这些都会使我们的精神力量分散或者削弱。过去形成的反射让我们觉得分散的心灵比较高效,但如果真能将心灵联成一片,我们会明白,专注养成效率,分散导致低效、错误和紧张。
专一和安全
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专注一点都能防止错误,并避免代价高昂的事故。在厨房或商店里使用强大的工具和危险的器具时,你得对手头的工作保持全神贯注,才能确保绝对安全。我是故意用“绝对”两字的,就安全而言,我觉得应该力争这一点,丝毫马虎不得。单单做到“这看起来挺安全的”或“我看能行”是不够的。一旦涉及自己或他人的人身安全,我们就需要确立更高的标准。
让无益的干扰降低安全性是多么不值得啊(比如轰鸣的收音机声或无关紧要的交谈)。以厨房为例,试想你正操着格外锋利的刀子在厨房切菜,这时候可以讨论谁会赢得今年的奥斯卡奖吗?如果一定要谈论本年度最佳影片的问题,那就把刀子放下,在引起别人的充分注意之后,再投下你的选票。
同样的道理,操作电锯或旋转碎土机之类性能强劲的机器时,也不能让自己的注意力从机器上挪开,哪怕一瞬间都不行。如果有人进入工作区域和你说话,那就让他先等一等,等你的工作告一段落、可以关掉机器或把手和身体从危险区域移开时再去交谈。希望各位都能明白,这是守礼的表现;假如突然转身、亮出断手,那就显得无礼了。
接近那些正在操控机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