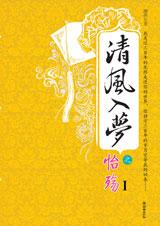丁庄梦-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转身拖着玲玲走掉了。
这时候,校院里的热病们,赵秀芹,丁跃进、贾根柱、赵德全,七七八八的人,八八九九的人,都觉得事情不该是这样。一场大戏不该这样简简单单收了场,就都追望着堂叔拖着玲玲穿过校院子,跨过大门消失掉,都还站在原处儿,如同没有明白发生了啥儿事,都还站在原处儿。
就都那么木呆着。
呆站着。
无所事地呆站着。
月亮偏西了。
想起我叔来。想起贼欢该是两个人,女的走去了,还有一个男的哩。便都扭回头。便都看见我叔不知啥时从屋里走出来,衣服穿得齐齐整整着,连袄脖子的扣都严实实地扣结着,坐在仓屋门的门槛上,低着头,像进不了家的孩娃样坐在门槛上,把两条胳膊垂在两个膝盖上。垂挂着手。吊挂着他的胳膊垂着手,像进不了家的孩娃一样坐在门槛上,有些饿头就无力搭下去。
人都扭头望着我二叔,望着爷。等着看我爷、我叔下一步会做啥儿事。
我爷就上前做了事。上前猛地抬起腿,不由分说在我叔身上踢一脚:“还不快回屋,想在这丢人丢死呀。”
我叔便起身往着屋里走。路过人群时,他脸上竟然有了笑。挂了挤出来的笑,瞅着庄人们,淡淡笑着说:“让你们笑话了——让你们笑话了——求大家千万别让我媳妇知道啊。快死的人,我还做最怕媳妇知道的事。”
走了老远的路,还又回头交待着唤:“求你们,千万别让我媳妇知道啊。”
丁跃进和贾根柱去找了我爷爷。谋合着去找我爷说了一桩让人意外的事。
日头还是和往日一样儿出,一样儿暖,一样儿在日升几杆时,把平原上冬末的寒气驱赶掉,把暖气铺散撒落在学校里。校园里,那些杨树、泡桐都含着绿色了。春天像露珠样挂在了树枝上。杨树上绒黑绒红的樱穗已经吊在了半空里,似乎咋儿白天还没有,经了一夜我叔和玲玲贼欢的事,春天就来了,杨树上就挂着绒穗了。桐树就挂着葡萄似的一吊一吊的桐铃了。有一股清新已经开始从那树上生出来,散发着,淡淡地在那校园里走,在那院里飘。校园的围墙是砖墙,可那砖缝里落了土,这时候,就有嫩绿的草芽从那砖缝生出来,挤出来,金黄色,嫩黄色,透明地亮,越过草叶望过去,看见日光金澄澄的青,和金箔儿在水里发光样。春天就来了,悄无声息地来。因为校园里有了贼欢的事,它就首先来到了校院里,让校院冬浑的气息里,有了清新的铺散和流动。人都睡着了,捉了一夜奸,都累了,待日头从丁庄漫过来,丁庄没病的人都起床把猪窝、鸡窝的门打开,让鸡、猪又开始了一天的新日子。可是天色大亮时,有病的热病人们也才刚睡到梦里去。
鼾声才在屋子里响。
说梦话的人,也还没有说上几句话,贾根柱和丁跃进却已经醒了来。他们是睡在一个屋,在学校教室的二层上。在二层靠东一间教室里。贾根柱就睡在窗下边。日光像金水儿样越过窗子流在他的被子上,流在他脸上。暖气把他叫醒了。睁开眼,怔一下,起身朝窗外看了看。看了看,慌忙到对面床上去唤丁跃进。不是唤,是摇了一下子,跃进一个惊怍就从床上翻身坐起来。
愣一愣,跃进想起了事,就和根柱从屋里出来了。下了楼,径直朝校门口的屋里走。径直到我爷的屋前爬在窗上看了看,又径直到门口敲了门。刚一敲,身后就有应声了。我叔睡得死,他累了,睡得死了样,经了那么大的事,好像他累了,昨夜儿在屋里和我爷争了几句他就睡着了。和我爷轻声吵了几句他就睡着了。我爷说:“亮啊——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这么不要脸。”
我叔不吭声,
我爷说:“你这么不争气、不要脸,你会不得善终、不得好死你知道不知道?”
我叔说:“不得好死又怎样?反正就是死在这热病嘛。”
我爷说:“你能对起婷婷吗?”
我叔说:“婷婷和我结婚以前就有过男人啦,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对不起我的话。”
我爷说:“你对待起你孩娃小军吗?”
我叔说:“爹,瞌睡了,我睡啦。”
我爷说:“你也睡得着?”
我叔不说话,努着力儿要睡着。
我爷说:“婷婷她娘儿俩知道咋办呀?”
我叔翻个身:“她怎么会知道?”问着话,他就果然睡着了,鼾声细细地响,很快也就睡实了。有了贼欢的事,有了动动荡荡被人捉奸的事,他像走过了多远的路,筋疲力尽了,很快睡着了。
我爷睡不着,恨我叔,愁我叔。睡不着,他就独自在屋里床头上坐,听着我叔那长短不一的浑乎乎的鼾,恨不得起床把他活活地掐死在床上。想着掐,却是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只是在那床上枯枯地坐。枯坐着,围了被,衣裳没有脱。枯坐着,想了很多的事,又如啥儿也没想,脑子里嗡嗡啦啦响到后半夜,又直到天亮都是一片野荒的白。野荒茫茫的白。恨我叔,又恨将不起来;怜着他,又怜将不起来。待窗口泛青后,眼皮儿硬,又没有瞌睡在眼上,爷就起床朝着门外走,路过我叔的床前时,想弯腰一把掐死了他。弯下腰,却是把他掉在床下的被角朝上撩了撩,把他露着的肩膀盖上了。那肩膀上还有新起的热病疮痘儿,红红的,四五个,像在水里泡过的碗豆一样胀大着。
爷立在床边上,细看一会叔的疮痘出门了。
摸了摸叔的疮痘出门了。
在校外的田头和地边,走走站站回来了。
回来看见丁跃进和贾根柱在敲他的门,他从他们后边走过来,哀求求地问:“跃进、根柱,有事呀?”
意外的事,就从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得如日头从西边出来东边落下样。如平原上睡了一夜平地里起了一座高山样。如枯干百年的黄河古道又有了满河流水样。冬末初春的季节里,有了满地六月才熟的小麦样。丁跃进去敲门的手在半空僵了僵,他和根柱同时扭回头,看见我爷立在他们身后边,三尺的远,脸上挂满了累,眼里的红丝和蛛网一模样。他们彼此就看着,静静地看,默了好一会。
跃进脸上挂了淡淡的笑,说:“叔,你一夜没睡吧?”
我爷苦笑一下说:“不瞌睡。”
贾根柱就望望丁跃进,彼此对了眼,扭头望着我爷说:“丁老师,我俩想和你商量一个事。”
我爷说:“有事就说吧。”
根柱瞟瞟大门口:“到那儿说。”
我爷说:“在哪都一样。”
跃进说:“别把丁亮吵醒了。”
他们就退到学校大门里侧的边角上,站在一座房的山墙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根柱瞅着丁跃进,说:“你说吧。”
跃进又瞅着贾根柱:“还是你说吧。”
根柱就把目光搭在我爷的脸上一会儿,先把双唇闭成一条线,后又用舌头舔舔嘴唇说:
“丁老师,我和跃进都是活不了几天的人,想来想去有桩儿事不该满着你。”
我爷就又瞟着他们俩。
根柱笑了笑:“丁亮和玲玲是我和跃进锁进屋里的。”
我爷的脸色有些变。有些青,有些白,望着他们的目光又有些茫。荒野上的茫。抓捞不住后人要从半空掉在地上的惊慌慌的茫。最后把目光落在丁跃进的脸上时,爷以为跃进会有些欠疚地把头低下去,可跃进却是抬着头,和贾根柱刚才一样脸上挂着笑。挂着和我叔脸上常有的那种赖色的笑。挂着笑,望着我爷闭着嘴,不说话,像他俩要从我爷脸上看出啥儿样。
爷就有些惊奇地望着他们俩。
根柱就开口:“实说了吧,是我俩锁了门后让人把钥匙送给了玲玲男人的。”
跃进说:“根柱还想给丁亮的媳妇婷婷送一把钥匙去,是我把他拦住了。”
根柱瞟瞟跃进道:“主要是念起丁老师教过我,不是念起丁亮有啥好。”
跃进说:“叔,还有桩事要和你商量一下子。”
根柱说:“丁老师,我俩知道丁亮和玲玲贼欢的事你是最怕他媳妇婷婷知道呢。”
跃进说:“所以就来和你商量这桩儿事。”
根柱说:“也不是啥儿大不了的事。”
跃进说:“对你没啥儿不好的,你只要答应就行了。”
根柱说:“一答应就天下泰平了。”
我爷说:“有啥事,你俩就说吧。”
跃进说:“根柱,还是你说吧。”
根柱说:“谁说都一样。”
跃进说:“你说吧。”
根柱说:“那我就说啦”,扭过头,望着我爷道:“丁老师,听了你可别生气,我俩是为了怕你生气才和你说的,才来和你商量的。想着你是明白人,才来和你商量的。要是换了庄里的第二个人,就是李三仁他还活在庄子里,还是丁庄的村长兼支书,支书兼村长,我和跃进说做就做了,说干就干了,压根儿不会和他商量的。”
我爷说:“你们俩——到底啥事吗?”
根柱说:“就是学校里的事,你以后啥也别管了。病人的事,也一点别管了。这些都由我和跃进管着了。”
跃进说:“叔,直说吧。就是让你把我俩当成校长看,当成这一堆热病们的领导看,当成庄里的村长、支书看,我俩以后说啥你听啥。只要你听了,热病们就没有谁会不听我俩的话。”
我爷笑一下。哑然地笑一下:“就说这?”
“就说这。”根柱板着脸:“你得把热病病人们集中起来说一下,宣布以后学校里的事都归我俩来管了,政府照顾的东西归着我俩来管了。听说丁辉手里有一枚村委会的章,你得把庄里的公章从丁辉手里要出来,那章以后也归着我俩来管了,就当我俩一个是村长、一个是庄里的支书就行了。”
我爷就望着他俩不说话。
跃进说:“让你宣布一下就行了。”
根柱说:“你不出面宣布我俩就把丁亮的事告诉宋婷婷。告诉了婷婷你们家的日子就乱了,就要家破人亡了。”
跃进说:“叔,由我俩来管病人、来管住庄里的事没有啥儿不好的。”
根柱说:“保证比你管得好。——我们都知道,你大儿子丁辉把上边照顾给我们的棺材卖掉了。听说他要再挣些钱后就搬家,不搬到东京就搬到城里去。你家老二丁亮不光和人有这贼欢的事,还是和自己的弟媳妇,你说你再管这庄里的事、学校里的事,咋还合适呢?”
跃进说:“叔——不让你管是为了你好呢,为了你们一家人的好。”
根柱说:“你要不同意我俩就把丁辉和玲玲被人捉奸的事去说给婷婷听,那时候你们家的日子就乱了,就要提前家破人亡了。”
他们俩,一递一句地说,同双簧戏一样。和马香林唱的坠子样。我爷就在那儿看,就在那儿听。日光晒在他脸上,使他的脸有了发光的白。苍白着,竟有细密一层汗珠挂在那脸上,像水洗了一样挂在他脸上。忽然间,爷已经很老了,头上的花发也差不多全白了。银晃晃的白,立在山墙下,他的头像是城里卖的飘摇在半空的白色汽球儿,要不是有那脖子的牵,也许他的头会荡在半空里,会在荡着中,猛地掉在学校的大门里。爷像不认识了庄里的根柱样,像不认识了同族侄儿跃进样,望着他们俩,就像他代课教书时望着课本上他看不出意思的两张图,算不出得数的两道题,就那么地看着他们俩,半张着的嘴,从开始听他俩说着话,到末了嘴都半张着,没有动一下,没有合一下,眼也没有眨一下。
校院里的桐树上,有麻雀水喳喳的叫,在他们立站着的静里边,如同有一股急雨荡在校院里。他们就那么立在沉寂里,死默着,默死着,三个人不停地你看着我,我也看着你。到末了,先是贾根柱有些耐不住性儿了,他像喉咙痒样咳一下,咳了一下说:
“丁老师,我俩说的你都听见没?”
爷就照根柱和跃进说的宣布了。
在吃饭时候宣布了。没说别的事,只说他老了,丁亮、丁辉这两个不争气的儿让他丢尽了人,他再也没脸来管学校里的事,没脸来管热病人们的事,更管不了庄子里的事——也就索性不管了,以后由根柱和跃进他俩管着了。
说他俩还年轻,病也轻,心也热,就由他们管着了。
人都蹲在灶房和仓房门口的日头地里吃着饭,都想起昨夜我叔和玲玲贼欢的事,就都觉得我爷确也没脸再管啥事了。自己孩娃都管不了,哪还能再管了别人的事。便都扭头去找我叔在哪儿,就都看见他蹲在灶房以东、离仓房最远的檐下吃着饭。人们看他时,他也看人们,脸上还挂着厚赖赖的笑,像他压根不把昨儿夜里的贼欢当成一回儿事。不把爷不再管学校的大小事情当成一回儿事。不把贾根柱和丁跃进管事的事当成一回儿事。他的笑,飘挂在脸上,像是装出来的笑,还像是当真不把被捉奸当成丑事的笑。他的笑,让人们捉摸不透时,就有人在饭场这边唤:
“丁亮呀,占着便宜了是不是?”
我叔回话说:“快死的人,贼欢一天说一天。”
贾根柱和丁跃进不看我叔的笑,他们把端在手里的饭碗放在地上听,听着我爷宣布的话。听完了,从身边窗台上拿起一卷标语似的纸,用洗锅刷子粘着碗里的饭,把那红纸贴在了灶房门前的杨树上。
他们不说话,很严肃地贴着那张大红的纸,贴完了,人都过去看,见是他们订出来写在纸上的条规文:
一、每个病人必须每月按标准兑粮入伙,缺斤少两参假者,日他祖奶奶,让他全家人都得热病死;二、凡政府照顾的粮、油、药物等,由学校统一管理,任何人不得贪吃多占;贪吃多占者日他祖先八辈子,连他祖先八辈、后代十六辈,都得热病死。
三、争取政府给每个病人照顾一口黑棺材,棺材由贾根柱、丁跃进商量发放,不听指挥者,不仅不发棺材,还动员全庄人去曰他祖先八辈、后代十六辈。
四、学校的财产任何人不得私自挪用占用,凡用者必须由贾根柱、丁跃进商量同意;偷占挪用者,不得好死,死后会被人开棺盗墓。
五、凡牵涉到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