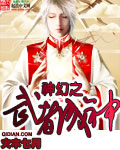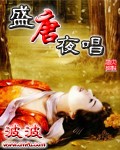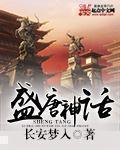幻之盛唐-第5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支起的红油伞下,缠枝牡丹的头花贴鬓,云印芙蓉的雪里青绡裙的尉迟瑶,款款行走在其中
“又是瑶娘……”
几名侍女捧着扬州送来的琼花,轻步悄声走过,忍不住私语偶偶,虽然都是类似出身的可怜人,但是随着服饰的对象和主任身边地位的亲疏远近和个人喜好,也自然分成一个个小团体。
“胡女真的就这么招人喜欢么……”
“恭喜瑶娘了,主人给您做了新曲……正在试唱呢……”
负责值更的初晴,巧言笑兮的对她道贺到。
“这次……是去了李尚宝那里……还有雪娘作陪……”
作为梁氏的女人,除了身为主母的阿蛮,可以专宠内房之外,其他女人都是按照侍寝轮值的日子,按照大人的喜好,搭配若干人一起侍奉的。
只是大人的口味有些的特别,喜欢让女人们陪夜的时候,必须打扮成朝拜时的大礼盛装,或是穿上一些奇奇怪怪的服侍造型……
今天的风格,乃是仿照佛门净土变的彩绘壁画中,那些歌舞飞天袒胸露臂的造型,萧雪姿那交缠在胸前的帛带,根本遮不住那两团硕大的摇荡,连两点都凹凸出来。抱着个装饰性的竖笛,倒骑盘缠在男人身上,被永王家那位前郡主李昔悦对脸贴胸从后抱着,眼目迷离反转雪颈,口舌交缠的做那哀呻娇吟之语。
……
雨丝沥沥中的河西道,又是一个早晨,但是时间对大多数背井离乡的人来说,已经麻木的没有意义了,大片沦陷区内荒废的田园和牧场,被迫逃离他们的自小生活的土地,赖以生存的家园,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了。
卷缩在墙根下简单窝棚里的人体,在太阳的照耀下,终于获得了足够的温暖蠕动起来,随着召集的哨子声,麻木或呆滞的汇成一条条洪流,向城中一个个散发着热气的粥棚兼集合点卯处报到。领到一碗薄粥后,稍稍点了肚子之后,然后拿上出工的牌子,神情木然的由工头领着进入一个个临时的工地。
在那里,大堆烧得的焦黄的土豆和地瓜,码的老高,那是一天唯一能吃饱的正餐。
吐蕃入侵,在河西各地造就了大量的流民,而且这次他们不要老弱的俘虏,只有青壮男子和年轻的女人会被留下来。因此逃亡的大潮,像是汹涌的洪水一般,涌进那些还算靠近后方的州县中。
好在以龙武军为核心的河西行台上下对处置这种状况,已经有相当丰富而成熟的经验,不管做什么,就是不能让这些青壮无所事事的闲着。
按照枢密院和中书省联署《战时田土备荒》的训令,在西北路实行军民一体的战时体制,从关内到河西,将进行大规模的丈田和编户,所有紧、要、显、望之属的州县,因为战乱暂时无主的土地,将被军队暂时接管,然后组织流民的进行播种耕作,大量种植快生速熟的豆薯类作物,进行备战备荒,就近输军。
“灵州防御使率朔方留后将士2600员并藩骑子弟1300员,已经抵达行台……”
“天水太守派人送来暂编营新卒1200员,补充营2700员……”
“成州刺史派人送来暂编营新卒1200员,补充营2700员……”
“岷州司马带来……”
“武州刺史……”
“渭州守捉……”
“原州……”
开春之后,河西以东各州输送的兵员和劳力,也陆续汇集到了行台……各州送来的守捉、团练兵,被称为暂编营,保留小建制分配到各地戍守部队中使用,送来没有受过基本训练的普通青壮,则作为后勤劳役和预备兵员,随时调配给那些伤亡惨重需要退下来修整的营团。
随着春天的到来,吐蕃人长期占据河西、陇右的意图,也越发的明显,随军的牧奴,甚至已经出现在了湟水的上游,位于下游的河西重镇兰州,甚至可以捞到一些死去的牛羊。
河西行台中军的巨大沙盘上,来自双方阵营的更多筹码被加入进去,堆积交错在一起。代表吐蕃各部军队的旗帜和番号,也随着鏖战和接触,越来越明确起来。
绵绵细雨中,河州城外,临时平整出来的大校场,成列高举着刀枪的队伍,接受校阅,不断被授予各色旗帜,然后就此奔赴战场,蜿蜒而去。
“这些都是什么人,根本没有训练过多少日子,也没随军临战过的经验,就这么送到前方去……”
观礼的人中,一个年轻的军官,有些愤愤地道,他的肩甲上是朱鸟纹,代表武学见习生的身份。
“这不是叫他们去送死么……”
“你以为吐蕃人来了,他们就能独善其身么,多少人已经家破人亡,多少人的妻子儿女,沦为吐蕃人奴役之下,这不过是早死晚死的干系……”
另一名老成多的军将张思俭摇摇头道,加入龙武军前,他是山南军的出身,对这些东西看的也要深刻的多。
“至少在我们的旗下,他们是为了保卫乡土而死的……”
“这是诡辩之说……”
“起码我们既不兴随意抓丁或是裹挟百姓来充数,让他们自愿应募的……要是河东、朔方军那班人,指不定还变成怎样……”
张思俭转头正色道
“我们目前是在用大半个河西道和整个关内道人力物力,来对抗吐蕃人的倾国之力……”
“现在朝中唯一有实力的河东、朔方大军尽远在云中、河北、平卢一线,自顾不暇;山南、剑南调遣过来的兵马,还在关内进行适应和编练……在这个夏汛到来前,我们必须构建新的防线,争取更多的时间……”
“吐蕃的王军主力和本帐,可还大都没过西倾山以东啊……而现下整个西北路,几乎靠本军独力支撑……我们输不起,也不能输,行台必须考虑到最坏的情形……”
“但是我们堪用的人手奇缺,没有足够的军士和老卒,来训练和统领他们……”
年青军官犹自争辩道
“那就从团练中选,团练不足的,就从义勇中找,义勇还不够,就用那些武装民夫。”
张思俭斩钉截铁地道。
“本部经营多年的三级战备轮训体制,各庄子的巡丁和工场的护卫队,可不是摆设吧,基本的操列和令行禁止,他们还是知道一些的吧……”
“军中庇护和供养他们及家人,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一刻……”
“那我请求带队去前方……坐望他们去死,我总是做不到的……”
年青军官也下定了决心。
……
在略带丝丝凉意的春雨中,
县令张牧之,满头大汗汗的支使这手下人,将大锅支起烧开,他是成都武学出身,早年积累下一定的资历后,因为某种需要和交换,由武途转入文职被外放到这里做县尉,当然官面上的说法,这批特任是为了填补当年武威之乱造成的空白。
因此,他们处事的方式,与那些从吏目熬资历上来的实务官,或是正途科举或是荫补出身的官员,有很不小的差别。虽然作为正途官,不再享受两府三军内部的待遇,但是他们的家人,还是按照军输的标准和待遇住在特定的聚居区内,接受年节的优抚和日常补助的。
用某位大人的话说,这是那些为这个集体作出贡献的人,理所当然应该做到的。
按照朝廷新的体制,原本在近、望、紧、要之县,才设立的末流辅官——县丞,将受到兵部驾部司的直管,而变得炙手可热起来。
手下人除了同乡和老家人外,钱谷、物料、大半都是陆续由人介绍,提携过来帮忙的两学三附出身,在当地形成一个比较得力的小圈子。这也是这些外放年轻官员的普遍现象。
“快快,准备热水和药物……”
“今天至少有好几路粮院大队和补充团的人马要经过这里……”
从途径军队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前方的状况,早前经过的那些军队令行禁止,没有军令甚至连大路都没有离开过,哪怕饮食取水就在眼皮底下,但是后面这些补充团,就越来越不好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过的军队越多,总是能收容不少因为缺乏经验等原因掉队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甚至有些是吃不了这个苦,反悔偷偷半道试图溜走的。
作为有唐一代的官员和将领,文武分野并不是很明显,也不想后世为了防范武人作乱而刻意以文抑武制造出一条悬殊巨大的鸿沟,或是以极其狭隘的选士范畴,而令行政系统内的官员们,不得不靠大量编制外的幕僚和吏员来开展工作。
所以这种构成大唐统治力最底层父母官的任务要繁重的多,上马能挽弓御敌,下马能治政安民,这是对这些靠近边州,治下藩汉陈杂的父母官们最基本要求。治理那些归化的番人,光靠怀柔是不够的。
至少他在那些番姓小部中,是被半敬半畏的称为方瘸子的。
依靠途径这条要道,早年结交的那些商团关系也带到了地方,还有来自背后上官和同袍老兄弟的一些支持,在静边之乱后,他手下用军中退养的老卒,名正言顺的在这个人口勉强过万的中县,练出一只500人的土团兵,其中有一百多名自备弓箭的猎手和三十多名鞍马齐全的番汉骑丁。
他不知道别人那里是怎么样的情形,但他觉得扶持自己的势力,并不是只有他这么一出选择,毕竟当年因为各种原因选择放弃了军中的发展,而被放出去的人有好几十。
当初只是顺手布下的闲棋,居然变成了一路关键的妙招,他们可以用查私防盗的名义,有限的干预和保护河西走廊这条西北最重要的商道。而到了战时,他们又成为地方的中坚力量。
这些日子,这些土团兵全部召集在大路上,维持秩序,组织闲余劳力,协助官军过境,又要巡视春耕,防止忙的脚不着地,这次他亲自出动,却还有一个秘密接应的任务,
不惜破坏规矩,亲自待人越境进入邻县,若是被人揭举出去,又是一场大风波。
……
吐蕃人占据的地区,也有人在雨幕中叹息,
“多么好的土地啊,拽在手上是粘糊糊一大团……”
吐蕃的国属庶人石松,正在新翻肥沃泥土的芬芳中陶醉着。任由雨丝打湿他的毡帽和辫稍。
河曲之地,当今吐蕃赞普的生母,金城公主的沐汤邑,当年大唐皇帝陪的嫁妆,水草肥美和满山满谷牛羊骏马的沃野,多少吐蕃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数十多年后终于又回到吐蕃的手中,为了争夺它,数十年来这片土地上不知道浇灌了多少吐蕃和大唐健儿的血。
他和很多同样身份的人一样,千里迢迢从吐蕃国各个角落,征召和趋势下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在他同一批的行人中,甚至有来自比邻天竺和黎域的叶茹之类,最偏远地区的牧奴和庶人。如此大规模的迁徙,在吐蕃短短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吐蕃虽然号称数千里之大国,但是大部分土地贫瘠而干旱,四季最不缺少的就是各种风霜雨雪的灾害,吐蕃五茹横跨高山雪原大漠草地诸多地区,地貌气候环境生产生活习俗风貌不尽相同,进行统治和管理的方式也颇有区别。
象石松生活的伍茹,自小长大的迩药之地,遍地是不能食用的咸泊,和寸草不生的荒碱地,生活在当地的大多数庶人和佣奴,只能在管领头人手中世代经营的那几分贫瘠的可怜的口分田之外,还要利用砾石荒滩和存不住水的板结沙土中,那丛丛稀疏的草,进行艰苦的放牧。
为了让牲畜积累足够的肥膘,他们不惜跋山涉水数百里,然后赶在大雪下来前,找到过冬的避风地,其中还要提防饿红眼的荒原野兽和来自同样受灾而走投无路的部落可能的袭掠。
象这种成色的土地,在吐蕃国内也只有那些大贵人的领地内才配有,虽然石松家所在的整个村落,都是吐蕃最勤快的农人,做梦都想能够在那些河流边的土地上耕作,但那往往只有贵人家的远宗族人和部曲才拥有的特权,现在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就在这片低地上。
清澈而充沛的河水,无所不在的滋润着这片土地,连春生初长的野草都生的特别的枝叶肥厚,掐一把都能挤出汁液来。或许可以在今年野草全部变白之前,让自家的孩子吃上真正青稞做的糌粑。
石松家世代都是吐蕃国属的庶人,作为祖辈父辈的一生,就是繁重无暇的耕耘和放牧中度过,一些命不好的人会在灾害和各种意外中死去,幸运一些的,则在繁重的劳作中慢慢未老先衰,再被榨干骨头里最后一份气力后,为了给家里最幼小的孩子省下一分过冬的口份,在大雪封山前自发的走上那条只身去“祭拜”山神的路子。
只求雪山高地之灵,能够少降下几场雹子或是霜害,让这些苦命人多收一点谷子,少冻死几只牲畜,这样从嘴里省吧省吧的能多养活一个娃子,蒙山川之神灵的保佑,辛苦的熬到成年,送到贵人家的田庄堡寨里,给家里分担其一份徭役和差使。
如果这是一个女娃,可以从贵人家的最底层的婢女做起,给家中减少负担,然后在成年后,用作兄弟的换婚,或是卖掉赚一份嫁妆来补贴家里。
假如这是一个长相好的男娃,或许有机会被贵人家的管事看中,派去做一个相对轻松的扫粪马童、拾鞭人之类的轻松活,可以省下家里的一份紧巴巴的口粮,如果这个那娃子机灵一些,能够学到些服侍人的手艺,最后讨得主人的欢心,指给一个女奴婢,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毡帐和分家。
如果这个男娃子足够健壮,有幸随小主人出征又活着回来,或许就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从一个腿上沾满牛粪和泥土的“庸”,变成一个佩戴刀剑穿着皮子,需要人仰视的“桂”。
可惜的是上个冬天的白灾是在太过厉害,对盛产牲畜、皮毛和奶类,被称为吐蕃草仓畜栏的青海之地,影响最大,再加上那些高地上上移到这里来的牲畜,多少有些水土不服的症状,因此开春的面对大片的良田沃壤,畜力却是严重不足,因为战事的需要,连稍微壮实一些的牛,都被那些大人们强征去运送前方输给和自己的战获。
于是三五成群的人犁,再次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你们这些懒骨头啊……”
想到这里,石松手中的鞭子,也更加卖力的抽在那些佣奴身上,由于管领的贵人手下实在缺人,所以不得不用他们这些时代驯服的庶人,来管理那些数量庞大的佣奴,这是一个他不得不把握住的机会。
他最大的一个儿子,正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