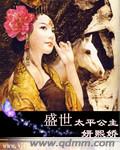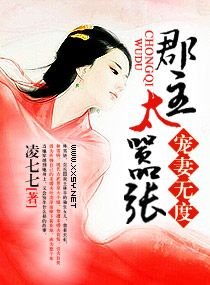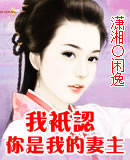春秋小领主-第25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欢的美女,实在是令人哀伤……
赵成的目光时时瞥向这位楚女,他不奇怪楚女的存在,只是生活在华夏的氛围里,他自小被教育要庄重、要有威严、要行事出于“礼”、要含蓄……奇怪的是,楚女似乎完全不知道这些,他听说这些楚女是楚王的宫女,那么她们接受的应该是楚国宫廷式教育,怎么,楚国宫廷教育如此热情奔放,如此不讲究含蓄以及如此喜欢扭腰。那位楚女腰肢细的手堪一握,却片刻不肯停顿,不断地扭来扭去的,真让人担心那细腰扭断了。
“我是不是也要搜罗几位楚女”?赵成退后一步,心说:“只是不知道母亲怎么想?或许应该先跟父亲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哦,听说蔡国妇女特别擅长厨艺,总喜欢把自己的男人照顾的,饭菜端到男人牙齿边。我还听说,蔡国男人从不喜欢下地干活,也不喜欢战斗,就喜欢在家里享受女人伺候。而地里的活儿,几乎都是女人完成的,不知道父亲喜不喜欢这样的女子。也许父亲喜欢,因为父亲喜欢研究厨艺,弄几个蔡国美姬回家,父亲今后不用独自研究美食了,那些女子会替父亲操心的……”
赵成心里想着事,郑重的向赵武鞠躬:“谨遵命!”赵成是用军礼答应父亲的,晋国军中的规矩比较严,虽父子在军营,但接受军令的时候,也要用军中礼仪彼此应答。
赵武也放下了元帅的威严,用亲切的姿态询问赵成:“如此一来,你的婚礼拖延了,不要怪父亲,好男儿为国征战,岂能顾及到家事,等我回去,替你办一个更加隆重的婚礼。”
赵成退后一步,嗫嗫的说:“身为臣子,我怎能与君上同期举行婚礼?如今这样最好,等君上大婚之后,我再举行婚礼,才是最妥当的。”
一直粘在赵武身边,细腰扭来扭尖的楚姬脱口称赞!“好男儿!”楚姬的突然开口让赵武脸色一变。在座的人都脸色愕然:楚姬说的是晋国语言。这是楚姬第一次开口,她语调清晰。
春秋时代,人们的审美观跟后世完全不同。后代的人以手无缚鸡之力,毫无反抗能力作为英俊才子的标准,并认为美女就应该爱这样的才子。而春秋的英俊标准则是孔武有力,能够保护自己的家人,能够对外征战掠夺别国的资源,能够取得一定地位让家人受到尊重……楚姬说的是这时代流行的主流观点,这倒不值得惊愕。
但一直以来,楚姬说的完全是鸟语,她用一副不懂晋国语言的姿态陪伴赵武日日夜夜。赵武因为她不懂晋国语言,所以在商讨军情的时候从没有回避楚姬,因此楚姬的开口,倒让赵武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转念一想,赵武又哑然失笑了:这是晋国军营,周围的都是晋国人,楚姬即使是间谍一类的角色,她怎么传递情报?晋国士兵会听从她楚国语言的吩咐吗?
再者说,春秋时代的语言,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继赵武之后百余年出现的《论语》,总共十五万余字(15919字),却只用了一千三百多个字词(用字量:1344个),就书写而成如此的长篇巨著。所以,这年头,能熟练掌握一千三百多个字,就已经是类似孔子那样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圣先师”了。
赵武自己有过荒山学艺的经历,在这个单音节时代,一词多义,词汇量贫乏,真要有心,学会一种语言只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对于现代有过学习外语经验的人,一天背十个单词并不感觉吃力,只要有心,一百天之内学会一门外国语言,简直像喝凉水一样简单。赵武本身自己经历过这事。
想起当初在战船上,楚姬充满柔情蜜意的吟唱《越人歌》,赵武也就放弃追究的念头。人世间有爱,任何艰险与困难都不足为惧。只要楚姬一心想与赵武沟通,学会晋语对她来说不是障碍。想通了这一切,赵武脸上显得波澜不惊,但他心里充满柔情蜜意,脸上表情淡淡地摆了摆手,吩咐说:“今天我们的援兵到了,随便庆贺一下双方会师吧!吩咐军中摆出酒宴。”
赵武其实不是一个追求享受的人,想当初赵氏重新恢复家族名声,幼小的赵武谨小慎微,谁都不敢的罪,他哪里有追求享受的时间。但赵武身上带着一些现代人的习性,总是让春秋人感觉到格格不入,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赵武很有点逆流而上的姿态,无论真实的历史与现在的历史。
基于现代人的习性,赵武对居住状况,以及饮食卫生的追求,在春秋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于是,赵氏在列国间都有一种奢华无度的称号……。赵氏使用的餐具最精美,赵氏煮菜时掺杂的香料最繁杂,赵氏就餐前很多仪式非常古怪……子产与向戎原先不是赵武体系内的人,他们以往听孙林父以及鲁国的公孙、叔孙豹谈论起在赵府宴饮的经历,语气中充满炫耀,可惜这两人没有亲身经历过,不好给予评价,这次他们终于见到了全套的赵氏奢华。
赵武出征的时候,准备的比较匆忙,随身物品简单。当然,赵武也习惯了出门在外必须的简朴,想当初赵氏初上阵的时候,赵族只是一个小贵族,带领一个服装都很驳杂的花衣军团,没有资本追求奢华。如今,赵氏已经是大贵族了,新来的援兵集团中,赵成带领的主要是赵氏后勤人员。
赵成是赵氏少主,这次出战是他的初阵,智娇娇宠爱他,生恐他不习惯军营的生活,给他配备了全套的奴仆,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光是用于就餐与做饭的炊具就拉了满满十大车。赵氏现在有资本有实力,轻而易举做到这点。
等宴席开始的时候,元帅大帐内摆上来的瓷具,让礼仪之国宋国,以及最老霸主国郑国也张着嘴,伸着舌头,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赞叹。春秋时已经有了挂釉的瓷器,但数量很少,从那些春秋贵族特意把极少量的挂釉瓷器埋入墓中与玉器、金器一同殉葬看来,春秋时代,挂釉的瓷器价值等同于玉器、青铜器。赵氏的餐具却是全瓷。这些瓷具外面挂的釉并不均匀,在赵武看来,简直是伪劣瓷具,但这些散发着釉色的瓷,落在郑国与宋国正卿的眼中,简直是君王才可以享用的礼器。
如今,这些礼器上充满了如山一样的食物,个个香气扑鼻。此外,端上桌的还有一些当地水果。这水果,大家倒是认识。南方的天气炎热,即使在这冬天,也还有许多四季的果实,这些果实的形状与现代略有不同,以至于赵武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当然现代各种水果都是经过几百年人工驯化而成,不是古代野生的水果所能比拟的,赵武认不出来,那是必然。
就餐的餐具使用的是带锯齿的商匕(餐刀),另外,叉子也提前出现了,不过这时的叉子是两齿叉。与现代人想的相反,春秋时代,贵族举行的宴席上,最常使用的餐具是刀叉,唯有平民用不起完整的青铜器,才使用筷子替代。因此,在这场宴席上,只有奴仆面前摆着筷子,他们用筷子夹取食物,不是给自己吃的,而是给各个盘子里摆放,进行分餐。
春秋贵族的宴请方式,为每个人面前摆个小桌,桌上摆着自己吃的食物。按照当时国人的习惯,盘中的食物尽量追求丰盛,堆得老高。贵族吃不下这些东西,也不会浪费,因为撤下去的盘子,里面剩的残羹冷炙就是奴仆的食物了。
桌案上,诸卿面前整齐摆放的、用于饮酒的器皿也不是青铜器,而是一种色泽均匀的黑瓷。这年头瓷器属于高科技,是因为陶匠总无法提高陶窑的窑温,没有高温就没有大规模量产的瓷器。如果不是赵武提早发现了山西煤炭,并开始使用煤炭开始烧窑,也许如此多的瓷器不会出现在春秋。而正常的历史上,中华之地大批量出瓷器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煤炭,才提供更高的窑温。
整个宴席上,唯独赵武与赵成使用的酒杯。与大家的稍有不同,这两人使用的是绿色的玻璃杯!早期的玻璃都是绿色与红色,这是因为早期的玻璃都是从青铜器与铁器冶炼中发现的,所以都带有铜与铁的燃烧色。赵武的玻璃杯比较厚重,厚的跟青铜器酒爵相似。没办法,当时人的审美观念以厚重为美,轻薄的东西则认为是轻浮。而赵氏出产的玻璃杯,最初也是仿造青铜酒爵的形状开始,所以杯壁非常厚,这种厚壁杯子散热不快,如果向里面灌注热水,玻璃杯经常会炸开。
比较起来,赵武的酒杯颜色更加均匀点,颜色仿佛是秋天麦苗一般葱绿的翠色。而赵成的酒杯颜色稍有点杂,带有缕缕的铁锈红色。其实,在春秋人眼中,两色的玻璃杯更罕见,更珍贵。
但赵武与春秋人不同,就在于他喜欢的东西,大多与春秋人观念拧巴着。是他首先提出了纯色玻璃的概念,他的酒杯是自己挑选的。在参加酒宴的人眼中,赵成握着比自己父亲更昂贵的酒杯,是赵武太宠爱这个儿子的表现。作为儿子,酒器居然比父亲更精美,太不符合级差待遇。
这两支酒杯很罕见,赵氏虽然研究出了玻璃的制造,但由于原料的限制,赵氏目前出产的玻璃还大多是中国一贯的钙钡玻璃。这是一种浑浊玻璃,可以冒充玉器。所谓“随侯珠”就是这种成分的玻璃。
赵氏也出产钠镁玻璃,但因为原料限制而产量很少,几乎不对外交易,所有的出产都被关系密切的贵族家族包揽。而钠镁玻璃因清澈透明,大多数被当作水晶,用于制作高级器具。像如今赵武父子手中这样清澈透明的钠镁玻璃杯,目前,整个华夏唯有眼前这两件而已。
手里握着价值千金的玻璃杯,赵武父子却毫无觉悟,他们举杯叮叮当当的碰在一起,赵成祝贺父亲取得百年难遇的大胜,赵武则预祝儿子能留下一个完美的初阵记忆。座下的子产却在啧啧叹息:谁说赵武举止不像贵族,那个贵族像这样,把价值万金的玻璃器皿不当回事的碰撞在一起……瞧着都心痛。
音乐声响起,丝竹渺渺,赵氏特制的酸酪(酒)呈现献上来,五颜六色的果酒喝到嘴里仿佛像蜜一样甘甜。在座的郑国大臣与宋国大臣称赞不止,而座上的赵氏父子依旧淡淡然的,他们还窃窃私语:“今年的粮食欠收,果子似乎也因为干旱而比较干涩,酿出的果酒口味不比往年,酸涩了许多啊!”子产已经彻底无语了……一旁的楚女,则从头到尾只感觉无穷无尽的惊喜!
这样的宴席连着举办了三天。三天后,晋国军队整装待发。赵武留下中行吴继续监督造船,自己则领着晋国其他部队调头转向东北方向。
晋国总共三个整编军,如今前线集结了两个军多一个师的兵力,霸主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兵力来到南线,不为针对另一个超级大国楚国,而是气势汹汹转向了蔡国。
蔡国的国都遭围攻已经三个月了。宋国的军队战斗力不行,刚开始攻击失利后,宋国立刻改变策略,驻扎在蔡国国都城下,开始采用长久围困的策略。困城战是漫长的,宋国以前遭遇围困,都到了百姓相互换交换儿子当作食物,用尸骸当作柴火的惨烈地步。这次宋国转而围困蔡国,三个月后,蔡国国都已经失去了炊烟。
南方的隆冬虽然不太寒冷,但在这个用麻衣、兽皮做御寒物的古代,没有足够的柴火取暖,也是很让人受不了得。贵族有厚重的皮裘,日子还过得去,百姓已经冻得无法出门捡柴了。
蔡国司马忧心仲仲的站在城墙上,下意识的询问本国执政:“楚国还没有来救援吗?我们还能抵抗下去吗?”
第二百三十章 观众太不配合
蔡国执政想了想,回答:“我们的粮食还充足,今秋收的粮食还没有吃光。如今宋国堵住了四处城门,虽然让我们无法出城砍柴,但我已经考虑好了,从明天开始拆毁城郭外围的木屋,把原来那些木屋居住的人集中到内城,大伙相互挤一挤。总能熬过这个冬天去。”
蔡国司马摇头:“楚军已经战败了,我不知道楚国的援兵多会儿才能到来,不如我们投降吧?让我们暂且投降宋国,等宋国撤退了,我们再派人前往楚国送信,如果楚国还是无法救援我们,想必,他们会原谅我们这次投降北方的行为。”
蔡国执政摇头:“要投降,我们也不能投降宋国啊!我听说晋国正在与楚国交战,如果楚军退了,那么晋国人会转来帮助宋国。宋国不过是晋国一条狗,我们投降那条狗有什么收获呢?不如转而去投靠狗的主人……嗯,我们之所以坚持,就是盼望晋国人的到来,等晋国人到了,我立刻投降。”
蔡国司马拧起了眉毛,望着天际间,轻轻的说:“晋国人到了。”“哪里?在哪里?”蔡国执政紧着问。
天际间隐隐约约多了一些黑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黑点越来越大,渐渐的已经可以看清一个个方阵了,果然是晋国人。傲慢的晋国人以一个旅为一个方阵,为首的晋国战车轻快的行驶着,旁边的徒步步兵肩上扛着长枪,满脸都是趾高气昂的狂妄。他们确实有资格狂妄,用六个师的兵力打败楚王亲自带领的楚秦联合军队,追杀楚王数百里,任何人取得这种战绩,都有资格把鼻孔翘上天去。
晋国的军队一贯以整齐著称,远处晋国的方阵非常整齐,四个旅像四块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前锋两个旅一左一右行进在道路两边,在这两个旅身后,一个旅形成的方阵与前方两个旅形成倒品字,与后方两个旅则形成一个正品字,整个五个师的部队仿佛一朵盛开的五朵梅花,行进在道路中央的那个旅就是花心,师部的指挥体系也在其中。晋军隆隆的敲着鼓,时而用军号调整着队列的阵线使之整齐,而后用晋国人惯有的那种不慌不忙的步伐向并推进。
城头上,蔡国兵见了气势汹汹而来的晋国人,深深的吸了口冷气。晋国的军队以前就以齐整而闻名,现在换了统一的服装,统一的兵器,整个队伍显得更加肃穆威严。他们无形中透露的重重杀气,让蔡国兵虽然相距遥远,虽然明知道有城墙的保护,但依然感到阵阵两腿发软。
蔡国司马毕竟是军人,他也上过几次阵,所以首先从震惊中觉醒,赶紧催促蔡国执政:“执政,晋国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