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靠的”哥萨克去追捕逃犯。三名哥萨克警察受命“竭尽全力搜捕梅谢里诺夫,想办法活捉他。万一他反抗,不得已时可以动用火枪;但只打他的腿脚,不要打死他”。
在给雅库茨克省长的报告中,警察局长请求增援12名士兵,以加强本地的防卫力量。他担心还有革命者前来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
不久梅谢里诺夫在雅库茨克州被捕获。他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冒充某个神甫的儿子。他没能抵挡多久,最后被迫道出了真情。原来他是警方追缉已久的革命党人伊波利特·梅什金。
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过去一样,仍然顽强而孜孜不倦地写作。冬天他通宵达旦地写,一到清早又把所写的东西烧掉。百无聊赖啊,如果什么也不写,他就要发疯或者把一切都忘掉。
在维柳伊斯克孤独而漫长的岁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几十部长篇小说。但只有小说《余辉》中的两部保存了下来。作家因怕突然搜查,习惯于把写好的东西销毁。边写边撕,不必保存手稿:写过一次的东西永远会留在记忆里。
他试图通过中间人,把内容全然“无害”的作品寄到《欧洲通报》杂志编辑部。但寄出的作品全被第三厅扣留。人家也是“吃一堑,长一智”,生怕再蹈《怎么办?》的覆辙。
1877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地听到战友涅克拉索夫病危的消息。他深为震惊,他给表弟佩平写信:
“……如果你收到我的信时,涅克拉索夫还在继续呼吸,就请告诉他,说我热爱他这个高尚的人。……我为他痛哭。他的确是一个心地十分高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作为一个诗人,他自然高于所有其他的诗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遭遇,不仅使他的知交和战友感到不安,报刊上也出现了为他鸣不平的呼声。但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把这个囚徒看作是誓不两立的死对头,对他决不会施仁政发善心。
生命每人只给一次,在这个问题上帝是公正的。权倾一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不可能万万岁,在1881年3月1日被民意党人的一颗炸弹炸死。他死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境况才有所松动。
沙皇去世的消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实行了严格的保密。
由于害怕革命党人在亚历山大三世加冕典礼期间,会采取恐怖行动,政府方面通过中间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维柳伊斯克迁移的条件,与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进行了秘密谈判。1883年5月27日,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恩准”,“在警察的监视下将车尔尼雪夫斯基转移至阿斯特拉罕,但沿途不准人们向他欢呼”。
阿斯特拉罕是俄国南方里海岸边的一座城市。3个月之后,两名宪兵军士带来了要将车尔尼雪夫斯基送往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但转移到什么地方,依然对本人保密;对外只称他是“五号秘犯”。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意识到他命运中将要发生一个转折,所以催促宪兵快快动身。
启程的时间原定在正午12点,但一清早他们就上路了。当一些维柳伊斯克人来古堡找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他已经不在了。
从维柳伊斯克出去没有车路,周围是一片可怕的沼泽地,也没有桥梁,必须骑马淌过小河……惟一的道路就是原始森林中的一条羊肠小径。车尔尼雪夫斯基拒绝骑马,只好乘雪橇;有一段路不得不以狗取代马。
6。 最后的岁月
到了雅库茨克,车尔尼雪夫斯基被直接送到省长家中。
省长切尔尼亚耶夫过去对这个囚徒极尽刁难之能事,现在对他却热情而体贴。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惊奇,他们到达时,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到了要离开雅库茨克时,才弄明白省长如此殷勤的真正用意。原来人家怕他在城里呆下来休息或上街买点东西,这名重大“国事犯”如果在这里露面,说不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车尔尼雪夫斯基上马时带着讥讽的口吻说:
“该转回去见见省长大人,吃了他一顿早饭,是不是该付他个把卢布……”
押送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公开的秘密”,在离开西伯利亚时搞得满城风雨。通过报纸全俄国都知道了。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是到了伊尔库茨克才知道要转移到欧洲城市阿斯特拉罕。
当晚,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被用四轮马车继续往前送了。不是一般地乘行,而是在飞驰。乘的是驿车,日夜兼程,一昼夜走230俄里。时值秋季,第五天他已经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离伊尔库茨克足足1000俄里。沿途各省长都得到了当局的密码电报,要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有人“破坏社会秩序”云云。
经过两个月的劳累行程,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0月22日深夜到达萨拉托夫城。他被安置到宪兵上校的家里。获准可在此地短暂停留,同家人见见面。看来是故意安排在夜晚到达,生怕萨拉托夫人有同情的举动。
家里人并不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萨拉托夫的确切日期。奥莉佳十分焦急地等待着会面的通知。当她得知丈夫已离开伊尔库茨克,正在来萨拉托夫的途中时,写信给他的亲戚说:
“我高兴得简直要发疯了,我连自己在做什么和该做什么都记不得了。现在更是如此!要能飞到前面去迎接他就好了……我大哭了起来……什么也看不见。”
当天晚上,一个侍女进来要找奥莉佳,递给她一张条子。奥莉加看过后激动万分,匆忙披上皮大衣,穿上套鞋……
经过多年的分别,奥莉加在宪兵上校的住所同丈夫短暂会面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晚就乘驿车走了。临行前和奥莉佳约好,第二天她也乘轮船到阿斯特拉罕去会合。
10月27日早晨,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伏尔加河右岸与阿斯特拉罕遥遥相望的哥萨克福尔波斯特镇。乘小汽艇过河后,他被送到市中心广场的一家旅馆。
阿斯特拉罕的警察局长已经在动手写汇报:
“车尔尼雪夫斯基已于10月27日上午10时到达阿斯特拉罕城,已委派警察所长及侦探巴卡诺夫对他进行监视。并责成巴卡诺夫定期向宪兵局长汇报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时,未出现任何欢迎场面和发生任何游行示威。”
这一夜,在旅馆的房间里终于剩下他一个人,“护送者”没有了。宪兵办完手续后便回去销差。
车尔尼雪夫斯基稍事休息后,就到码头去接奥莉佳。城里人声嘈杂熙来攘往,各族人都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波斯人,鞑靼人,希瓦人……他几乎在码头上等了一整天。轮船到达时已是傍晚时分,他从旅客中认出了奥莉佳的身影。
他们在邮政大街找到了一套3室的住房。住宅陈设很简单:两把椅子,一张有点摇晃的桌子,一张沙发,加上床铺,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们刚住进这套房子,儿子便从彼得堡赶来了。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儿子还是小孩,现在亚历山大已经29岁,米哈伊尔也已25岁。
儿子在阿拉斯特罕逗留的时间很短促,父亲没来得及亲近他们,也来不及把他离家20余年的辛酸经历告诉他们。
儿子回彼得堡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表弟佩平写了封信:
“我和我的孩子还很生疏。他们来时我感到非常‘陌生’。他们和我一起只度过了8天,这么短的时间我能很好地了解他们的才能吗?特别是米沙,这段时间老在为家务事忙碌,一天难得有工夫和我谈几分钟。来时他同我很生疏,走时也还是那么生疏!”
说来也辛酸,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最操心的事,是偿还向亲友借的钱。这些人在他流放期间帮助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不仅想还欠亲友的款,而且还想还“公家”的债。尽管在阿斯特拉罕生活的头几个月他经济很拮据,他仍然请省长告诉他,他总共“欠”了公家多少钱——当局在伊尔库茨克贷给他的路费,还有从伊尔库茨克到奥伦堡的一辆新四轮马车车费。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来时体弱多病,但工作的愿望并没有减退。他很想坐下来工作,一直到肚子辘辘叫唤。吃完后再从早干到深夜,或从夜里干到第二天下午……他希望在佩平的帮助下,能在《欧洲通报》上发表小说作品。他在维柳伊斯克流放时,写成并销毁了许多中、长篇小说。内容还非常完整地保留在脑子里,现在可以毫不费劲地口授出来。儿子亚历山大对创作有兴趣,写过诗歌,也写过剧本。作为传授经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两个钟头之内给他讲了他写过的一本小说的第一章。
还在西伯利亚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拟订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文学创作计划。根据佩平的回信,未经当局的特别许可,报刊是不敢发表他的作品的。结果是反客为主,他计划中只占次要地位的翻译,却成了他维持家计的惟一手段。于是,他便坐下来翻译《比较语言学》,尽管他心中有数,这本书没有什么价值。
贫困在困扰车尔尼雪夫斯基。争取发表作品(哪怕用笔名)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使他十分苦恼。警察时刻钉梢,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在严密的监视下。他们在这里完全成了与世隔绝的人:深居简出,不跟任何人见面,不同任何人交谈。何必给人家造成难堪呢……
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迫在宪兵局拍了照,照片被印了24张,送往阿斯特拉罕及各县警察手中。
迁移到阿斯特拉罕一个半月以后,有一天英国《每日新闻》报的一名记者,到他住所来采访。记者感兴趣的是,能独家报导和从囚禁地回来的著名革命家见了面。
不言而喻,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他谈话时十分谨慎。稍一漏嘴,他就可能受到新的迫害。这次采访后刊登出来的题为《一个俄国政治犯》的文章,当然不会反映出这个革命者的真正精神面貌。
记者对他年轻的相貌感到惊愕——根本不像55岁的人:一头厚发,看不见丁点儿斑白;精神饱满,态度直爽。不过再仔细端详,记者终于发现,20多年的苦役和流放生活还是留下了痕迹。
过了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到了阿斯特拉罕的消息,传到了首都青年学生当中。
1884年1月12日,在传统的大学节——莫斯科大学建校纪念日,一群大学生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拍了一封电报:
为大学生最好的朋友的健康干杯。
一群莫斯科大学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为不能发表作品而苦恼。到阿斯特拉罕半年之后,他作了个试探性的动作:给表弟佩平寄了封短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萨申卡,请你把下面这则消息寄往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编辑部:‘我们听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准备出版自己的作品集’……
因为他寄出的信件,警察局都要拆开检查。他想通过这一特殊的办法试探一下,看当局对他恢复文学活动的意图有何反应。
果然警察局获悉了这封短信的内容,便立刻发函到出版总局,要求不能让上述“消息”见报。
一年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有关方面了解清楚,当局对他有个限制条件:作品要经过检查,而且只准署笔名——这样才允许他从事文学活动。
1885年,经过朋友的周旋,出版商索尔达琼科夫委托车尔尼雪夫斯基翻译韦伯著的11卷本《世界史》。这项工作足够干好几年,可以解决他的无米之炊了。
英雄迟暮,宝刀不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工作能力仍和以前一样令人吃惊。他聘请了年轻人费奥多罗夫作秘书,有时开玩笑称之为“打字机”。
车尔尼雪夫斯基每天早晨7点起床,喝茶时便看校样或原著,接着便是一连5个小时口授译文。他念得流畅而轻松,出口便成文章,就像在读俄文书。午饭后浏览报刊,下午3点继续翻译,直至下半夜……
实际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喜欢这部洋洋巨著,更不赞同韦伯的一些观点(如浓厚的德国民族主义色彩)。他不知疲倦地翻译它,除了挣钱谋生,暗中还另有打算。
他被剥夺了发表著作署名的权利,只好利用韦伯的名字作为幌子,暗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对原文如此这般删节剪裁,清除掉书中的“废话”和反动观点;而且附上一篇专为该卷而写的引文。所谓引文,就是一篇极有分量的评论力作。他的最后几篇论文就是这样产生的,收集起来总的题目叫做《世界史若干问题的科学概念论文集》。
经历了漫长的苦役和流放生活,他现在又使用批判的武器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学说进行战斗。
尾声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阿斯特拉罕被软禁了5年多。家人为把他转移到莫斯科或彼得堡不断奔走,因为在这两处有利于文学工作。可是当局坚持不予批准,直到1889年7月,才准许他迁回萨拉托夫。
回故乡前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出版人潘捷列耶夫交谈时说:
“对于我来说,萨拉托夫和阿斯特拉罕完全一样;不过奥莉佳会痛快一些。我个人倒很想移居到莫斯科,那里有个大图书馆,别的我无所求。”
在房东、秘书和女佣人的帮助下,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行李用船托运走,他本人于6月24日,在一名警官的陪同下启程,秘书很高兴跟随移居到萨拉托夫去。
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一次回乡探亲,至今已过去整整28个年头。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在,沿着伏尔加河岸各个轮船公司的码头鳞次栉比。过去杂草丛生的街道已经铺上石板。平地拔起许多新楼房,城里有了铁轨马车,铁路已把萨拉托夫和彼得堡连接起来;只有城郊那些小房子破烂依然。农奴制废除已经将近30年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多大的改变。
流放只是摧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健康,但丝毫没有使他的聪明才智和精神素质受到影响。他对自己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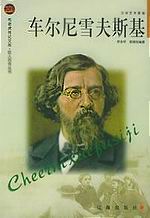
![[戈索夫斯基_魏镇轩_译] 佛里介伊射线封面](http://www.8b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