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孕,因担惊受怕,生下了个聋哑儿子。她的身体也彻底垮了。最后赫尔岑被释放了,但必须离开俄国;理由是他妻子有病需要矿泉治疗,还要医治儿子。到了法国,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想为沙皇效劳,逮捕了赫尔岑并将他遣返俄国。他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便倒下死了。我不敢拿自己同赫尔岑的才华相比,但我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他,我应该等待类似的遭遇。”
尽管他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估计不足——他们今后所承受的考验,要比赫尔岑承受的艰难痛苦得多。
好个奥莉佳,并没有因他的这些警告而离开他。她分明懂得,供她选择的这条道路充满着危险。也许她那时并没有坚定的信念,可能只是出于本能。
起初,车尔尼雪夫斯基跟未婚妻商量好,开春以后他先到彼得堡逗留几个月。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再回萨拉托夫来接她。但很快又改变了这个计划,奥莉佳在家里处境艰难,同母亲及哥哥的矛盾扩大,一天也不愿多留。她开诚布公地表示,结婚后要马上同丈夫一起到彼得堡去。
男方的父母,起初对这门婚事持否定态度,因为市民舆论姑娘过于活跃。车尔尼雪夫斯基敬爱父母,一贯顺着他们。但这次他宁可使他们伤心,自己的决心毫不动摇。他在日记里这样表明态度:
“婚姻问题上他们不是裁判员。因为他们和我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政治或宗教等问题上,听从他们是荒唐的;在婚姻这件事上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是奇怪的。”
母亲起初试图阻止儿子,但她发现儿子的决定已无法动摇,终于被迫让步了。婚礼定于1853年4月29日举行。谁知母亲没等到良辰吉日,突然得了重病医治无效,撒手西去与世长辞了。儿子也因忧伤劳累,生了一场大病。
婚后不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偕同妻子动身去彼得堡。出发那天来了很多学生,住房的周围挤满了人,他们含泪给老师送行。
2。 定居彼得堡
在去彼得堡的路上,他无时不惦念着留在家中的父亲。老人家年事已高,母亲的去世使他深受震动并万分忧伤,内心的寂寞孤苦可想而知。
车尔尼雪夫斯基旅行途中每到一站,利用短暂的停留必给父亲写一封书信。在楚纳基、阿尔扎马斯、下诺夫哥罗德等地,无论多疲劳,都坚持写的。为了安慰父亲,他报告说他的身体好些了,已不那么虚弱无力,不再发冷发热。
他们行进得很缓慢,只是白天走,晚上停下来歇息。奥莉佳第一次出远门,坐在四轮马车上头晕得厉害。车尔尼雪夫斯基急着快赶到彼得堡,因为韦津斯基正准备出国,希望在他走以前能见面,所以马车在莫斯科只呆了两小时。韦津斯基可能帮助他在军事院校找到教书的工作。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他们乘坐的是刚开通的火车。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萨拉托夫任教的两年,亲眼看到人民的生活多么艰辛。无权、愚昧和赤贫的农民,遭到多么深重的凌辱和痛苦。少年时代他就生活在这里,不过那时他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更不知道打破古老生活秩序的办法。大学时期扩大了他的精神境界。萨拉托夫的两年使他加深了生活体验。现在他决心已定,此生要投身于革命斗争。
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彼得堡,因未找到合适的住房,暂时住在捷尔辛斯基家。捷尔辛斯基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但仍然同佩平及车尔尼雪夫斯基两家保持着亲戚关系。
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以惊人的精力,开始去实现既定方针。
他的主要愿望,是在文学和政论领域大干一番。但这一愿望没能很快实现;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时间,需要作准备,需要和期刊出版界建立联系。除了这个长期目标,当务之急是谋个职务,挣钱养家糊口。在他看来最具吸引力的是在大学当教授,要不就在公共图书馆里当一名学识渊博的图书馆员。但也要一两年的努力才有可能谋取到这种高级职位,而且首先必需取得学位。于是便向教育区的督学提出申请,要求参加硕士学位考试。督学答应他等到明年秋天应试。在这之前,他决定在中等武备学校教书。
他偕新婚妻子来到彼得堡,韦津斯基和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比他所期望的还要亲热。
韦津斯基暂时出国,他把自己在军事学校所教的大部分课程,交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担任。车尔尼雪夫斯基带来了已完稿的《伊帕季耶夫编年史词典试编》,交给了斯列兹涅夫斯基,希望刊登在《科学院通报》上。斯列兹涅夫斯基接受了这部稿子。这部书稿并不能获得物质报酬,按当时的规定,这类著作没有稿酬。但专著的发表会增加他在大学教师中的威望。可以说这是为科学、为他的学术地位投入的无偿劳动。为编纂这部词典历时数载,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啊!现在还得关照词典的排版、校对和印刷,要花大量的劳动。他本人也说:“和别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是最枯燥、最难懂,恐怕又是最费力的一部东西。”
这年夏天,他同《祖国纪事》的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商谈,为这家杂志撰稿的问题。果然,这份杂志的7月号上,刊出了他对《论斯拉夫语和梵语的共同性》和对《诗人文选》两书的评论文章。这两篇书评处女作,标志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评论的开始。
《祖国纪事》在三四十年代是一份很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别林斯基在主持该杂志的评论栏目,把它办成了优秀文学和进步思想的阵地。1846年别林斯基离开编辑部后,由克拉耶夫斯基主持编务,刊物每况愈下今不如昔了。到了五六十年代,杂志完全丧失了以往的战斗性,变成了一份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杂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民主主义立场,当然郁郁不得志。直到1853年秋天,结识了主持《现代人》杂志的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并加盟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境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来到彼得堡,各种各样的事情简直忙不完,根本没有一点儿空闲时间去消遣,给父亲写信也只匆匆数行。为了生计他得拼命工作。在第二武备中学教课,算是本职工作,每月固定收入40卢布,大部分花在伙食和房租上面。所以每月他必须撰写120页以上的稿子;靠稿酬补贴家用。还要设法给私人上课、业余担任《俄语及教会斯拉夫语历史语法》一书的校订工作。此外,他还要准备硕士学位的考试,撰写学位论文。
他的工作习惯是上半月搜集阅读资料,下半月集中力量写作。工作起来寝食俱忘、通宵达旦。妻子奥莉佳为丈夫的健康非常担心。他自己却越忙越痛快,还开玩笑道:
“上帝保佑,但愿天天忙碌;因为在彼得堡没有事做,比任何东西都可怕。”
刚到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生活十分俭朴,每一个戈比都要精打细算。第一年,他们只上过两次剧院。很少出门作客,更少请客。大学时的朋友当中,常来拜访的是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的宿愿这时终于实现了,已经从下诺夫哥罗德迁居来到彼得堡。专为《现代人》杂志撰稿,时而也在其他杂志上发表诗歌和小说。
奥莉佳待人接物表现得活泼、质朴、聪明大方,这使诗人米哈伊洛夫对她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有一次他在她的纪念册里作了一首题名为《肖像》的诗:
和仙女一样,
她的眼神似闪电般地发光;
和活泼的波兰少女一样,
声音如银铃般柔和地响;
和痛苦的小伙子一样,
她脸色是那样惆怅。
你可以不迷恋上她那双美丽的眼珠,
你可以不为她那亲切的话语所打动;
但在她的跟前,
你决计不会去爱别的姑娘。
在斯列兹涅夫斯基家里,奥莉佳也受到亲切的接待。
1853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因词典的印刷事宜,偕同妻子一起到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家作了几天客。奥莉佳很喜欢老师一家人,特别是老师本人和他的母亲。斯列兹涅夫斯基的母亲为学生有这样一个好妻子由衷地高兴。
8月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迁到彼得堡城内、邻近韦津斯基家的一处房子。韦津斯基有三个小孩,房子太挤,所以只好住在他附近。三间宽敞的大房间,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和佩平分占。不错,房租是贵了点——每月20卢布。但没办法,这样的住房少于20卢布上哪儿找!他早就喜爱这条沿河大街,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
佩平在学术界已初露头角。他即将结束大学学业,成绩很好,已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表发了一篇关于18世纪剧作家卢金的论文。教授们预言他前程无量,他那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和渊博的图书知识,使教授们感到惊讶。
就内心世界而言,这对表兄弟相距甚远。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这位未来的教授和院士,精神方面的需求过于狭隘。他那模糊的自由派观点和中庸的社会理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佩平不作他的绊脚石,不与他争吵,不妨碍他,而是专心致志于研究古代语文和文学。因此,他们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日常生活中从没发生过任何冲突,相处得非常和谐。佩平终日坐在写字台边,编纂他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词典,为杂志写学术论文,并准备一篇争取在学校获奖的文章。
有时他们一起去参加尼基坚科、韦津斯基和斯列兹涅夫斯基等人举办的晚会。车尔尼雪夫斯基深知,佩平的成就会使他的双亲感到自豪。便写信回萨拉托夫告诉他们,说佩平那篇关于卢金的论文非常成功。学术界权威人士对这篇文章称赞备至,还说应该为年轻的佩平在刚创办的哈尔科夫大学谋一个职位。
表弟的文章虽好,并没有引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多大的兴趣。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广大读者中传播进步思想。首先是别林斯基的思想,而不是去搞那些历史和文学领域里纯学术的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产生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发现如今人们变得对政治淡漠;已经无法辨认两年前认识的那些人……文学评论不再是传播思想观点的手段,已成为单纯的图书介绍。别林斯基在杂志上的地位,已为图书学家所取代;这些人能背得出珍本的目录,只醉心于咬文嚼字的考证。这位思想活跃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深知,编年史词典或古斯拉夫语的论文,对社会生活最不可能产生影响。他在寻找另一条更能发挥自己力量的途径。
3。 论文答辩会
1854年秋,硕士学位考试并没有如期进行。这件事反反复复拖得令人难受。
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没有放弃搞学术活动的想法,打算考完硕士学位再考博士学位。他本人哪里知道,他的这篇学位论文,因为观点非常尖锐、公然向一切传统观念挑战,引起了大学主管人物的不满。所以对论文答辩的事,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拖延。
9月底,系主任尼基坚科总算抽时间把论文读完,并授权“准备答辩”。校长普列特尼奥夫又把论文送交尼基坚科,征求他的正式意见。等尼基坚科签署了意见,又拖过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21日,系主任才通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学术委员会即将批准打印论文。
“即将”二字乃是模糊的将来时,至于要拖到何年何月,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论文打印好后,依照程序首先呈送给教育部长诺罗夫审阅。部长读了论文大大吃了一惊,认为通篇都是异端邪说,怎么能公开辩论呢?部长大人把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主任严厉批评了一顿,又把此事挂了起来。
转眼间,时间跨入了1855年。
1855——这一年在俄国历史上非同寻常。俄国与土尔其为争夺黑海出海口而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遥远的克里米亚前线,不断传来令人忧虑的消息。尽管萨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表现了无比的英勇,但俄国的败北已不可避免。一时间举国舆论哗然,一致认为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极其落后,政府官僚机构腐败透顶。
著名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写得一针见血:
“祖国到处被廉价出卖!”
社会上人们的政治热情又高涨起来。到处公开议论朝政,批评官方的战报尽在说假话。军队缺乏应有的装备,医院一片混乱。军粮及其他后勤供应濒临断绝。还谈到库尔斯克义勇军,用斧头去对付敌人的远程大炮。连持保守观点的人,也指责起沙皇政府来了。
就在萨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正处于激烈紧张阶段,2月18日老沙皇尼古拉一世突然一命呜呼!
消息传开,进步知识分子欣喜若狂,都把沙皇之死看作农奴制度行将崩溃的征兆。他们认为俄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都期待着革命风暴的来临。
沙皇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撰写评述普希金作品的第二篇文章。他心潮澎拜,用笔在草稿的边上和底下批注:
“此时得到了消息”,“此文于1855年2月18日写毕——最后几行是在人所共知的这个事件的影响下写成的”。
也许当时的政治气氛,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位论文的命运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件原本只需两个月就该完成的例行手续,在拖了18个月之后,系主任尼基坚科终于决定,在1855年5月10正式举行论文答辩会。
终日忙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有机会没忘记给父亲开个善意的小玩笑,好让老人家高兴高兴。他从数千里外寄去一册装订好的论文,和一张答辩会的请帖: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阁下:
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校长恭请阁下,于星期二下午一时,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罗斯语文硕士论文的答辩。无请帖者请勿到会。”
远在萨拉托夫的老父亲,收到儿子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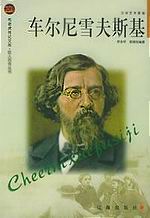
![[戈索夫斯基_魏镇轩_译] 佛里介伊射线封面](http://www.8b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