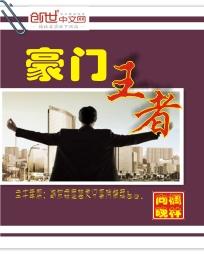民国大文豪-第1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时两人的交谈很友好,但当《访苏归来》出版后,奥斯特洛夫斯基指责纪德是个卑鄙无耻的骗子,欺骗了苏联人民的感情。
和纪德同属法国作家的罗曼罗兰批评了纪德《访苏归来》。
罗曼罗兰是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获奖是《约翰克利斯朵夫》。
1935年他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
因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西方文化界地位极高,罗曼罗兰在苏联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和斯大林等苏联高层有过交往。
他看到了蒸蒸日上的苏联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官僚主义作风,广大农民和一般老百姓的贫困生活。
回国后,罗曼罗兰写了《莫斯科日记》,记录了在苏联的见闻,包括对于斯大林等苏联高层的印象,还指出了高尔基性格上的软弱。
只是,他做出了封存《莫斯科日记》50年的声明。
“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日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
据说是因为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妻子的家人还生活在苏联。
罗曼罗兰和纪德都看到了苏联的问题,也都写了下来,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纪德认为苏联没救了,罗曼罗兰觉得苏联还可以抢救一下,我们应该帮助它。
这恐怕是罗曼罗兰批评纪德的《访苏归来》的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访问苏联的西方学者很多,比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和英国戏剧家萧伯纳。
1920年5月,罗素以非正式成员身份随工党代表团访问苏联,与列宁和高尔基有过面谈,他对苏俄政府的统治感到失望。甚至于恐惧。
他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阐述他的观点。
萧伯纳于1931年访问苏联,回国后。他发表演说撰写文章,赞扬苏联人民的卓越成就。并多次公开声称未来的世界属于社会主义。
中国文化界来苏联的人更多,同样写了不少游记性质的文章,记录了在莫斯科的见闻。
比如徐至摩的《欧游漫录》和瞿秋百的《赤都心史》。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观念对苏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有人极力的赞美,有人大肆的批评,只有多年之后,才能真正判断出是非对错来。
正如纪德所说:“预先带着信念的参观者对光明和阴暗面常常是很敏感的。苏联的朋友常常很不情愿看到苏联的阴暗面,或者,至少说不情愿承认它。因此,往往仇视苏联的人说了真话,热爱苏联的人说了假话,这种情况是太多了。”
林子轩同样是位参观者,不过他是一位来自后世的参观者。
在他的世界里苏联早已解体,成为了历史中的一段记忆,是非对错早有了公断。
他这次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更重要的是陪着冯程程见识一下这个时期的苏联。
林子轩在中国虽然有名气,但还没到引起斯大林注意的地步,如果他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能够和斯大林见上一面。
就算是苏联文学的创始人高尔基也见不到。
因为高尔基自从1921年就到意大利养病去了,直到1928年才返回苏联。
正因为不被重视,让林子轩有了较为自由的行程安排。
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管理人员的介绍,除了一些必要的参观地点和欢迎会议,林子轩可以在莫斯科随意走动,没有限制。
这样就很好,林子轩可不想随时随地的被人监视。
说实话,在莫斯科游行示威,声讨段祺睿政府的暴行只是一个形式,表达大家的愤慨之情,对国内的局势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游行活动到上午就结束了,林子轩和冯程程回到住处休息。
到了下午,当两人想要到莫斯科街头逛逛的时候,有人前来拜访,来人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说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他说是宋子闻安排他来接待林子轩的,并拿出了宋子闻的信件。
林子轩看了信件,的确是宋子闻的亲笔信,说明这个小伙子的身份不简单啊。
“我姓蒋,先生叫我京国就行了。”小伙子自我介绍道。(。)
第三百一十一章 这就是莫斯科()
林子轩一听这个名字就明白了,这是以后的太子啊。
宋子闻找这位未来的太子爷陪着他,恐怕是担心他在苏联闹出什么事情来,不好收场。
蒋京国出生于1910年,在上海受到商人陈果福的照顾。
1920年就读于上海的万竹小学,1924年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
1925年10月,蒋京国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这所学校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此时的蒋京国虽然还是位少年,却透着上海人的精明,言语得体,态度热情。
对待林子轩用的是晚辈对长辈的礼节。
林子轩接受了这个安排,在人生地不熟的莫斯科有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导游也不错。
即便没有蒋京国,他们也要找一位俄语翻译,你不能期望莫斯科的市民会说汉语。
三人都来自上海,自然有不少的共同话题。
按照蒋京国的说法,莫斯科真没什么好玩的,和上海没法相比,这里的物资极为短缺,商店里的商品品种单调,就连服装都是同样的款式。
别说是追求时尚了,只要稍微穿上鲜亮的衣服都会引起非议,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
更谈不上娱乐,戏院里演的是歌颂革命的戏剧,报纸和杂志上是关于大革命的讨论,出版的书籍都是赞扬新时代的。
根本见不到类似于上海的八卦小报。
上海和莫斯科是两个极端,一个是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一个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堡垒。
在莫斯科的街头,随处可见宣传革命的画像和标语。
林子轩带了相机,想要拍摄一些照片带回去,发表在报纸上。算是对于苏联的印象,却被蒋京国拦住了。
外国人在莫斯科拍照要经过当局允许,还要审查照片的内容。否则严禁携带出境。
林子轩没想到这个时代的苏联已经如此戒备森严了。
其实,1926年的苏联算是较为宽松。因为斯大林还没有完全掌权。
列宁过世后,苏联高层内部纷争不断,斯大林的主要对手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是俄国早期的革命家,列宁的亲密战友,被认为是列宁最有可能的接班人,在苏联民众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列宁生前把斗争矛头直指斯大林,并多次在病榻上要求托洛茨基代表他反对斯大林等人。
但斯大林联合苏联其他高层一致排挤托洛茨基。
那些苏联高层为什么选择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呢?
因为斯大林不是天才,他不善写作。也不善演讲,工作成绩平平,但博弈各方都能接受他,大家认为他没什么政治资本,性格简单,容易被操纵。
结果却是,斯大林没成为任何人的棋子,反而是别人成了他的棋子。
在把托洛茨基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赶出苏联政坛,流亡国外后,斯大林于1934年开始了大清洗计划。逐步铲除他的对手,最终大权在握。
也让苏联进入最为黑暗的时期。
和以后的苏联相比较,1926年的苏联可以说是阳光明媚。
除了老百姓贫穷点。国家不富裕,审查制度过于严格外,真没什么好的吐槽点。
林子轩抱着观光者的心态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体验着这个时代的苏联。
莫斯科的市民要比其他地区的市民衣装整洁。
虽然也有看起来像是流浪汉一样的存在,却并不多见,食品商店门口排着长队,其他商店则乏人问津,几乎看不到奢侈品的影子。
他还碰到鬼鬼祟祟试图兜售古董的苏联人。
蒋京国介绍说那是以前俄国的贵族,私藏着一些家族传下来的古董。专门卖给有钱的外国人,因为苏联人一旦发现。就会举报。
或许是林子轩穿的服装过于高档,才引起了这些人的注意。
想要购买也可以。只是要当心上当受骗。
仅仅走了几条街区,林子轩和冯程程就没有了兴致,除了建筑不同,这些街区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景象,没有奇特之处。
通过一座城市的景象就能看出这座城市所承载的文化。
晚上的时候,他们到戏院去看了一场戏剧,讲述的是十月革命的故事,演的很不错。
当然,如果每天都看类似的戏剧也会感到厌倦。
这不是说苏联就没有经典剧目,至少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和《胡桃夹子》等经典的芭蕾舞剧还在上演,只是并不是每天都有。
林子轩对此颇为期待。
虽然他不懂得芭蕾舞,但也愿意受到芭蕾舞艺术的熏陶。
接下来的两天,林子轩先是参观了一所学校,然后听了一场报告会。
这是苏联方面安排好的参观行程,让来访者充分感受苏联伟大的革命热情。
在莫斯科的一所小学,参观之后,校长提议林子轩题词,这是每位参观者都会有的程序。
林子轩想了想,用中文写了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英雄报告会的主角有军人、农民和工人,他们通过各自的职业来展现苏联大革命前后国家的变化,讴歌国家的制度好,讲的声情并茂,热泪盈眶。
报告会结束,又举办了一场座谈会,重点对报告会进行总结和谈自身的体会。
林子轩听不懂俄语,蒋京国在一旁翻译。
这些人大概的意思是听了报告会,被英雄们的事迹感染,浑身充满力量,要为祖国贡献青春,伟大的祖国,伟大的领袖等等。
这时候,苏联人觉得参观者应该发表意见了。
听了这么激动人心的报告会,难道你的心灵还没有被震撼,没有被洗礼,从而成为苏联的坚定拥护者么?
林子轩望着那些激动的面孔,有点不忍心打击他们的积极心。
“我来到苏联这几天,看到了不少问题,我觉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林子轩发言道。
这句话让蒋京国吓了一跳,心想怪不得宋部长交代了要看住这位林先生,就是怕捅娄子。
他非常机警,并没有照实翻译,而是说了一句不相关的话,反正林子轩也听不懂,先把这件事糊弄过去再说。
“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所以苏联现在应该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林子轩继续说道,“既然有初级阶段,那么就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我认为中级阶段是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而高级阶段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如此才算是社会主义。”(。)
第三百一十二章 哲学船()
林子轩把话说完,蒋京国才松了口气。
他真害怕林子轩会说出一番抨击苏联政策的言论,那样后果不堪设想。
他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半年有余,虽说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里学习,但他不是聋子和瞎子,总能通过报纸看到莫斯科的消息。
苏联政府对待**********者绝不留情,莫斯科充斥着肃杀的氛围。
他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觉得林子轩的说法问题不大,便组织了一下语言,把林子轩的发言翻译了出来。
座谈会上的苏联人来自各个阶层,既有工农兵,也有一些社会学者。
对于林子轩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话题没有人接茬。
这个话题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问题,说不好就是路线错误,容易出事。
他们彼此看了看,氛围变得古怪起来。
终于,一位学者说话了,蒋京国翻译了过来,并提醒林子轩小心回答。
“林同志,你觉得怎么才能更快的实现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跨越?”
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回答,涉及到苏联国家政策的走向。
林子轩不能说你们不要实行计划经济,要实行市场经济,还要从西方国家引起先进技术,才能快速的发展,否则就会破产解体。
不说这些建议适不适合苏联的国情,他要是说出来必定会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奸细。
好在林子轩不是政治人物,他是一位家,不需要回答这么严肃的问题。
“我不懂经济,我想这需要苏联人民共同的努力。”林子轩应付道。
这句话让蒋京国和在场的人放松下来,没有人想惹麻烦。
接下来他们自顾自的交谈,也不去询问林子轩的意见了,担心这位中国文学家又说出什么让人惊讶的观点来。
座谈会结束,按照惯例,会有一份会议记录送到苏联的情报部门备案。
这是外国名人在苏联才会有的待遇。每一位苏联公民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外国人的言行。
林子轩并不在苏联情报部门严密监控的范围,只是稍微引起情报部门的注意。
毕竟苏联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林子轩算是小有名气。
会议记录被送到情报部门,有专业人员分析林子轩这段话的意图。这段话有两个要点。
一个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对苏联国内贫困现状的不满。
另一个要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苏联国家性质的定性。
从这段话还能分析出这位中国人认为苏联应该先发展农业,实现温饱,再发展工业。
这是对苏联国内经济发展政策的横加干涉。
这位分析人员觉得问题很严重。已经到了国家性质和革命理论的高度。
于是,他写上自己的意见,把情报呈递给了上一级部门。
上一级部门同样进行了分析,无法判断这位中国家的意图,特意请来了苏联国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来研究这个“初级阶段”的问题。
一些理论家翻阅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最终发现,这个问题马克思没说过啊!
在马克思时代,讨论的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不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