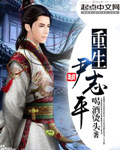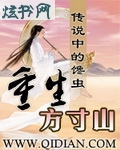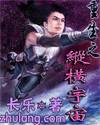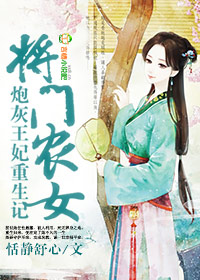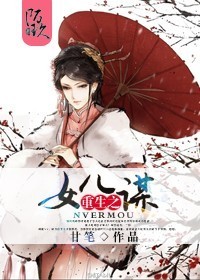重生之大明摄政王-第40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怎么会。”刘泽清潇洒一笑,答道:“我不至于这一点雅量也没有。再说,天如兄是何人,那是我刘某的大恩人,我的家不就是天如兄的家一样?”
“哈哈,言过了,言过其实了。”
“天如兄此来有什么要紧事,是路过北上入京师吗?周先生没有复位,这真是太可惜了!”刘泽清对复社和东林的动向一直很关注,京城的官场变迁当然也是他关注的重点,周延儒没有成功复首辅之位,老朽范复粹却成了首辅,这叫刘泽清微觉沮丧。
“呵呵,鹤洲啊,鹤洲!”张溥很感慨的拍了拍椅子的靠手,微笑道:“天子的心思,瞬息万变,但这万变,不离其宗,你难道没有想到,为什么周挹斋没有现在就被召回京师么?”
“这个,我实在想不到。”
“还是天子要看杨文弱在湖广的所为,如果再立大功”
“那,周先生不是危险了?”
刘泽清大为色变,东林党和复社是他的背后靠山,张溥是最大的盟友,而张溥和周延儒现在也是政治上的盟友,时人尽知。如果杨嗣昌直入首辅掌内阁枢机,周延儒回不去,他的靠山也就靠不住了。
“呵呵,这新功哪里是这么好立的?”
张溥再次呵呵一笑,一副智珠在握的模样,他缓缓道:“去年东林四公子之一的吴次尾从京师回南,沿途所见,触目惊心。河南与鲁南,湖广北部一带,受旱之重,为国朝近三百年来从所未有之事。年逾两年,几乎寸雨未落,赤地千里,百姓户口十不存一,一县一万余户,仅余不足千户,而丁口赋税,仍然不得减免,鹤洲,我问你,这样的情形好比什么?”
“好比是坐在炸药桶上啊”
“嗯,是的,你说的不错。”提起这般惨事,张溥脸上也有一点不忍,但还是侃侃道:“河南南阳几府,还有皖北一带,也是饥民处处。剿贼,武力只是三分,要紧的还是政治清明,地方官所用得人,赋税也要减免几分这事儿,吾辈同仁已经数次上书,言及民间之惨,请皇上加以赈济,不过,效果极差啊。”
这种深层次的交流,刘泽清就有点楞神了,他关注的只是人事层面上的事,对政治和军事上的根本之事,那就缺乏了解和关注了。
其实当时的士大夫也并不是没意味到民间疾苦,也不是没有看到民间惨况,而且也是知道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的危险程度是与日俱增的。在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这三年间,河南一省受灾最重,湖北北部和皖北其次,在这广大的数千里方圆的地方,到处都是饥饿的流民,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土地龟裂,生民十不存一,耕牛种子死光吃完,种种凄惨情状,令人见之而忍不住泪下。
这种程度的灾害,官府就算加以赈济都免不了会产生问题,更何况从十二年底到十三年就开始加征练饷!
七百多万两白银的练饷!
此时三饷已经全部加齐,一共是两千余万两的赋税,这些赋税并不是加在宗室或是外戚身上,也没有加在士绅和巨商的身上,而是加在了农民和普通商人的身上!
天下骚乱,用刘泽清的说便是坐在了火药桶上!
这些事实,张溥并不是不知道,但也是屁股决定立场,他和他的同伙们,也就是那些以直言敢言以清流自诩的士大夫们,上书言事时,极尽百姓之惨,请皇帝减赋减税,修省敬天,但舍此之外,真正问题的他们却是提也不提。
唐宋元明清,这五个王朝,两个是异族建立,三个是汉人王朝,亡国的原因错踪复杂,但只有明朝是亡在财政崩溃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究其根本性的原因,朱元璋设定的体制当然是最要紧的原因,那种各自为政的计税和收税方式,湖州的百姓要自己把粮食送到驻在高邮的卫所军中,海南的某个县要替北京的城防工程烧制砖头五十块,然后自费送到北京,烧砖的部门直接和户部打交道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国家的户部说是天下财计所在,但其实除了收入和支出外,毫无其它的度支功能,没有统筹和精细化管理的职能和能力,在国家承平之时尚且不乏财政危机,在到了天灾和人祸一起来的时候,崩溃也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而在这一链条中,皇室、宗室、勋戚、太监、文官,对财政压力最大的毫无疑问是文官阶层,以及提供文官的士绅阶层。
明末的皇室用度已经十分俭省,如万历年间福王加冠之国用银数百万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崇祯已经尽发内帑,而国库一贫如洗,明明加三饷苦害天下,相同的征收额度,清朝却能平安无事,这其中的奥妙已经是不言自明。
明清更替,最大的不同第一是在宗室之上,数十万宗室的养育费用被俭省下来,而清朝的财政收入在国初就有近三千万两,百姓却能承受的住,却是因为清初就用最残酷的手段打压过江南的士绅,在纳粮额度和商税征收上,清对士绅阶层的征收额度远过于明!
这,就是奥妙所在!
明朝对士大夫阶层的无底线的宽容和放纵,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士绅拥有无限的特权,而且这种特权可以传诸子孙!一代中式为进士,世世代代都可拥不完粮纳税,一个家族一旦出了一个进士,很可能成为百年以上的旺族!
在江南,这种家族制的成功放眼各州府到处都是,两百年以上的旺族都比比皆是,甚至有一些家族在江南的小城中世代把持着中进士的名额,当地的财富,自然也就源源不断的流向那个家族的手中。
士绅不完粮纳税,一旦中举便是如此,只要传出音信,其宗族或是外人就带着田契前来投奔,然后这些人就成为佃户,隐户,从此国家就收不到他们一文钱的赋税,而他们只需给进士主人交纳田租就可以了。
虽然还是要交租,但算起来不需要向国家纳税,不受黄榜和白榜的骚扰,没有力役,这样算来当然比给国家纳税要合算的多!
除了田地,在明朝中后期后,士绅与富商勾结的情况也是十分普遍,大名士和东林领袖钱谦益在无锡一带有大量的庄园,同时还投入股本加到海商里去,海上贸易获得的利益当然十分巨大,钱谦益一次能带两万银子入京,在当时是巨额财富,不经商的话,岂能轻易获得这样巨大的财富?
士绅经商,却不纳商税,明朝的税制复杂而税率偏低,象和买这样的陋规可操作的地方太多,大富商和士绅肯定不会纳商税,过税关时也可以避税,这样就是把极低的税率转嫁到了平民商人身上,在崇祯年间,普通的商人也是遭受着和农民一样的困苦。
三饷加而民间崩溃,其最大的奥妙,也就在于此了!
第1446章 转道()
张溥是复社领袖,很多事情就算知道内情也是不会去多想,更不要提去说了。他张家也是士绅世家,享受着不完粮纳税的特权,交往公卿,把持地方政务,结社议论朝政,明明大明朝政一直握在他们这样的人手中,但所有的错误都是皇帝或奸逆的,而清流却是一点儿错误和责任也没有的。
清朝时言官论政一直受到限制,而很有力的论点就是不要再重复东林之祸,这个观点一直到同治年间仍然很有市场,可见当时东林祸国一事也并非秘密,东林党人们也不是如他们吹嘘的那样清正廉洁,以国家安危系于一身。
“天如兄是说,今年这一年,杨阁老的日子并不会好过?”
刘泽清很敏锐的抓住重点,发问。
“没错。”张溥笑笑,从容语道:“吾敢断言,杨文弱也就止步于此了。要紧的还是张守仁不知道怎么就和方前辈对上了,还和几个监军太监闹翻,这样他在湖广呆的日子不久了等此人一调到辽东,那里是个泥潭啊,他的好运,大约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些事情是最上层的博奕,关系到代表南方士大夫的东林和北方士大夫集团的斗争隐秘,东林党为了给杨嗣昌拉后退也没少搅和,就拿左良玉前后不一的种种表现来说,东林党起的肯定不是良性的向上的作用。
一直到清朝建立,朝中汉官的南北之争也没停过,到清亡乃止。
这些事,刘泽清不会了解,他只是觉得释然。
很多事情,经过张溥的一解释,立刻就是了然于胸,心中也畅亮很多。
“鹤洲,你和兖州这些世家,淮扬商人的事,我不必多过问。登坛拜帅镇守一方者也是难免要有这些事,察见渊鱼者不祥么。只是有两件事,你现在要答应我。”
“天如兄请吩咐。”
“吩咐不敢第一,你要切实掌握好济南,省会首府,观瞻所在,如果出大乱子,大家脸上难看,有话也不好说了。”
“是,请天如兄放心。”
刘泽清知道这是担心他入济南后急着报复,军纪太坏导致城中骚动,出了大乱子后,大家就不好替他说话正位总兵官,所以他立刻答应下来,毫不含糊。
“第二,便是要约束住李青山,他就呆在兖州与东昌府的边境吧,不要继续向北打了。造声势,现在也造的够了。东平州收复,再保临清州无事,漕运平安,李青山被困住,其实灭或不灭,也就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此事还和兖州的一些世家有关不过,都在我身上。”
李青山的造反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有刘泽清,还有兖州不少世家,甚至还有淮扬商人的影子在其中。
此次能运作成功,也是因为朝中担心漕运受到阻隔,特别是李青山隐然有进入东昌府的意思,要是临清受到威胁,朝廷一定会急眼的。
刘泽清将此事包揽下来,张溥就放心的多,因而笑道:“我在这里不多耽搁,和鹤洲兄做完了交代便走京城那边,还有事情哩。”
“天如兄大事要紧,我不敢拦。不过,好歹在这里再住一两天,本城的名士们可是翘首以盼很久了啊。”
“哈哈,不能不能,此行不是直接北上,要折向浮山走一遭。”
“浮山?”刘泽清心中吃了一惊,愕然问道:“天如兄何以对浮山有兴趣?”
现在山东地界,对登莱两府,甚至青州和东昌等地的传闻是甚嚣尘上,兖州一带忍不住要出手,也是因为张守仁的那些庄园。
每庄有过万亩或几千亩地,福利之好,传闻在各地已经是住在天堂一般,很多大户人家的佃客都十分动心,在兖州,已经有几百户佃户退租,跑到东昌去入了张守仁的庄园,在那里,他们的待遇更好,也更被当人看,在江南当佃户,人身依附的关系不大明显,盘剥也不大严重,那里毕竟是衣冠世家,清流当道,所以剥削也讲究手法,不那么野蛮残酷。
在兖州这个地界,孔府和颜府这样的千年大世家在,自己设官厅,对佃户轻重仗责,重责打死的处罚都有,孔府带头,其余的大世家有样学样,佃户被田主当奴隶一样对待的才是普通的情况。
这和登莱青州的情形差不多,所以逃佃之风盛行,张守仁也被恨之入骨。
而这股风潮的源头自然就是浮山,也成为众人注目的所在。若不是张守仁兵马众多,留几万人看家,恐怕还真有人想打浮山的主意。
既然打不得主意,也就敬而远之,张溥想去浮山,却不知道为何。
“吾友陈卧子在彼,所以不得不往啊。”
张溥长叹一声,不欲多说,在浮山的事情上,他和陈子龙已经有了严重的分歧,在这个时代象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清流领袖是时刻关系朝局,对地方动静也十分注意,而保持这种注意的办法就是书信。张溥和陈子龙书信不绝,谈及浮山的信件极多,分歧也是越来越大。
陈子龙与张守仁的赌约还在,一心想在浮山看张守仁搞番薯增产的事情,对别的事,真的不大放在心上。
张守仁发明的浮山生态圈的做法,他已经写成一本小册子,托朋友带回江南,广为刊印。只是书成之后,在江南反响一般,因为生态圈是建立在田地少水缺肥的基础上,当时的江南虽经过一次大旱,但总体来说是不缺水也不缺肥的,所以反响平平,识者寥寥。
而想在北方刊印发行,陈子龙的影响力有限,所以更加困难。
在张溥和陈子龙书信往还的时候,多半都是谈这样的事,张溥一旦攻击张守仁和浮山的情形时,陈子龙就把话题引开,几次三番之后,彼此心里都明白,已经是到了决裂边缘。
张溥此行,也是有挽回和陈子龙友谊的打算,并且,他也是对浮山有了一定的好奇心,是想实地看上一看。
“好,既然天如兄有要紧事,我就不阻拦了,只能摆酒一桌,替兄钱行。”
“这是当然,你这里什么菜式没有”
张溥一句话未说完,也是又咽了回去。
他是随口说的,突然想起来这样说并不妥当刘泽清当年领兵时威信不立,为了震慑军心,也是为了威胁兖州一带的士绅世家给他一席之地,在一次酒宴上,刘泽清下令烹饪人肉来食,还有一次生食人脑。
此事在大明朝野间纷传很久,众说纷纭,有人根本不敢相信是事实。
张溥当然是知道,所以很快把话吞了回去,只道:“不拘吃什么,你我相交贵在知心,酒宴什么都是次要的。”
“是,一如天如兄之吩咐!”
刘泽清对张溥的失言一笑了之,立刻便是吩咐人整治上等席面上来,一个外客也没有找,只是叫自己的兄弟刘源清前来做陪,三人饮到陶然,张溥拒绝了刘泽清的挽留,坐着一顶四人抬的小轿,一个管家,两个长随和两个伺候书房的,一行不过九人,若是往常,兖州往北再往西全是官道,十分方便和安全,现在毕竟不同往常,刘泽清见了不大放心,派了自己的亲兵二十人束甲挎刀,骑着战马相随,送到济南地界后,再行返回。
待张溥走后,刘泽清才站在阶上,淡淡吩咐道:“今日是谁当值守备?立刻派人,将其杀了,再杀他全家,一门良贱,不分老幼男妇,全部给我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