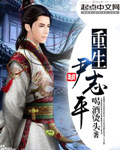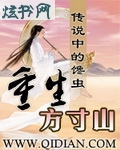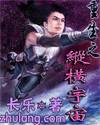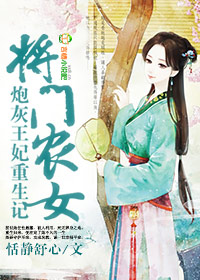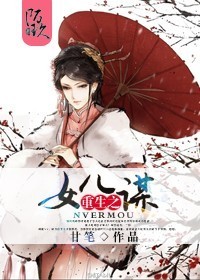重生之大明摄政王-第3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戚也越来越多,这样下去不说相位安稳,就算是人头能不能保住,也是难说的很了。
但薛国观却是自己把话给说绝了,再劝,就是毫无意义的事了。
“阁老但有所需,下官和浮山上下,绝不会坐视。”
一年多来,林文远和薛国观也算相处出感情来了,眼看老薛往绝路上走,话语中也是有十足的感情。
“言重,言重,但真有所需,老夫也会真的开口。”
薛国观将林文远送到门前,叫家人打着灯笼,罕见的送到二门。以他的首辅地位,就算是尚书侍郎或是国公侯伯都没有这样的体面了。
“阁老请回吧。”
“唔,老夫还有最后一句话。”灯火下,薛国观只戴着网巾,一头白发份外刺眼。当了阁臣和首辅之后,额上白发自然而然的增多了,看着林文远,薛国观道:“老夫亦收受过浮山的冰炭敬,但算来并没有过份的地方。现在国事如马车急行,前路已经断绝,如驰往断崖,时刻可能坠落。吾辈纵不能救,亦当挽回于万一。天下鼎沸,最终吃苦的还是老百姓,我观国华是有心之人,寥寥数语,书信不便,就请文远你带回去说给国华吧。”
“是,下官每一个字都记着。”
林文远看着头发花白的薛国观,毕恭毕敬的躬身一礼,终是拜别而去。
回到浮山会馆的时候,留守的人上来禀报:“参将,里头有个姓吴的官儿,说是礼部的主事,已经等了大半个时辰了。”
“哦,我去更衣。”
林文远出入相府都是很随意,穿着便服就行了,但他是以参将身份在京师主持浮山会馆,有官员来拜,当以官服相见。
等他换了袍服,匆忙到正堂的时候,吴昌时也是在灯火之下发呆。
昨天不顺,今天仍然不顺,来拜会的主人又是不在,害得他在孤灯之下,久久等候。
好在浮山这边向来是以招待奢华闻名,上等大红袍加上不停上的冰水果果盘不停的送上来,倒也略解了吴昌时一些焦燥。
“是吴主事,下官有失远迎,又叫吴主事久候,罪过罪过。”
林文远风度是没的说,待人接物都叫人如沐春风,在京城地界也算一个小名人了,他微笑着迎上来,吴昌时的火气也是消解,笑着拱手还礼,说道:“浮山会馆里茶也好,各色水果管够,还有冰镇酸梅汤,要是在这儿还能等着急,这火气未免太大了一些。”
又问道:“不知道林兄去哪儿了,耽搁这么半天。”
“还不是无事穷忙!”
林文远把话题转过,问道:“不知道吴大人这么着急,有什么要紧的事?”
按说吴昌时可以递帖子来,或是写信来,要么就叫人留话,不至于自己在这里久候,留在此处,当然是有要紧事情。
“登莱之乱已经上奏朝廷,本官此来,便是为的这件事。”
吴昌时等的不耐烦,也就不讲什么虚文客套了,开门见山的道:“今日之时,贵上恐怕不免会有小小处分,哪怕是薛相回护,朝廷总不能不讲一点脸面。要想无事,便要有更强更好的理由才行。今不才有小小一计,可渡此难关,不知道林兄有没有兴趣听?”
“哈哈,吴大人说笑了,但请说来,末将一定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记清楚。”
起更之后,吴昌时兴致勃勃的离开了,林文远开始在灯下写信。
这是每天必有的工作,军情处的正经情报,包括今晚的会谈都会有会谈纪要,然后通过军情处的邮传系统往浮山急递,几天之后,张守仁的案头就会有报告呈送。
但那是正经报告,在林文远这里,还有非正式的书信。
以他看来,吴昌时的办法未尝不可一试,但以他的观察,这个复社出身的官员太热衷,品格不高,而且颇为阴沉,又有以书生左右天下大势和驭使武将的骄狂,纵使他藏的十分隐秘,但林文远仍然是能看的出来。
一个庸官加狂生的灵机一动,是不是真的就是大局变幻的开始?
林文远不知道,但他深信,张守仁会做出最合适的判断来。
第1339章 早朝()
八月初三,这一日是常朝的日子,天不亮,宫中与朝会有关的各监寺就是忙碌起来。执扇举伞,象房牵出大象排列在两边,锦衣旗校和散手卫并府军前卫等皇城禁卫一字排开,备显威严,百官从长安左右门进来,于午门处集合,然后再从午门左右掖门进入宫城外朝,在皇极殿下集合。
文官班次于左,武官和勋臣班次于右,泾渭分明。
待皇帝仪驾至,百官山呼拜舞,接着是各部并都督府、都察院等部院寺卿上前奏事。
奏事者,都是官样文章,皇帝在御座上都是不做表示,或是直接答一句“可”,或是“依制办理”便可以了。
等奏事结束后,如无意外,便是可以退朝。
一大早起来,昏天黑地的赶到宫室,做的就是这样的虚样文章,皇帝和百官都以为是苦事,但为了表现出皇帝尊重祖制和勤政,就必须得这么做,而为了表现百官奉公勤谨,亦是必须要早朝。
孝宗年间,皇帝在大雪天曾经降旨给百官免朝,照顾百官辛苦,结果被几个言官上奏一通猛批,说是众臣不以为辛苦,皇帝又何必多事破坏祖制。
这几个二百五当然博得一片称赞声,当然,背地里肯定是娘亲遭殃,还不知道被人骂成什么模样。
但早朝是祖制就这么留传下来,不上朝就是荒淫无道,谁也没有办法。
“皇上有旨意,众臣听着”
即将退朝之时,一个司礼太监捧着金花盏走了出来,站在阶上,昂首宣读最新的旨意。这样的事并是没有发生过,但也是极少。众官精神一振,便是一起听着宣读旨意。
“朕闻春秋之义,以功覆过,方今降徒干纪,西征失律方今。陕寇再炽,围师无功。西望云天,殊劳朕忧!国家多故,股肱是倚,以卿才识,戡定不难。可驰驿往代文灿,为朕督师,出郊之时,不复内御。可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卿其芟除蟊贼,早奏肤功!诗不云乎:‘无德不报’贼平振旅,朕且加殊锡焉!”
平厌分明,胼四骊六,充满诗书礼乐并春秋等上古雅集中的字句接连而出,外朝没有消息,可见是司礼监中的高手写成,先是说杨嗣昌在举荐熊文灿等人的事情上犯了错,然后便是引用春秋的话,叫杨嗣昌以功覆过,接着便是说陕寇再起,王师无功,以杨嗣昌的才干,一定可以剿贼成功,解除朕忧。
旨意中,对杨嗣昌也是十分倚重,以股肱相称,并且表示“不从中御”,也就是说杨嗣昌持节出外之后,皇帝不在宫中干预他的指挥,等贼平振旅,也就是成功班师回朝后,将会有殊荣加赐。
在这样的殊荣之下,所有的朝臣都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杨嗣昌。
以阁臣之尊,自请到湖广视师,无论如何,众人也是敬服于杨嗣昌的果决。此人一离朝,一两年内,哪怕攻讦的奏章如飞雪而至,皇帝也会力挺到底。
而一旦建功,杨嗣昌此前的失误就会被彻底清除,皇帝会对他信任如初,宠眷不衰。
旨意念完之后,就是真的退朝了。
薛国观不得不先做表示,在众人面前先对杨嗣昌拱手道:“大人忧心国事,为解圣忧,自请督师,学生不如也。”
“哪里,首辅大人过奖了。”
次辅范复粹也道:“阁部一至襄阳,半年之内,必有捷音传至。”
“剿贼之事,学生一定戮力而行,绝不使陕寇再复横行。”
“如此甚好!”
大学士之后,各部尚书,侍郎,特别是工部和户部等各部堂官也是纷纷上前祝贺杨嗣昌蒙受皇帝信任,吏部尚书谢升抚须笑道:“阁部以大学士之尊出外,依愚见,官衔当以督师辅臣为最佳,诸君以为如何?”
“妙!”
“甚佳!”
杨嗣昌也在脸上露出笑容:“过誉了,学生愧不敢当。”
“当得,当得,若圣上垂询,必将以此号奉上。”
在众人奉承声中,杨嗣昌却只感觉天威莫测,象今天的旨意就是突如其来,完全打乱了他的打算和计划。他没有自请出外,但崇祯却是说他自请,这其中的驭下手段和表达心意的手法,也是叫人害怕。
在这个时候,多说无益,真惹怒了皇帝,首级难保。
他唯有连连拱手,向大家表示谢意,到最后时刻,也是在众人的奉承下飘飘然起来。
如果真的如大家所说,一两年内剿灭献贼,那么,自己不仅大学士的位子是稳的,进至首辅,真正执掌大明十年的权柄,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当今皇上喜怒难定,刻忌寡恩,从即位到如今首辅已经换了多少任了?除了吏部尚书,怕是没有几个人清楚。
嘉靖年间,严阁老一个人秉政二十年,此后隆庆,万历年间,阁老首辅任职在五年到十年间的也有不少。
到崇祯年间,能任职满一年便是叫一声侥幸了。或许,在自己身上就是可能产生一个例外吧
张献忠凶而狡,曹操罗汝才奸滑似鬼,革、左五营也很劲悍,但杨嗣昌想一想,只要有劲兵听从指挥,以自己的身份,饷械不缺,平贼当非难事。
卢象升和孙传庭都曾经说过,以五千精锐在手,平贼不难。难道以他杨某人阁部之尊,还不如两个督抚?
信心满满之时,杨嗣昌也是突然想起吴昌时的的建议,整张脸都阴沉下来原本是荒诞不经的话竟然是到了要真正考量的时候,这个吴昌时,不简单!
早朝之后,内阁并各部都照常办事,到下午的时候,兵部对登莱之乱的处理意见也是到了崇祯的案头。
崇祯心思也是复杂,原本他看张守仁年轻,也很有忠义之心,所以简直是拿他当第二个戚继光或是李成梁来看,十数年后,调任辽东击奴,可能解决东事的钥匙就在张守仁手中。
但这个将领也果然是走上了跋扈的道路,这一次变乱,明显的就是文官和武将在争权,崇祯心里跟明镜似的。
但张守仁在手续上是毫无问题,各官通奴都有亲供加来往书信,连腊丸都抄出好几个来,抄出来的东虏物件也很不少,证据链是完整的。
兵部的处理意见就是犯官拿问京城由三法司会审,张守仁革职待勘,或是解任调来京师,登莱镇兵由尤世威代管。
这样算是各打五十大板,到了京城之后是怎么个审法,学问就大了去了。
“昏聩!”崇祯看着兵部奏折,看到是职方司张若麒所上,想起他与张守仁的争执,不觉在心中大骂。
现在的武将,岂是容易解任的?若是激出变故,岂不又是多事?当年孔有德之乱,起因不过是一只鸡,要是文官和士绅稍微体量国家的难处,少惹一些事非出来,怕是大明也没有现在这般艰难了。
“传杨先生来!”
“是,皇爷。”
传旨的小太监轻手轻脚的出去了,崇祯心中也是有一点难过的感觉。使杨嗣昌出外督师是他多日的想法,寻常督抚已经驭使不动骄兵悍将,只有杨嗣昌这样身份的天子近臣怕还是能叫那些丘八买帐。
“朕也是迫不得已,若非寇急,朕亦不忍先生离朕左右先生离开后,朕身边亦离不得人。然而宗龙非赞襄之才,先生临行之前,举荐何人继任本兵?”
“臣举荐陈新甲,论才在宗龙之上。”
“朕知之矣。卿离京时,朕将召其入京,继任本兵离京之后,卿还有何需要?”
“伐贼之事,无非得兵将,得粮饷。臣请将督饷侍郎移至近湖广地方,方便将江南并江西粮饷送到湖广。”
“依先生之言。”
“再有,左良玉虽然跋扈,然而其麾下实力最强,兵将最广,虽有小挫,诸镇兵马恐亦未有比左良玉更强者,臣想,乞皇上格外开恩,开复其官,并加授其为平贼将军。”
大明的将军号,最上的当然就是征虏大将军和骠骑大将军,再下是征虏前将军右将军,再下则是征虏将军,再下则是镇朔将军,再下则是征西将军或征南将军,再下则是平贼将军。如游击将军虽言将军,其实是杂号,为最低品。
能加镇、征将军号的,不过是宣府总兵和沐府的征南将军寥寥几家,所以将军号十分珍贵。
张守仁阵斩东虏七百余级,一战斩首近两千级,如此殊功,又有保济南和鲁王的大功,朝廷未封他为总兵官,不过就是加了一个征虏将军的封号,这就是难得的殊荣了。
以左良玉的实力,加一个平贼将军,其实在以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在文官掌权的万历到崇祯年间,却是难得的殊荣。
至于王朝倾覆之前,眼看就要沉船时,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左良玉为宁南伯,后来加到侯爵,到南明时,李定国和孙可望都封国公,爵禄从一毛不拔到一钱不值,也不过就是二十年间之事。
“就依先生吧。”
对此事崇祯不以为然,但也只能答应下来。
几桩大事说妥后,杨嗣昌又提起铠仗,厩马、关防并仪仗,还有随员及调动兵将之事,崇祯无不依从。
从下午时分,一直到掌灯,再到赐便宴,君臣二人,密议良久。
第1340章 八大王()
杨嗣昌出京,在大明是最后的垂死挣扎,最少在对付农民军上头确实是最后的机会。他要对付的不仅是张献忠和革左五营,亦有现在销声敛迹的李自成。
崇祯对他寄予厚望,有所要求,都是立刻答应。
最后时刻,杨嗣昌两眼通红,趴在地上叩首道:“臣,世受国恩,此前寇乱、虏警不断,臣中夜推枕,忧思难解。此次出京视师,远赴戎机,当竭尽全力,为圣人扑灭陕寇,还大明畿内清平,若不效,唯死而已!”
崇祯听到“唯死而已”的时候,心中只觉一寒,一种无依无靠的感觉突然袭上心头。
这么多年,除了对温体仁和周延儒有这种有限的信任和倚靠感外,也就是眼前这“杨先生”算是他真心依靠的人。
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