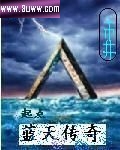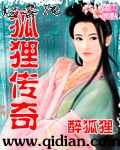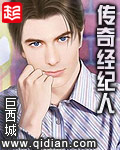陈良宇传奇-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句话,教给战友们,告诉他们如何安全作业,又想出不少土办法,减少近身排除哑炮的危险。这样一来,爆破连的伤亡大幅降低,连队的战士将他奉若神明一般,从来也不让他参加危险的点炮、排炮作业。
这样,尽管劳累,陈良宇在部队的时候,心情也慢慢地开朗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因为毛泽东急于看到所谓三线建设的成就,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基建工程兵甚至连星期天也被剥夺了。一天劳累下来,头挨着枕头,就会呼呼大睡。第二天天刚朦朦亮,又要出工了。几个月当中,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陈良宇受到战士照顾,还可以在工作时间内抽空写信,其他时间,都是处在无休止的劳动中。
偶然有机会,陈良宇也在想,这奴隶一般被发配的日子,何时才能是个尽头啊。
【洗不掉的烙印】
再说陈更华因为“美国特务”的问题,被关押在常州金坛干校政训班隔离审查,白天下地干活,喂猪割草,晚上“深刻检查”,坦白交代“美国”特务的罪行。陈更华也和陈良宇一样,经受了人生头一次脱胎换骨的锻炼。烟斗也不能抽了,只能抽最劣质的纸烟,胖大的身躯,日见消瘦。每天晚上,陈更华都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交代材料,留学美国的经历写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又不能据实而写,只能按照共产党的调子,把美国社会写得一团漆黑,惨无人道。
陈更华在私塾里饱读四书五经,笔下本来十分了得。但是写那些劳什子的交代材料,既不能实话实说,又要写得煞有介事,让专政人员觉得是诚心在坦白交代,着实难为坏了陈更华。这就好比是要写一部历史,但又不能秉笔而书,半是纪实,半是小说,折腾得陈更华夜不能寐,唉声叹气。好在中国古人早就创造了所谓春秋笔法,婉转曲折,既有事实,又有伪托,无非是要满足专政人员的要求,但求蒙混过关,不至于皮肉受苦。这样的交代材料,陈更华却也不知写了多少。
一九六九年,金坛干校的政训班忽然莫名其妙地结束了。陈更华莫名其妙地在牛棚中呆了两年之后,也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对于他到底是否是“美国特务”,既没有结论,却也不再审查,只是把他写的许多交代材料塞入档案中,把他打发回了上海。
陈更华回到上海后,倒是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他以社会闲杂人员的身份,闲居家中。这个时候,他更加想念起了因为受他拖累,而被发配到山沟里的大儿子陈良宇。为此,他不停地给陈良宇写信,让他放弃在部队发展的思想,争取尽快退伍。另一方面,陈更华又整天地走访朋友和熟人,包括他以前修X光机时候熟悉的一些医院,他当买办时候认识的船舶建造方面的熟人,放下架子,曲意逢迎,要把陈良宇弄回上海。
陈良宇得知父亲从牛棚出来,欣喜之余,对自己的命运仍然比较悲观。因为陈更华虽然从牛棚放了出来,但是在案件上没有结论,陈更华所谓的政治面貌仍然是“美国特务”嫌疑。这样,陈良宇的家庭成分,丝毫并没有因为陈更华隔离审查的结束而得到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取得信任。他被永远地打上了家庭成分的烙印,成为被排斥和不能信任的边缘人。
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倍感失落,既没有任何前途,也没有任何未来,只是浑浑噩噩地在部队里充当工程兵奴隶,每天劳作十多个小时,然后在极度劳累中睡去。他的梦中,无数次出现上海的繁华街市,丰富的物产,但是醒来之后面对的却是一些满身汗臭的战士,以及无穷无尽的崇山峻岭。他现在已经放弃了一切理想与追求,只希望回到上海,过上普通人的普通日子。
【回到上海】
陈更华得知自己的所谓“美国特务”嫌疑,影响了大儿子陈良宇的前途,使得他被发配到深山冷沟中成为工程兵奴隶,心中非常难过,也不免大骂SHIT。他对共产党的怨恨,这个时候到达了极点。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该忍还是得忍,该低头还是要低头。所幸他从江苏回来之后,再也没有人理睬他;共产党的街道组织也没有把他管制起来,因此他还是比很多人要幸运。不仅有自由之身,而且可以到处活动。
为了帮助儿子解脱困境,陈更华几乎跑细了双腿。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更华终于转辗通过关系,找到了一条门路。他原来在充当船级社买办的时候,经常给造船厂的大型设备设定安全等级,因此认识的一位小兄弟汪某,正好在闸北区的彭浦机器厂当负责人。因此他一再上门,先送礼物,再套近乎,短时间内把关系搞得非常融洽。汪某也是宁波人,和陈更华倒是相当投缘。正好当时彭浦机器厂因为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因此一片混乱,既没有厂长,也没有党委,只有汪某是临时的负责人,大小事情都由他说了算。所以汪某答应帮助陈更华,如果陈良宇退伍,他可以接收陈良宇。
陈更华关节打通之后,也不耽误时间,一封电报“父病危,速回沪”,发往陈良宇所在的部队。三天以后,陈良宇满面忧伤,风尘仆仆地回到上海家中,却看见其父陈更华满面春风的笑脸。陈良宇错愕之余,马上体会到这是父亲的精心安排。父子两人因此在家中商量了许多天,谋划回到上海的办法。没有几天,陈良宇匆匆起程,随身带了许多高档礼品,特别是当时刚刚在上海面世的的确凉面料等,以及从上海铁路中心医院开具的慢性病证明,回到川西的部队。
陈良宇回到川西之后,没有立即回到连队,而是直接去了团部。在团部给团长政委送了许多希罕的上海产品,然后借口身体不好,要求退伍。陈良宇军校毕业,本身已经是军官序列,但是他事实上又是一个大头兵,没有任何职务。这在部队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陈良宇的家庭成分问题。
陈良宇为了达到退伍回到上海的目的,主动要求以战士的身份退伍。因为按照部队的规定,军队干部退出部队,称为转业,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通常按照部队的官衔安排相应的工作。中国公安、法院系统里面以前的许多文盲警察和法官,大多数是部队的军官退役下来的。而大头兵退伍,则由自己回原籍找工作,国家概不负责。所以如果陈良宇按照军校毕业的军官转业,就由国家统一分配,肯定是回不了上海,天知道会给分配到哪里去。但是如果按照战士待遇退伍,那就可以自己拿着封口的档案袋,回到原籍去找工作。
也许是大批上海产品,特别是西南地区难得一见的的确良布料起的作用,一九七零年七月,陈良宇获准从解放军六七一六部队,以士兵身份退伍。部队不仅没有难为陈良宇,而且还为陈良宇搞了一个热闹的欢送会。许多战友还在会上为陈良宇抱屈,认为白读了五年军校,结果还是以大头兵的身份退伍。殊不知陈良宇为了获得这个身份而窃笑不已。
第六章 小市民生活
【上海彭浦机器厂】
陈良宇终于从部队回到上海,合家十分高兴。陈更华更是十分得意,又开始抽起了他的大烟斗。事实上,陈更华的确是老谋深算,为陈良宇回到上海,安排得非常周详。因为文化革命中陈家房子被没收,合家搬到了静安区的石门路。按理说,陈良宇退伍回到原籍,应该到静安区的有关部门报到。但是陈更华联系好的彭浦机器厂,则是在闸北区。为此,陈更华又找到闸北区政府的有关人员,声明陈良宇乃是从上海铁中入伍的,而上海铁中和彭浦机器厂同在闸北区的共和新路上面,所以陈良宇应该回到闸北区办理手续。
陈更华的这种聪明办法,果然行之有效。陈良宇在闸北区办了手续,如愿以偿地退伍军人的身份,进入上海彭浦机器厂锻工车间,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上海彭浦机器厂最早成立于一九五八年,由上海造纸机械厂、上海锻压厂、上海铸造厂三厂合并,当时称为“上海冶金通用机械厂”,一九五九年又并入华海矿山机器厂、东方钢窗厂和汇通机器厂,正式更名为上海彭浦机器厂。这家国营大厂,最早生产的是电气冷轧机和造纸机,一九六四年由国家统一安排,开始生产推土机和履带式推土机。陈良宇所在的工程兵部队所用的推土机,正是来自上海彭浦机器厂的产品。
上海彭浦机器厂是个国营大厂,地处闸北区共和新路三二零一号,当时属于上海北面的城乡结合部,离市中心较远,地段也相当偏僻。但是这对于陈良宇来说,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回到了热闹繁华的大上海。
陈良宇所在的锻工车间,本身是彭浦机器厂中最脏最苦的。但是陈良宇到工厂的时候,工厂仍然出于混乱的状态,所以工作倒十分轻松。对于陈良宇这样的一个军校毕业的大学生,又以普通退伍军人的身份到锻工车间工作,厂里的同事也感到非常奇怪,经常好奇地向这位个子高高的“小陈”打听。但是陈良宇守口如瓶,从来也不向同事透露他在部队的情况。因此彭浦机器厂的同事们至今不知道陈良宇的背景。只是有一些小道消息,甚至谣言,说陈良宇是在部队里犯了错误,才把官职一掳到底。说陈良宇以前当过营长云云。陈良宇到厂里上班后,十分谨慎,即使听到风言风语,也是一笑了之。
在内心深处,陈良宇已经放弃了出人头地的任何想法。他从十七岁入伍,进入部队共计七年之多,全部的回忆中,不是拼命表现自己,就是因为家庭成分的包袱被歧视和发配,或者是奴隶式劳动,结果化了七年时间,等于是原地踏步,成了一名无权无职,也没有任何政治前途的普通工人。虽然陈良宇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但是他已经毫无进取之心,好比是一只终于把脑袋钻进了土堆的鸵鸟,再也不管外面世界的天翻地覆。
如此一来,陈良宇进入彭浦机器厂之后,为人非常低调。他既不参加党团活动,也不和工厂里任何一个同事有特殊亲密的关系,只是早九晚五,按时上下班。陈良宇到厂报到后不久,陈更华的熟人汪某被撤职,彭浦机器厂重新成立了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新任书记杨某和陈良宇毫无瓜葛,因此陈良宇也没有得到任何照顾。
彭浦机器厂是个数千人的大厂,但是由于陈良宇刻意的低调,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因此到厂数年之后,大多数工人都不认识他。
【爱情之果】
陈良宇最终回到上海,虽然是以退伍大头兵的身份回来,但是毕竟是回到了上海。这对于苦等了陈良宇多年的黄毅玲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喜讯。这许多年,她也随着陈良宇的起起落落,操了许多心,流了不少泪。
黄毅玲祖籍福建泉州,养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基督徒,家庭环境也比较优裕。黄毅玲性格虽然随和,唯独对于陈良宇,自小青梅竹马,情愫早系,竟是始终芳心不变。自从陈良宇离开上海,前去重庆读书,黄毅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给陈良宇写信。逢年过节,如果陈良宇没有回来探亲,必定寄送包裹。陈良宇在四川七年时间,中间探亲回家的次数不多,所以黄毅玲相思之苦,也唯独她自己一个人吞咽。
一九六六年,陈良宇争取加入共产党没有成功,反而因为外调,揭出其父陈更华是“美国特务”,断送前程。陈良宇因为受到打击,困顿异常;不仅从此表现落后,而且自暴自弃,从此不再给黄毅玲写信。黄毅玲事先毫无所知,也不知道为什么陈良宇忽然不再给她写信。但是她毫不气馁,多次到陈家了解原因,并且持续不断给陈良宇写信,询问原因,排解忧愁。几个月之后,陈良宇始终不给她回信。黄毅玲暗下决心,跟单位请了病假,准备亲自前去重庆,面见陈良宇。临行之前拍电报告诉陈良宇,她将前来重庆。陈良宇这才软了心肠,回电报让她不要到重庆去,另外写信解释。此后陈良宇写了上万字的长信,向她倾诉苦衷。两人言归于好。
从小以来,黄毅玲和陈良宇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特别。黄毅玲虽然比陈良宇大了两岁,但是平时都是事事处处让陈良宇“挣面子”,当老大;但是反过来,陈良宇如果有什么挫折和困难,黄毅玲就会象姐姐一样地倾听,为他排忧解难和提供帮助。所以陈良宇不给黄毅玲写信,也仅仅是一时困顿而已;从根本上,他长期以来都十分依赖黄毅玲。
陈良宇身高一米八十,脸色白净,又经受过部队锻炼,爱好运动,年轻的时候堂堂一表,十分吸引女性的注意。黄毅玲身高只有一米六十,长相非常普通,也不算白净,何况比陈良宇大上两岁。从外表来看,两人并不般配。陈更华倒还好,李谋真当年就大有看不上黄毅玲的意思。所幸黄毅玲性格特别随和,处处逢迎李谋真,这才让李谋真没有明确反对。因此从外表上看,其他的人都以为黄毅玲和陈良宇之间,乃是黄毅玲“倒扎钩”钩住了陈良宇,而事实上,陈良宇少年志高,却又横遭挫折,在心理上,一点也离不开黄毅玲的安慰和母性的温柔。陈良宇不管一切回到上海,从普通工人重新做起,固然是因为对个人前途失去了希望,但是同样重要的,也是渴望早日和黄毅玲厮守在一起。
黄毅玲虽然长相一点也不出众,但是家境很好,性格又非常温婉可亲,因此陈良宇不在上海的时候,也不乏倾慕之人。尤其是黄毅玲在卫生系统工作,倾慕之人当中,不乏大学毕业,前途无量的医生。上海华山医院最有名的外科教授,据说当年就是黄毅玲的裙下之臣。但是黄毅玲从未动心。一门心思,都在那个白净,骄傲而又潇洒的陈良宇身上。
这样,陈良宇回到上海后,几乎天天和黄毅玲在一起。黄浦江畔,度过了许多花前月下的美好夜晚。一九七一年,陈良宇虽然才二十五岁,黄毅玲却已经二十七周岁了,上海人算虚岁,算是二十八岁。在风气开放的上海,也算是大龄未婚青年了。但是黄毅玲的性格,每次和陈良宇见面,虽然都想谈婚论嫁,但是却从来也不肯主动提起。按照上海女人的矜持和作派,加上上海女人的聪明和手腕,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