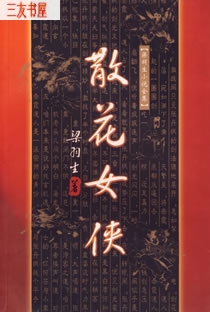散花-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曾有这样巨大影响的年产地,为什么长期不为外界所知?是我们的民间文化学界多年来大多醉心于书斋,不问田野,不问草根,还是它早早地“家道中落”,销形于世了?反正自打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政治功利对待民间文化,要不将民间文化强制地改造为政治口号的传声筒,要不宣布为封建迷信和落后文化,斩草除根。尤其到了“*”,它一定是消灭的对象。
当我一幅幅观赏这些古版年时,发现一幅版印对联,字体古怪,从未见过,比西夏字还奇异,好像是一种字样的谜。韩建峰说当地人能说出横批是“自求多福”,下联是“日出富贵花开一品红”,但上联已没人知道,连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认不出来了。于是,一种“失落的文明”的感觉浸入我的心头。这也是近十年来纵行乡野时,常有的一种文化的悲凉感。现在慈周乡前屯二村的年颇不景气,尽管还有几位传承人还能刻版与彩绘,但由于没人来买,很少印制。近些年,大量的木版被文物贩子以及日本人用很少的钱买走。古版是木版的生命。如果有一天,古版空了,传承中止,这个遗产自然也就完结。
我已急不可耐要跑一趟豫北了,因为我已确信它是迄今未被世人发现的民间古版年的遗存。我根据自己的验嘱咐他们两条:一、先不要惊动媒体,以免文物贩子和收藏爱好者闻风而至,对遗存构成掠夺性破坏。二、绝对不能再卖一块古版给任何人。并对他们说,等我去吧,我会尽快安排时间。还会带一个专家小组进行现场考察和深入鉴定。
在他们离开我的学院后,我开始不安起来。一边打电话嘱咐夏挽群对外要保密,切莫声张,无论如何要等进一步鉴定清楚再说;一边思谋着我什么时候去。
此时此刻,这个乡好比一个田野里的天堂。
三、风雨入乡
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十一月份中国民要在郑州召开“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验交流会”。在这个会上我要解决一系列亟待面对的问题,如解决全国年普查工作一些落后省份的困难,豫西剪纸普查成果的鉴定,全国陶瓷普查以及古村落普查的启动等事。我决定不乘飞机而改汽车。一是可途邯郸,考察磁州古窑的保护情况,顺便看看响堂山的北齐造像。二是为了便于到滑县慈周寨乡,去寻访那个未知的年产地。
没料到,入冬来最冷的天气伴我而行。那天从北响堂的石窟里钻出来,却见大雪厚厚地覆盖的山野与平,纯洁又丰满。我问同行的郑一民滑县在哪里。他举手一指南边。雪尽头,竟然黑压压地逶迤着一片浓密的树林。像浓墨大笔,在天地之间厚重地一抹。那迷人的古乡就深藏在这片黑é林里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豫北古乡探访记(4)
由冀南往中州一路而下,全是雨雪。在车灯照耀中,细小的雨珠雪粒夹着寒风像飞虫一般不绝地扑打在车子前边的挡风玻璃上。车身下边胶轮卷着公路上的积水发出均匀的刷刷声。我忽想此次去滑县别又像前年在武强抢救屋顶秘藏古版那样撞上了大雨,那么艰难和狼狈!
我的担心不幸被证实。我晚间抵郑州,一夜雨未停。上午在民间文化抢救验交流会上谈了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思考,午饭后上了车,雨反而大起来。有一阵子车盖上的雨竟然腾起烟雾,车窗被雨珠糊满了。我心里默默地祷告着,不断地念着一个字:停停。但是我的祷告今天不灵!
一个多小时后,车子从高速下来,拐到一条土路,土路已成泥路。两边的野白茫茫笼罩着初冬的冷雨。此次,随行而来的人不少,有我带来的考察组(孙冬宁和段新培),有中国民的副主席夏挽群、郑一民,也有闻讯跟踪而来的记者。一排黑色的车队渐渐陷入黄色的泥泞里。
后来,车子终于开不动了。有人敲车门,对我说前边的路很糟,车子根本无法行进,只能步行。我推开车门一看吓了一跳。“历史”竟是如此惊人地相似!这景象、这路况,甚至连道路的走向都与武强那次一模一样。也是要从眼前的野路向右拐到一条满是积水的泥泞的乡间小路。树木丛生的村落还在远远的雨幕的后边,像一种梦幻。是一种极其诱惑人的梦幻!
更惊人相似的是,当地人送来的长筒黑色雨鞋是43号的,交给我时说:“这是最大号的。”上次在武强,也是43号的雨鞋,也说是最大号的吗?然而我有上次的验了,我笑着对他们说:“麻烦你们找两个塑料袋儿来吧!”上次在武强就是双脚套着塑料袋进村的。不一会儿,他们找来两个塑料袋,是装食品的,很薄。我心想,糟糕!走不了多少路就得踩破。于是,又开始一次“新长征”雨里泥里入乡!
多亏身边几个朋友和助手帮助,你扶我,否则我早已“滚一身泥巴”了。滑县这里与武强不同的是,脚下的黄泥很厚,很软,不像武强那里,泥水中许多硬疙瘩。大概由于这里是黄河故道之故这区别是我的双脚感觉出来的。但它的好处是泥土细软,脚下的塑料袋竟没有磨破;麻烦是泥太厚,每一步都要用力把脚从泥中拔出来,还要用力把脚踏实地踩进泥里。尤其是我要去的那位韩姓的年传人的家在村子中间,待到他家中,双腿是黄泥,鞋子是冷水,而且举步维艰了。
又见到了魏庆选和韩建峰。他们见我如此狼狈,脸上的表情很不好意思。我笑道:“这雨又不是你们下的。如果是你们下的,我也会来。”他们都笑了。魏庆选说,他安排好了。要我去看的地方,就是韩建峰的家。
可能是前屯二村的百姓知道我们来看年,早在这堂屋的四壁挂满了年,屋中间摆满凳子,坐满了村民。有的抽烟,有的喝水。见我们进来不知怎么对待来客,有的干脆垂着头不说话。显然这是个封闭已久也安静已久的地方。这是间重新盖的平房,房子的间量比老式的房间大,里外两间墙壁挂的足有四五十幅。我虽是头次来到这豫北的老村子,但由于这些我已反复研读多次,早都熟悉,故而感到一种别样的亲切,仿佛在朋友的家里看到朋友。
当韩建峰叫我坐下来歇歇时,我笑道:“还是先看吧!”那次他和魏庆选来天津找我时,我就这样说的。他肯定还记得我这句话,便笑了。
豫北古乡探访记(5)
墙上的大半我都看过,也研读过了。但此刻我还是整体地再看一遍,同时细看其中一些作品。这次整体地一看,此地年的特色更为鲜明。特别是当你感知到脚下这厚厚的黄土是这些年的土壤,这一屋子的老老少少是这独特的艺术集体的创造者时,你就一定会被感动!这挂满墙上的天界诸神不是他们创造出来安慰自己的?这上的对联不是他们一辈辈告诫后人的道德箴言?那缤纷的色彩不是他们理想世界的颜色?这一屋子的老农面对我们这群“闯入者”,大概有些愕然,有些羞怯,有些不知所措而很少说话。但从这些我已看到此地人的所思所想及其共有的地域的心灵。
从这些里,我特别注意到的是三幅。
一是神农像。一个“人面牛首”、身披树叶的老者,被敬奉于面正中。我国有着七八千年历史的农耕社会,神农是开创耒耜生活的始祖。中州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土地,对神农氏的崇拜直抵今日,村民称为“田祖”。除去朱仙镇也有一种神农氏像,这在其他地方是罕见的。它说明农耕文明在中大地上一直长流不断。它具有活化石的意义。另一个“古老的信息”是一些的上端都印着“神之格思”四个字。这四个字来自《诗大雅抑》,是一句诗。但这四个字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的民间版中出现过。但如今本地村民已把这四个字从左到右念成“思格之神”了,无人再解其中意。那么它到底出自什么时候?显然这历史已十分古老了。
二是一幅上有满文的文字。在中国其他重要的年产地,如杨柳青、杨家埠、武强等地的年上都没有出现过,显然这幅是远销东北一带的。别看几个满文文字,足以表明这个产地在历史上的开放与极盛。
三是一幅《老虎》。乍一看似是山东杨家埠的《深山猛虎》,细看却是本地风格。但在构图上,因何与山东杨家埠的年如此相像?连一大一小老虎的姿态和方形图章的位置都和杨家埠的《深山猛虎》完全一样。这使我想起在研究此地年时,也曾对此地的家堂酷似杨家埠的家堂产生过疑问。据韩建峰说,由于此地年远销山东,他们还专门为山东人印制一种那里喜欢的《摇钱树》山东杨家埠年就大量印刷《摇钱树》。这不是属于一种为外地“照样加工”吗?这些都表明此地年曾达到过的极大的规模与影响。它曾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年产地啊。
然而,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历史辉煌?
他们从老人嘴中,也许听说过祖辈的年曾每年向外地卖出上百万张,销售区域不仅覆盖中州,而且东至渤海黄海之滨,西达青海,北抵关外诸省。其实,滑县曾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只不过被遗忘罢了。而历史,只要被遗忘就是一片空白,只要中断就会失去。
今天我们说发现了古乡,也只不过是在把它遗弃之后又重新找到而已,并非真正意义的发现。
从村民口中得知,此地年由于“*”的打击,完全终止制作与使用。“*”后这一地区的年传人曾思图东山再起,但生活骤变,兴趣转移,故而市场始终未能复兴,这一来反倒对这门传统艺术失去信心。近年来,已有一些无孔不入的古?商贩跋山涉水来到滑县各乡各村,收罗年古版。许多珍贵古版已被很廉价地买去。显然现在遗存的古版无法全面地反映历史灿烂的全象了。刚才看到的那幅刻着满文的年,版已叫人弄走,只剩样。还有许多与版,俱不存在。 txt小说上传分享
豫北古乡探访记(6)
版是产地的生命,失去了版就中断了生命。我站在韩建峰家现有的全部不过区区几十种年中间,最强烈的感受是濒危!今天随我同来的,还有许多跟踪报道的记者。今天的消息一旦见报,这个古乡一定会成为新闻的焦点,并很快变成古?商贩们争相夺取的新高地。此时,我已想好怎样向记者们“发布新闻”了。
在记者们的要求下,我讲出我的判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中国古版年之乡,是在艺术上完全独立的年产地,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今天已被遗忘的北方年的中心,因此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存。我将它和北边相距不远的、中最大的年产地朱仙镇比较了一下它们完全不一样!从内容来讲,这里的年与民间的祭祀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在中国年俗中,祭祀是最主要的内容。它体现了古代人和天地之间一种和谐的企望。属于精神生活,不应该把它看做迷信。从绘风格来讲,它与朱仙镇大不相同。比如色彩,朱仙镇有一种紫的颜色,强调黄紫对比,这里的很少使用紫颜色。此外这里的颜色大多是用水稀释过的,半透明的,比较μ雅。但朱仙镇的颜色不加水,基本是色,对比强烈。朱仙镇的年是以套版为主,套版一般是六套版;但这里的年是以单线印刷加手绘为主,比较接近杨柳青的法。在法上,通常是先用深颜色,再加上一点浅的颜色晕染,尽可能地把平面的表现得立体一些。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它把字与结合得很好。在幅的两边配上对联和横批,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适合挂在堂屋正面墙上,显得大方又文雅。这里的在一些边角处喜欢一些兰花和竹子,这些都是文人里常见的题材。从它的内容到它的绘技艺、刻版、构图、文字和的结合,到它的印刷,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艺术体系。所以说,这个古乡的发现是豫北地区民间文化抢救的重要成果。我希望第一个是要保护好古版,这些老版千万不要再卖了。千千万万别卖给外国人了,也别卖给文物贩子。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个东西的价值会渐渐显现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是你们的一个根,祖祖辈辈创造的一个积累,卖掉了就不会再有了。再有,我希望当地政府继续做好普查,细心整理,争取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希望媒体多强调对这个产地保护的意义,不要再它像某些地方那样珍贵的文物刚刚出土就被肆掠一空。
大概我的话打动了随我而来的孙东宁,他是我的研究院一位年轻的美术学教授,他主动提出留下来,住在传承人韩建峰家,深入普查,他说他背来了录音和录像全套设备。我说:“那好,你做好口述实录。同时帮韩家把全部版做好分类、统计和编号。”
孙东宁留下了,我心稍安。在回去的路上,虽然依旧又是冷雨,又是寒风,却不觉得,两只脚顾不得地上是水是泥,以致冰冷的水把鞋子灌成水篓。心中却溢满欢喜。这欢喜无可比拟。
此后两天我在郑州开会,并赴鞏义与安阳一带考察,不时与孙东宁用手机联系。得知他那里收获甚大,做了韩建峰家庭两代传人的口述史调查,查访到这里的乡村数百年来不断变更行政管辖的历史。还将韩家全部版整理成可管理的档案,找出流失古版去处的许多重要线索。同时,同来的摄影家段新培自告奋勇提出要前去助孙东宁。我想,视觉记录必不可少,便请郑州民派车送段新培去了。这几天是入冬来最冷的几天,风雨交加一直未断。不过我对段新培的工作十分放心。在当年抢救估衣街时,他站在风雪飞扬的楼沿上拍摄那条古街的全景。如今古街不存,全仗他的勇气与真情才使历史不是空荡荡地消失掉。
一周后,在我们由豫北到冀南考察广府古城后,回到研究院,着手此次考察滑县李方屯年的材料整理工作,以及中州两地(朱仙镇与滑县李方屯)年的比较研究。此间,正待我频频与魏庆选寻求各种相关材料时,前屯二村的传人韩相然和韩建峰父子来到天津,并带来近半个多月前他们四处搜寻的木版样。大部分属于扇,多为戏曲故事、民间传说和吉祥图案。其中一幅《新女性图》属于民国初期的“改良图”。由此认识到,扇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