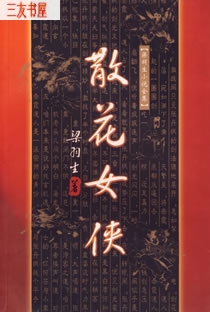散花-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边。人爬出来后,心里犹然惦着那。地震后的几天,我钻进废墟寻找衣服和被褥时,冒险将它挖出来。所幸的是我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细长的装饼干的铁筒里,又搁在书桌抽屉最下一层,故而完好无损。这随我又一起逃过一劫。这与我是一般寻常关系吗?
此后,一些朋友看了这幅无比繁复的巨,劝我不要给那位美籍华人。我执意说:“答应人家了,哪能说了不算?”
待到1978年,那美籍华人来到中国,从我手中拿过这幅的一瞬,我真有点舍不得。我觉得她是从我心里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说她一定请专业摄影师拍一套照片给我。此后,她来信说这幅已镶在她家纽约麦哈顿第五大街客厅的墙上,还是请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制作的镜框呢。信中夹了几张这幅的照片,却是用傻瓜机拍的,光线很暗,而且也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中间抽暇去纽约,去看她,也看我的。我的的确堂而皇之被镶在一个巨大又讲究的镜框里,内装暗灯,柔和的光照在中那神态各异的五百多个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虽是临摹,却觉得像是自己的。我对她说别忘了给一套照片作纪念。但她说这幅被固定在镜框内,无法再取下拍照了。属于她的,她全有了;属于我的,一点也没有。那时,中国的家还不懂得可以卖钱,无论求与送,全凭情意。一时我有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得空空荡荡。它毕竟是我年轻生命中整整的一年换来的!
现在我手里还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中断这幅而去了那幅之后,已没有力量再继续这幅了。我天性不喜欢重复,而临摹这幅又是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况且此时我已走上文坛,我心中的血都化为文字了。
写到这里,一定有人说,你很笨,叫人弄走这样一幅大!
我想说,受?多半缘自于一种信任或感动。但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也来自信任和感动吗?你说应该守住它,还是放弃它?
我写过一句话:每受过一次?,就会感受一次自己身上人性的美好与纯真。
这便是《清明上河图》与我的故事。
醒俗报
几年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李欧梵先生来津看我。那时候,他正对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碰撞时期上海的社会形态发生研究兴趣,因此迷上了那时代上海出版的报。从早期的《点石斋报》到后期的《良友报》,中西交错,色彩斑驳,非鱼非鸟,极是新鲜和奇异。
在我家聊天时,我便拿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津出版的《北洋报》、《玫瑰报》、《华北电影报》等等给他看。他睁着吃惊的眼望着我说:“怎么天津也有这种报?”我笑而不答,又把一匣《醒俗报》放在他手中。他失声叫道:“这不和上海吴友如的《点石斋报》一模一样吗?”
于是我说:“那时,上海与天津一南一北,同为东西文化相撞前沿的城市。社会形态差不多。从桌球(乒乓球)、玻璃*(*)到小洋楼,凡上海有的,天津也有。”
这一来,他对天津的报也生了兴趣,死磨硬赖从我手里“抢”走几本《华北电影报》,还顺手3走一册印着不少周璇和蓝蘋(青)照片的迷你型的小刊《玲珑》。
由清末到民初,中国的社会*,政治软弱,外侮日切,一些有责任感的文化人便站出来,或兴办教育,或立坛宣讲,或创办报刊,主张铲除社会陋习与种种痼疾,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醒俗报》中“醒俗”二字的立意了,那便是要把民众从习惯而不自觉的种种陋习中唤醒,承担起共同兴国的重任。
《醒俗报》和上海的《点石斋报》一样,都创办于光绪年间,也同样使用单面有光的粉纸和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方形开本,每本十张折叠页,每页两面印刷,凡二十图,十天一期。刊物一开始就有鲜明特色。它面向大众,内容全是图新闻,大至时政要事,小到市井信息;识字者看字,不识字者看图,很像大本的“小人书”,物美而价廉,一时颇爱欢。故而很快就改为五天一期,一月六期。
报的主办者是几位新学的倡办者。社址设在西北城角自来水公司旁一座小楼内,后迁到城内广东会馆附近的平房里,条件简陋,但主笔却是津门一位知名的文化人陆辛农先生。
陆先生个子不高,为人爽利,能书擅,喜欢植物学和制作标本,精于小写意花卉。记得我年轻时在国研究会工作,见过他几次。他年事虽高,说话朗朗有声,十分健谈,喜欢开怀大笑。他对津门掌故知之颇多,常在报端发表文章,笔名“老辛”。文章中怀古论今,总是包含许多珍贵的史料细节,观点也很开放,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开明人士。因而他主编的《醒俗报》,自然是内容鲜活,视野开阔了。
《醒俗报》还邀请一位名叫陈恭甫的家作图。陈先生是一位市井名家,善时装人物。这在当时充斥古装仕女和山水花鸟的坛上是很难得的。陈恭甫的很写实。他虽然不像上海吴友如那样精工细致,却密切配合新闻,得很快,半工半写,但极有生活气息。在今天看来,中许多场面,都是今日再难见到的历史生活的图景。
《醒俗报》具有很强的批评性,这是上海的《点石斋报》所不具备的。它始自创刊,每期封面都是一幅“讽”。用辛辣而幽默的笔法,鞭挞丑恶,抨击时弊,特别是直接针砭官场的种种*,在当时是颇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这些直接介入生活与现实的办刊方针,贴近了百姓的所思所想,自然受到世人的欢。尤其当时“漫”一词尚未流行,讽应是最具时代精神的新型种。
也正为此,《醒俗报》历了一次很大的挫折。
1908年初夏,成亲王之子载振赴黑龙视察而途津门,天津南段警察局长段芝贵为了谋求黑龙巡抚职务,用巨金买伶人杨翠喜向载振行贿。这桩“美人贿赂案”惊爆于世后,津门家张瘦虎了一幅讽名为《升官图》这应是中国漫史第一幅反*的漫了。他投稿给《醒俗报》,揭露这一丑闻。刊物的主办人吴子洲胆小怕事,阻挠这一图新闻的发表,因之主笔陆辛农与另一刊物主办人温子英愤然而去。一时此事也成了新闻。
后来,解体后的《醒俗报》改名为《醒华报》。馆址迁至当时的奥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办刊的方针并没有改变,一直坚持着《醒俗报》创刊以来锐意批评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在图新闻上的自由评点,犀利而尖刻,为全国任何同类刊物所不及。此外,还增加了绘图小说、科技常识、趣味猜谜等内容,更符合大众生活的需求。至于封面图案,一直采用讽,风格一如既往。《醒华报》的寿命不短,从清末跨时代地一直办到民国初年(1913年)。
陆辛农与温子英离去后,在日租界旭街德庆里内另办一份《人镜报》,开本比《醒华报》略略横长一点,只是文字采用了新式的铅字印刷。办刊主张和《醒俗报》没有两样,也是用讽来做封面,只是增加了文字版面,更适合识字的人阅读,相对平民性也就差一些。
这样,一时天津就有了两份刊《醒华报》与《人镜报》。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几年,天津出现的这些报,显示了这个城市文化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自愿担当唤醒民众的责任,而且敢写敢,富于勇气。今日读了,仍心生敬佩。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地震给我留下什么?(1)
在我私人的藏品中,有一个发黄而旧黯的信封,里面装着十几张大地震后化为废墟的照片,那曾是我的“家”;还有一页大地震当天的日历,薄薄的白纸上印着漆黑的字:1976年7月28日。后边我再说这页日历和那些照片是怎么来的。现在只想说,每次打开这信封,我的心都会变得异样。
变得怎么异样?是过于沉重吗?是曾的一种绝望又袭上心头吗?记得一位朋友知道我地震中家覆灭的历,便问我:“你有没有想到过死?哪怕一闪念?”我看了他一眼。显然这位朋友没有过大地震这种突然的大难降临是何感受。
如果说绝望,那只是地震猛烈地摇晃40秒钟的时间里。这次大地震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后来我楼下的邻居说,整个地动山摇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喊,叫得很惨,像是在嚎,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叫。
当时由于天气闷热,我睡在阁楼的地板上。在我被突如其来的狂跳的地面猛烈弹起的一瞬,完全出于本能扑向睡在小铁床上的儿子。我刚刚把儿子起来,小铁床的上半部就被一堆塌落的砖块压下去。如果我的动作慢一点,后果不堪设想。我紧抱着儿子,试图过身把他压在身下,但已没有可能。小铁床像大风大浪中的小船那般癫狂。屋顶老朽的木架发出嘎吱嘎吱可怕的巨响,顶上的砖瓦大雨一般落入屋中。我亲眼看见北边的山墙连同窗户像一面大帆飞落到深深的后胡同里。闪电般的地光照亮我房后那片老楼,它们全在狂抖,冒着烟土,声音震耳欲聋。然而,大地发疯似的摇晃不停,好像根本停不下来了,就像当时的“*”。我感到我的楼房马上要塌掉。睡在过道上的妻子此刻不知在哪里,我听不到她的呼叫。我感到儿子的双手死死地抓着我的肩背。那一刻,我感到了末日。
但就在这时,大地震戛然而止,好像列车的急刹车。这一瞬的感觉极其奇妙,恐怖的一切突然消失,整个世界特别漆黑而且没有声音。我赶紧踹开盖在腿上的砖块跳下床,呼喊妻子。我听到了她的应答。来她就在房门的门框下,趴在那里,门框保护了她。我忽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就像从地狱里逃出来,第一次强烈地充满再生的*和求生的渴望。我大声叫着:“快逃出去。”我怕地震再次袭来!
过道的楼顶已塌下来。楼梯被柁架、檩木和乱砖塞住。我们拼力扒开一个出口,像老鼠那样钻出去,并迅速逃出这座只要再一震就可能垮掉的老楼。待跑出胡同,看到黑乎乎的街上全是惊魂未定而到处乱跑的人。许多人*着。他们也都是从死神手缝里侥幸的生还者。我抱着儿子,与妻子跑到街口一个开阔地,看看四周没有高楼和电线杆,比较安全,便从一家副食店门口来一个菜筐,反扣过来,叫妻儿坐在上边,便说:“你们千万别走开,我去看看咱们两家的人。”
我跑回家去找自行车。邻居见我没有外裤,便给我一条带背带的工作裤。我腿长,裤子太短,两条腿露在外边。这时候什么也顾不得了,活着就是一切。我跨上车,去看父母与岳父岳母。车子拐到后街上,才知道这次地震的凶厉。的街面已被地震扭曲变形,波浪般一起一伏,一些树木和电线杆横在街上,仿佛刚遭遇炮火的轰击。通电全部中断,街两边漆黑的楼里发着呼叫。多亏昨晚我睡觉前没有摘下手表,抬起手腕看看表,大约是凌晨四时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地震给我留下什么?(2)
幸好父母与岳父岳母都住在一楼,房子没坏,人都平安,他们都已逃到比较宽阔的街上。待安顿好长辈,回到家时,已是清晨。见到妻子才彼此发现,我们的脸和胳膊全是黑的。来地震时从屋顶落下来的陈年的灰尘,全落在脸上和身上。我将妻儿先送到一位朋友家。这家的主妇是妻子小学时的老师,与我们关系甚好。这便又急匆匆跨上车,去看我的朋友们。
从清晨直到下午四时,一连去了十六家。都是平日要好的朋友。在“*”那种清贫和苍白的日子,朋友是最重要的心灵财富了。此时相互看望,目的很简单,就是看人出没出事,只要人平安,谢天谢地,打个照面转身便走。我的朋友们都还算幸运,只有一位的朋友后腰被砸伤,其他人全都逃过这一劫。一路上,看到不少尸首身上盖一块被单停放在道边,我已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怎样还活在这世上的。中午骑车在道上,我被一些穿白大褂的人拦住,他们是来自医院的志愿者,正忙着在街头设立救护站。他们告我,才知道自己的双腿都被砸伤,有的地方还在淌血。护士给我消毒后涂上紫药水,双腿花花的,看上去很像个挂了彩的伤员。这样,在路上再遇到的朋友和熟人,得知我的家已完了,都毫不犹豫地从口袋掏出钱来。若是不要是不可能的!他们硬把钱塞到我借穿的那件工作服胸前的小口袋里。那时的人钱很少,有的一两块,多的三五块。我的朋友多,胸前的钱塞得愈来愈鼓。大地震后这天奇热,跑了一天,满身的汗,下午回来时塞在口袋里的钱便紧紧粘成一个硬邦邦è头大的球儿。掏出来掰开,和妻子数一数,竟是71元,整个“*”十年我从来没有这么巨大的收入。我被深深地打动!当时给了我几块钱,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事过三十年,已记不清是哪些人,还有那些名字,却记得人间真正的财富是什么,而且知道这财富藏在哪里,究竟什么时候它才会出现。
家尼玛泽仁曾对我说:在西藏那块土地上,人生存起来太艰难了。它贫瘠、缺氧、闭塞。但藏民靠着什么坚靭地活下来的呢,靠着一种精神,靠着信仰与心灵。
个人对信念的恪守和彼此间心灵的抚慰。
大地震是“*”终结前最后的一场灾难。它在人祸中加入天灾,把人们无情地推向深渊的极致。然而,支撑着我们生活下来的,不正是一种对春天回归的向往、求生的本能以及人间相互的扶持与慰藉吗?在我本人几十年种种困苦与艰难中,不是总有一只又一只热乎乎、有力的手不期而至地伸到眼前?
我相信,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大地震的第三天,我鼓起勇气,冒着频频不绝的余震,爬上我家那座危楼。我惊奇地发现,隔壁巨大而沉重的烟囱竟在我的屋子中央,它到底是怎样飞进来的?然而我首先要做的,不是找寻衣物。我已历了两次一无所有,一次是“*”的扫地出门,一次是这次大地震。我对财物有种轻蔑感。此刻,我只是举着一台借来的海鸥牌相机,把所有真实的景象全部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