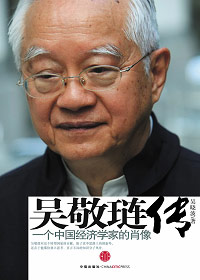吴敬琏传-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一系列活生生地发生在眼前的事情,让吴敬琏对国民党政权彻底绝望。他认为,母亲的宪政理想是虚幻的、软弱的,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才可能拯救苦难的中国。这时候的他,经常因病休学在家,便利用大量的空闲时间读书,他从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中,读到了*的《资本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高尔基的《在人间》以及《鲁迅全集》和巴金的小说等等。这其中,最让他着迷的是19世纪末的俄国哲学家、革命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那本充满了革命激情的小说《怎么办?》是第一本影响了青年吴敬琏世界观的著作,书中的主角、年轻的革命*主义者拉赫美托夫更是成了他的偶像。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一位“科学迷”变成了拉赫美托夫式的左翼激进青年。
卧病在床的吴敬琏还真的为革命做过一些具体的工作。他的二姐夫关在汉原来是《新民报》记者,后来转到美联社,最后当了法新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他在和谈期间一直和*代表团保持着密切联系。代表团撤退后,也利用外国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为共产党做些工作。吴敬琏就跟他合作,他天天躺在床上秘密收听延安广播,然后由关在汉以外国通讯社的名义发表出去。有一次,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用记录速度广播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吴敬琏一字一句地把它记录下来,复写多份在熟人中传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弱不禁风的激进少年(4)
1947年年底,国民政府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陈铭德和邓季惺两人都决定出马参选,他们的一些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小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朋友,如张平江、谭惕吾等非常支持鼓励。而在家庭内部,为了是否参选的事情,却几乎吵翻了天。吴敬琏和关在汉坚决反对,认为这是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邓季惺“相信法治到了迷信的程度”。而国民党的拥趸、邓季惺的三弟邓友德也表示反对,在他看来,邓季惺进立法院就是要去跟国民党作对。处在中间的陈邓左右都不讨好。这一景象几乎就是当时民间立宪人士在中国的一个缩影,稍稍拉开一点,竟还可以看到30多年前梁启超、邓孝可等人的尴尬。
事实上,早在1946年9月,陈铭德就在《新民报》的重庆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了中间者的困顿,他写道:“时至今日,一切都是打的局面,种种都是乱的特征,我们站在中间来办报,谈和平、谈*,来反对内战内乱,当然是不识时务……我们虽然明知这条中间道路是一条左右不讨好的道路,但为了明是非,辨真伪,为了代民立言起见,本报立场将始终如此做法。”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陈邓决意参选。陈铭德竞选国大代表顺利当选,邓季惺竞选立法委员则遭到抵制,她被国民党剥夺了提名候选的资格。强硬的邓季惺当即以自由人身份竞选。她的选区在四川,国民党以散发传单、羁留投票人等办法百般阻挠。邓季惺则亲下基层,四处演讲拉票,《新民报》同仁更是不遗余力,历时三月,最终竟突出重围,高票当选。在当时的600多名立法委员中,像邓季惺这样无党无派者,几乎绝见,她成了各党纷纷拉拢的对象,邓却公开表示,暂不参加任何政党组织,仅以报人身份参政。
独立的邓季惺在立法院果然不见容于各方。进入1948年之后,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共产党,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这时候,发生了“邓季惺大闹立法院”的事件。
6月17日,人民解放军攻下开封,国民党派出空军悍然轰炸开封市区,导致无数平民伤亡。6月24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作中原战局报告,多位河南籍立法委员涕泪控诉。邓季惺联络30多名立委提出临时动议,谴责对开封的轰炸,并要求严禁轰炸城市。第二天,南京《新民报》刊登了立委质询和邓季惺等临时动议的详细内容,一时,举国哗然。在当日的“立法院”院会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们纷纷以“泄露军事机密”为由控诉邓季惺,十多个人叫嚷说:“共产党尾巴已经伸进立法院,一定要彻底追查,把潜伏在本院的奸类清除出去!”
等到邓季惺上台发言的时候,台下仍然是叫嚣和嘘声不绝,未等她开口,就有人大喊:“滚下去,滚下去。”邓季惺一脸秋霜,毫无表情地站在台上,冷冷地观望四周,静待发言。接着就爆发了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场互骂,此事波及全国,史称“《新民报》泄密事件”。
这一事件之后,国民党终于将《新民报》视为眼中之钉,非除之而后快。7月9日,蒋介石亲自写下手令,宣布永久查封《新民报》南京版。接着有消息称,当局已决定将邓季惺逮捕并移交“特种刑事法庭”治罪。10月,邓季惺在友人黄苗子代购机票的帮助下,仓皇逃亡香港,两个月后,完成了善后事宜的陈铭德也化名出走。
从此,这位以“改良立宪”为终身理想的大律师、绝代女报人被“逼上梁山”,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改良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死亡”。而这一切,显然是她的儿子吴敬琏所愿意看到的。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学经济的年轻人(1)
1949年4月中旬,在*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的安排下,吴敬琏随母亲从香港回到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在香港停留期间,陈铭德、邓季惺和赵超构曾仔细策划如何改组《新民报》,以便在新中国“东山再起”,他们曾问夏衍,共产党是否允许私人办报?答复是:当然可以。在解放初期,邓季惺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之后就逐渐边缘化。后来,《新民报》系的结局是这样的:1950年4月,成都版停办;1952年1月,重庆版停办;1952年4月,北京版被政府以2万元作价收购,改成《北京日报》;1953年年初,上海版实行公私合营,易名为《新民晚报》。陈邓的报人生涯从此终结,1953年,他们分别被任命为北京市城市服务局副局长和民政局副局长。邓季惺回忆,她干过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主持修建了北京市的第一个火葬场。
父母的被边缘化,显然没有影响到吴敬琏对新社会的热情。一到北平,他就住进了羊肉胡同的香山肺病疗养院城内分院。到1950年春天,身体有所康复,吴敬琏就回到南京金陵大学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大学学业。很快,他加入了新*主义青年团,1950年暑期开始担任经济系团支部书记、校团委的团课教员。
这种“为建设新*主义社会而学习”的学生生活只持续了一个学期,就开始了抗美援朝的政治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朝鲜人民军占领了南朝鲜绝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直逼平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1月中旬,发生了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美国教授污蔑北朝鲜侵略南朝鲜的事件,学校的党、团组织抓住时机,掀起了影响全国的“反侮辱、反诽谤、反美帝控诉运动”,把群众的仇美情绪调动起来,为抗美援朝扫清思想障碍。①吴敬琏被控诉运动所激发的爱国心推动,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控诉运动结束后,由校团委出面,举办了题为“揭露美国利用文化教育机构进行侵略活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罪行”的展览会,吴敬琏是筹备展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整天忙碌,不知疲倦。1951年2月,中国政府接管了各地的教会学校,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公立金陵大学。
很快,英文从课程设置中取消了,西方的经济学论著被彻底废除。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各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采用的全部是苏联专家编写的教材。
在青年吴敬琏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我在大学期间,除了第一学年还上过几门现代经济学课程外,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当时我以为,掌握了这一套理论和办法,就能沿着苏联的道路,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使我对这些理论观点深信不疑的,并不是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事实材料,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某种信念。这种信念又因我国50年代上半期在新*主义经济制度下取得的成就而得到加强。这种思想脉络大概只有在50年代上半期身历其境的人才会觉得完全合乎情理。”(《中国经济的振兴有赖于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在口述史中,他更进一步说:“因为要反对国民党,所以就要接近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学习共产党的理论。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根本就没有学懂,很多事情并没有学懂。”
学经济的年轻人(2)
从1951年12月开始,为了整肃进城以后愈演愈烈的*之风以及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央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吴敬琏作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学校内清查贪污浪费的活动。例如,参加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的全市高校系统“打老虎”(“老虎”,指的是重点斗争对象)大会。这种会议是大小会结合的,大会上各校竞相报告“战绩”,当场“落实”宽待政策,然后各校再分头开小会“攻心”,迫使斗争对象交代。这种活动不用扩音器,全凭着年轻人高音喇叭似的嗓子,往往一“打”就是几天几夜,不达指标誓不罢休。
所谓“斗争阶段”结束后,吴敬琏被调到校增产节约办公室做结案工作。使他万分惊讶的是,在运动中言之凿凿的贪污案件竟一个也不能落实定案。
吴敬琏在大学里积极参加“打老虎”的同时,邓季惺和陈铭德在北京却成了被打的“老虎”。建国之后,邓季惺出资在北京南长街修建了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现在,这座私宅被认定是贪污《新民报》的钱建成的,职工上门来批斗,强迫他们交代。邓季惺当然很愤怒:“我是报纸的老板,我贪污谁?”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一些老朋友在运动中自杀了,其中包括邓季惺的老师和友人、一代四川船王卢作孚。这是一位社会声望极高、十分爱国的企业家,也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同事。他的自杀让邓季惺非常震惊和不理解,据吴敬琏回忆,他的母亲从来没有跟他讨论过对“三反五反”运动①的看法,不过他能看出她的困惑。对于当时的吴敬琏来说,这样的运动当然是必须的,哪怕父母遭到冲击,也是因为世界观改造的需要。
在忙完“三反五反”后,接下来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俗称“洗澡”运动。改造的对象是大学里的教授,而改造者就是像吴敬琏这样的“革命青年”。表现积极的他,成了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有时上着课,发现老师的讲授有悖《资本论》的理论,就会走上台去,开展大批判。他后来回忆说:“那真是无知狂妄、强词夺理啊!”
就这样,在革命的风暴中忙碌了好一阵子,吴敬琏的肺病又犯了,只好再次住进学校的疗养院。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长相娇小而秀气的女病友,名字叫周南。
周南是云南人,与吴敬琏同龄,比他小9个月,就读于金陵女大的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他们的长女吴晓莲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这样描述这对青年人的恋情—当时,两人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大学生们下乡参加“土改”时,吴敬琏因生病不能去,而周南参加“土改”回来后,也因发烧住进了疗养院。周南在疗养院一直发烧,肺炎转成了肋膜炎,吴敬琏时常过去安慰她说“别着急,我给你唱歌听”,两人就这样熟悉了。周南听当时经济系的同学说吴敬琏学习特别好,记忆力超凡,据说能背下整本《资本论》,这令周南对吴敬琏倾慕不已。周南的一个闺友劝她说:“你看吴敬琏那样,病恹恹的样子,你想以后做寡妇啊?”周南说:“我还是喜欢他,我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
吴晓莲后来问周南:“您就是听人家这么一说,有没有亲自考考他,看他是不是真的能背?”周南答:“没有。我又没有看过《资本论》。”吴晓莲在自己的书中感慨说,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一本《资本论》就能打动一个女人的心。不过有趣的是,到了晚年,吴敬琏在口述史中证实能否背诵《资本论》一事时说:“没有:这事儿是传闻,言过其实。” 。。
学经济的年轻人(3)
尽管能背整本《资本论》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传闻,不过,吴敬琏激进的思想、优异的成绩、善解人意的个性,当然还有俊朗的外形,显然还是深深打动了姑娘周南的心。
1952年9月3日,22岁的革命青年吴敬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全国大学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吴敬琏所在的金陵大学经济系被并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在这里,给他上二年级政治经济学课的是刚从*人民大学受过苏联专家培训的教员蒋学模。蒋后来成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沿用了几十年,据称先后发行了1 800多万册。蒋学模对学生时期的吴敬琏印象非常深,在几十年后的一次聚会中,他指着吴敬琏,用一口浓重的宁波腔说,“他是我的好学生”。也是在复旦的班上,吴敬琏与一位名叫周叔莲的同学十分投缘,这一缘分后来延续了一辈子。
1953年,吴敬琏和周南大学毕业。南京的周南留校当了助教,上海的吴敬琏竟又掉了“链子”,他被检查出肺病未愈,不能分配工作,只好留在学校的康复楼里又乖乖地养了一年的病,兼任康复楼团支部书记。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实在很难想象,在后来,当他80岁的时候,居然还能站在讲台上连续讲课3个小时。
1954年,吴敬琏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研究经济学的第一重镇。当然,比吴敬琏更高兴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