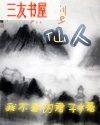上流社会知识竞赛-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琑uth Reichl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本发生在纽约的吃喝版的《 天方夜谭 》——通常,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对于中国读者来说,Ruth Reichl的这本《 千面美食家 》之所以大有看头,就是因为它太符合这个标准了。
Ruth Reichl之所以牛,是因为《 纽约时报 》的餐厅评论比她还牛,她若说了一家餐厅的好话,这家餐厅的预订立马会应接不暇,排到一个月之后去;如果她对一家餐厅说了几句坏话,虽不至于使这家餐厅在评论见报后第二天就关张,但生意肯定会一落千丈。奥普拉在节目中评价某一本书,也会产生同样的效应。如此大的权力,完全是建立在《 纽约时报 》这家百年老店的话语权的基础之上。与中国的媒体相比,《 纽约时报 》在餐厅评论上相对不受餐饮业的商业利益左右( 从《 千面美食家 》的字缝里不难看到,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更受报老板个人价值取向的影响 ),有当年《 大公报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风范。按照张季鸾的办报方针来写餐厅评论,权威的确立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胃口问题了。另外,技术上,为确保评论写得更到位,报社的内部规定是评论员必须对每家餐厅至少暗访三次以上,为了写得能全面,餐厅评论人每次还得约上二三好友共同前往,公款吃喝一轮。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写饭店的(2)
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中国的媒体有的也设有同样的工作岗位,但是绝制造不出话语权大到像Ruth Reichl这样的餐厅评论员。就餐厅评论这个行当而言,其实“四不”什么的还不重要,钱不钱的,在今天也只是小事。在中国这样一个餐饮大国里,我基本看不出餐厅评论的必要。
中国的媒体受众( 接近或类同于《 纽约时报 》的读者阶层 ),谁不是三天两头就在街上找饭吃?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外出吃饭前,就不会( 也没有必要 )养成阅读专业餐饮评论的习惯,靠的是口碑,是各自的实战经验。我有一个在上海做媒体市场调查的美国朋友说,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客户( 广告商或媒体方 )向市调公司支付的费用实在太低,故做出来的数据也不太靠谱,但是,在中国办一本杂志或一家报纸的成本比美国低太多,所以,与其搞什么市调,还不如花钱出几期报纸或杂志,通过“实战”在市场上取得更直接更真实的数据。办报办刊如此,下馆子也是同理,还不如多吃几顿,好吃的第二天呼朋唤友接着再去,难吃的,大不了下次不去了,也就是一拍脑袋一抹嘴的事儿。
老外呢?尤其是《 纽约时报 》的那个读者阶层,在这事上的习惯就和中国人民太不一样了。他们有阅读并迷信餐厅评论的习惯,第一是因为他们不常下馆子,第二是因为餐厅评论里写到的那种馆子确实很贵。据《 三联生活周刊 》报道,皇家苏格兰银行私人银行部门Coutts Group的研究人员曾为伦敦的“百万富翁生活方式”制定过一个标准:一栋五个卧室的独立住宅、两个用人、两辆豪华轿车、一艘游艇、法国南部的一套度假公寓、每年两个豪华假期、两个孩子上私立学校、每周出去吃两次饭——达到以上标准,财产必须超过300万英镑。
我相信,在中国,整副身家哪怕只得三万英镑的人,看到“每周出去吃两次饭”,都会乐不可支,甚至乐到马上就出门去暴撮一顿以示庆祝。这么说吧,既然百万富翁也只是每周出去吃两次饭,那么纽约或伦敦的中产,下一回高级馆子的频率,大体相当于中国同一阶层的人去一趟音乐厅或歌剧院。再反过来换位思考一下,咱们去看场歌剧或者听个演唱会什么的,订票前能不做做功课,出门前能不打扮一番吗?
再打个比方,老外和我们中国人都骑自行车,但后者是日常交通工具,前者是休闲玩具或者专业竞技体育器材。这还不能算是夏虫不可语冰,鱼一辈子生活在水里,当然终生不知水为何物了。不仅中国的广大食客不把下馆子当回事,老派的中国美食家,拿饭馆本身也不当棵葱。王世襄先生的公子王敦煌,论资格,绝不输给纽约的那个女人,可人家在美食书里一上来就声明:“我从小时候就没吃过几回馆子,倒不是没人带我去……什么‘康乐’、‘五芳斋’,这个楼那个馆的,有什么好哇,不就是烹大虾、桃花泛吗?还有什么翡翠羹,有什么可吃的?还不如在家随便吃点什么,不比那几个菜好吃!馆子有什么值得记忆的?做的也和家里差不多,有的还没有家里做的好哪,也就是热闹热闹眼睛。到了我能够自个儿上街的时候,不管上哪儿玩去,多晚,也必得回到家再吃饭。”(《 吃主儿 》)
因此,中国的读者既不必垂涎三尺,更无须妄自菲薄,我估计,二十年之后,餐厅服务员和媒体从业人员的工资都涨了二十倍,北京、上海的餐厅评论员或许也会过上乔装下馆子的日子,在此之前,大可以把《 千面美食家 》当成侦探小说,或者《 性欲都市 》的餐厅文字版来读。
还不如在家随便吃点什么
《 吃主儿 》——看书名,就知道这是一本写吃的书,不稀奇,现如今,在公司里有张凳子坐着就算白领,在城里上过几馆子就算美食家了,有点意思的是,这本写吃的书乃是这样开场的:“我从小时候就没吃过几回馆子,倒不是没人带我去……什么‘康乐’、‘五芳斋’,这个楼那个馆的,有什么好哇,不就是烹大虾、桃花泛吗?还有什么翡翠羹,有什么可吃的?还不如在家随便吃点什么,不比那几个菜好吃!馆子有什么值得记忆的?做的也和家里差不多,有的还没有家里做的好哪,也就是热闹热闹眼睛。到了我能够自个儿上街的时候,不管上哪儿玩去,多晚,也必得回到家再吃饭。”
还不如在家随便吃点什么——口气大,是因为底气足,人家家里吃的,一点都不随便。
作者王敦煌先生,从小( 大约是50年代初 )是由家里一男一女俩破落贵族拉扯大,最起码也是喂养大的。王家的,玉爷和张奶奶都是旗人后代,虽因家道中落沦落到汉人官宦之家打长工,但旗人的那些穷讲究却也病去如抽丝,改也难,尤其在吃喝一道上,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俩“吃主儿”吃过见过,好吃会吃,会买会做,除此之外,“吃主儿”还包括一位有文化有见识并好吃善烹的大玩家老爸,于是就有了“他们仨”不得不说但说了也白说的故事。
钟鸣鼎食之家,无非也是上午上菜场买菜,买完菜回家做饭,和寻常人家一样,该干吗干吗。只是“吃主儿”买起菜来不惜工本,精益求精,烧起菜来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吃起来更是骨头里面挑鸡蛋。从一碗面、一壶茶、一种作料,到一道菜乃至十二人的家宴,无一处随便,无一时苟且。在这个吃喝型家庭里,吃喝风气甚炽,学习气氛更浓,因为老爸在一道“糟煨茭白”上的制作方法和饭店厨师的正规做法有很大的出入,儿子居然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个问题,我产生了一种假想,为证实这个假想是否成立和父亲进行了探讨,果不其然,这种假想果然是成立的。”知道的是“糟煨茭白”;不知道的,看到这话可能以为这是一家子科学家。
这是一本反饭店的书( 某种意义上也是反全球化的 ),反饭店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烹制某款菜,如果是出于商业行为,那必然受到原料供应成本高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而最后影响到这款菜的最高口味。”至于王家家厨出品,则“根本无成本二字可言,料不惜废,食不厌精”。
李渔在《 家庭行乐之法 》一章里说:“世间第一乐地,无过家庭……圣贤行乐之方不过如此。而后世人情之好向,往往与圣贤相左。圣贤所乐者,彼则苦之;圣贤所苦者,彼反视为至乐而沉溺其中。如弃现在之天亲而拜他人为父,撇同胞之手足而与陌路结盟,避女色而就娈童,舍家鸡而寻野鹜,是皆情理之至悖,而举世习而安之。”李渔之行乐,重在伦理,然而与“不如在家随便吃点什么”相比,吾等天黑之前就忙着在街上满世界找饭店饭辙的主儿,岂非那“避女色而就娈童,舍家鸡而寻野鹜”之辈乎?当然,在外面吃饭和回家吃饭一样,都有充分的理由,社会变迁之外,无非喜新厌旧,人之常情,就像李渔分析的那样:“其故无他,由一念之恶旧喜新,常趋异所致。然欲变而新之,自有法。时易冠裳,更帏座,而照之以镜,似换一规模矣。有好游狭斜者,荡尽家资而不顾,其妻迫于饥寒而求去。临去之日,换新衣而佐以美饰,居然绝世佳人。其夫抱而泣曰:‘吾走尽章台,未尝遇此娇丽。由是观之,人之美,饰美之也。倘能复留,为勤俭克家,置汝金屋。’妻善其言而止。后改荡从善,如所云。”
承认人性之局限,态度是正确的,食色之道,其势一也,但是李渔的解决方案却不适用于饮食,最起码,家里的餐桌上很难“时易冠裳,更帏座”地变出王家那么多的花样,在“应接不暇的早餐”一节里,作者提到的早餐有十好几种,除了西式的之外,光是馒头就有烤馒头、炒馒头、炸馒头以及肉丁馒头这四种做法。对于在饭店里“走尽章台,好游狭斜”的广大吃客来说,家里的馒头如果变不出三种以上的花样,改荡从善,哼哼,却又从何改起?
对于读者来说,书中所记之吃食及其做法,真吃起来可能好吃,也可能不好吃,不服气也是可以理解的,众口难调,其实,就是王家仨吃主儿内部,在烹饪的技术问题上也不时会发生“党内路线斗争”。此外,能使“还不如在外面随便吃点什么”者聊以自慰的是,“他们仨”的故事之所以是说了也白说的故事,系因时过境迁,人是物非。作者的遗憾是:“即使自己制作,也很难达到当年的口味了。当年家里制作的很多美食,它们的原料、配料甚至是作料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了,即使再精心也制作不出以前的美味了。”别说家里,就是饭店,往事也只能回味,同类的书,如梁实秋、唐鲁孙和赵珩先生的,又如情况极为相似的江献珠女士所著《 兰斋旧事与南海十三郎 》,甚至明人张岱的吃喝文字,皆成屠龙之术,其对于吾们这些每天开饭时饱受《 每周质量报告 》惊吓的广大读者而言,卖点上若稍有片长寸善,无非忆甜思苦,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吃不如吃不到耳。
请客方知饭店亲
古老的中国智慧这样教导我们说:
如果你想一天不得安宁,你就请客;
如果你想一年不得安宁,你就装修;
如果你想一辈子都不得安宁,你就结婚。
关于“一辈子不得安宁”的另一个版本是:“如果你想一辈子都不得安宁,你就娶姨太太。”娶姨太太当然是旧社会的事,新社会改叫“包二奶”。这个版本,无疑令“一辈子不得安宁”更有说服力,但是不知何故,旧社会里的姨太太们好像个个都擅长炊事,至今仍在流传的一些著名私房菜系或者个别名馔,都出自姨太太之手,莫非,老爷们当年就是为了经常性地避免“一天不得安宁”而选择了“一辈子不得安宁”?
扯远了。就说请客,对于习惯于下馆子的主儿来说,所谓“一天不得安宁”,基本上指的是在家里请客——我看出来了,这三件事之所以都让你不同程度地不得安宁,完全系因它们都是在自个儿家里办的——不信,你改到饭店请客,去别人家装修别人的房子,或者和别人的老婆在别人的家里结婚——当然也不会很安宁,但比你更不得安宁的,肯定就是别人了。
为了把《 天下美食 》杂志上种种好吃的内容落到实处,以飨同好,我们在办公室楼下设了一个厨房,摆了一张可容纳十来人吃饭的饭桌,墙上高悬楠木牌匾一道,上书“天下美食厨房”,乃蔡澜先生之手笔。厨房里一应设备,当初装修的时候,也都是按照饭店里的专业级配置。这一亩三分地,虽不是自己的家,但怎么说也算是杂志社同仁们一个共同的小家——温馨吧,然而与请客吃饭有关的一应问题,也就由此而生。
各式各样的食材,虽然系杂志社同仁或酒肉朋友们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搜罗而来,却因为“天下美食厨房”里没有一个男人是饭店出身,更没有一个女人是姨太太出身,故除了朋友们一时兴起客串,每回在楼下请客吃饭,都要请饭店里的大厨到场“堂会”,尽管炊具一应俱全,但大厨们有时还得另外带几件自己用惯了的家伙事儿。就说今年春天,有同事到浙江安吉报道当地的春笋,顺手就从山上挖了一批新鲜的回来,于是就打算在“天下美食厨房”安排一场春笋宴,以飨同好。于是,当下磨刀霍霍,呼朋唤友,找了一家相熟的饭店,请店家派精于料理春笋的厨师前来现场制作,且以笋为主题,安排了一些配菜。请客吃饭是在晚上,当天下午,我就和助理来到饭店,和老板及大厨专门开会研究,从原材料到调味品,从主料到配料,从主菜到配菜,从配菜到配酒,从餐具到菜单,从现场制作到半成品运输,需要派几个厨师,必须配几个服务员……
两个半小时里,大概讨论了不下三十个细节。大约在讨论到第二十八个的时候,饭店老板点上他这天下午的第九根烟,冷不丁地爆出一句:
“老沈,我看,今天晚上还不如就把你的客人直接请到我的饭店里吃一顿算了。”
醍醐灌顶啊,谁说不是呢?饭店多好哇,什么都有,什么都是现成的,我这是干吗呢?我没日子作了吗,我?
所谓“一天不得安宁”,也只有到了这一天的这种节骨眼儿上、也就是神经和体力双双濒临崩溃的当口,才会想到饭店的种种方便:订座,动动手指;点菜,动动嘴巴;吃喝,再次动动嘴巴;买单,再次动动手指;最后,拍拍屁股走人——同理,在家装修的时候,也会念及酒店的种种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