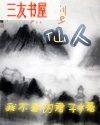上流社会知识竞赛-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以为可以清静一天,不料中午睡醒后一开手机,向我祝贺母亲节快乐的短信便如潮水般涌来,其中频率最高是以下这两条:
其一,“今天是母亲节,我用心灵之纸折成最美丽的康乃馨,献给你的妈妈,祝她幸福、平安!更感谢她养育你,使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朋友!”
其二,“昨天遇到天使在淋雨,我便把雨伞借给了她,今天她问我是要荣华还是富贵,我说什么都不要,只要现在看短信的人的妈妈今天节日快乐,永远健康!”
说实话,阅读上述短信的时候,我的拇指发抖,鼻子发酸,顶上发指,几乎感动到想哭,因为我深深地体会到发信人的一片苦心。首先,今天和一年中的其余364天一样,他们实在是忍不住想用自己的手机向另一些手机发出一个问候短信;其次,他们是那么真诚、那么难以自控地想问候我一声,然而在母亲节这个苦于找不到给我发短信的任何理由的特殊日子里,仍然能挖空心思,煞费苦心,拐弯抹角地发出了那么一条。有条件要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发。
问候别人的母亲(2)
所以,借此机会,我要由衷地感谢所有在母亲节这天给我发来短信的有心人( 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未曾见过她老人家一面 ),同时,更要特别感谢那些移动电话内容提供商( SP )们以及它们的那些不知名的短信写手( 尽管他们中的所有人也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当然,在此也一并问候他们所有人的母亲。
依依不舍地逐条删除“母亲节短信”时,我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绝对是像我这样一天不发短信问候别人就浑身不自在却因某些日子的不方便而苦于找不到恰当理由的人的福音。只要以母亲节的问候短信为样板,就可以进行无限的复制。
样板:“今天是母亲节,我用心灵之纸折成最美丽的康乃馨,献给你的妈妈,祝她幸福、平安!更感谢她养育你,使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朋友!”
下个月父亲节那天,我会抢先发出这样的短信:
“今天是父亲节,我用心灵之纸折成最美丽的康乃馨,献给你的父亲,祝他幸福、平安!更感谢他养育你,使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朋友!”
举一反三:“今天是教师节,我用心灵之纸折成最美丽的康乃馨,献给你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历任老师,祝他们幸福、平安!更感谢他们教育你,使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朋友!”
“今天是端午节,我用心灵之纸包成最美味的粽子,献给你的屈原,祝他幸福、平安!更感谢他从来没有养育你,从而使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朋友!”
一试身手最近的一个机会就在5月17号:“今天是‘五·一七’国际电信日,我用心灵之纸折成最美丽的套套,献给你的手机,祝它幸福、平安!更感谢你养育它,使它成为我手机的朋友!”
发短信上瘾之所以难戒,难就难在其根源乃在于手机这种东西基本上是握在手里的。手是人体最敏感的终端,神经细胞极为丰富,如果你大脑里的感觉中心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的话,通过手传递给大脑的资讯在感觉中心所占的比重约相当于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三个州的总和。因此,既然一机在手,手痒的事是经常发生,而且是一定要发生的。手中有机,心里便时时忍不住要“发射”一下,出于经济和礼俗的考虑,“Hold your fire!”虽然在大多数手机用户的耳边警钟长鸣,不过擦枪走火,也是在所难免。
我认为,在包括抽烟、喝酒、吸毒、赌博这些“老瘾”以及购物、上网、吃药、整容以及发短信此等“新瘾”之中,最难戒除者,一是口头( 吃喝、各种口头禅、粗口 ),二是手头,心头排在末位。也就是说,既有朗朗上口之辞,岂无轻易上手并且爱不释手之物?释手比释怀艰难多了,肚子里不一定非有东西,重要的手心里不可一日缺乏掌握,否则,会令自己和他人感觉上都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就连不食人间烟火的各路神仙,手上大都也要拿着一个物事。由此观之,用手机发短信、讲电话,实乃心和口的超完美组合,虽然手机数量尚未达到人手一册有多的红宝书的水平( 总印数50余亿册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有史以来最难戒的瘾,比开会还凶。
博 客(1)
庄雅婷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博客,那一年是猪年。在鸡年的年末,我自己也成为了博客。狗年再次相见,乃遂出“江海相逢客恨多”之感慨。趁她出书,正好把这档子“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混乱感觉理上一理。
老美最早玩的博客,主要功能不是自我表达,而是个人化的新闻发布以及对资讯和知识的过滤。但据报道说,在中国的博客却以“袒露日常私生活的内容”为主 —— 很显然,Blog作为Weblog( 网络日志 )的简称,在中国已经被汉化为日记,Diary —— 当然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很多人的日记不是早就被写成著作了吗?
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博客。在我国,所谓博客,其实就是一个写日记的人。日记历来只有两种:绝不可给别人看的和非给别人看不可的。其间的区别,更多是体现在对于日记本在物理处置方式( 硬体 )而不是内容( 软体 )。前一种,类似交给组织的申请或揭发材料,甚至给广大群众看的大字报;后一种,属于自娱自乐加自省自强型的绝对隐私,拼老命保密,一旦被人撞破,铁定恼羞成怒,翻脸是轻的,严重的会造成青春期心理创伤,一辈子都挥之不去。很显然,麻烦属于后者。批评博客不够地道的人,总爱举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他老人家从小酷爱写日记,婚后最大的烦恼,就是防止托太偷看他的日记本,于是一个想方设法地藏着掖着( 书架后,靴子里,存银行 ),另一个则千方百计地寻觅搜索,双方常常大吵大闹,女方曾为此离家出走,跳河,吞鸦片,威胁用铅笔刀及其他利器自残,甚至在书房里开枪。但最后的胜利属于托翁,临终前把日记本付之一炬( 下线并且格式化硬盘 )。后人能看到的只有托太日记,相当于“托博”上的一堆评论和留言,而且都是用同一个ID发的。(《 托尔斯泰夫人日记 》)
顺便说说,高度怀疑托翁与男秘书“断背”的托太有一次确实在托翁的皮靴里找到过他的日记,也确实在本子里粘了个纸条留言道:“让善良的人们来读读他的日记,看他是怎样和何时曾对我献殷勤的吧……当时我的列沃奇卡就是这样的,而且长期是这样的。现在他是切尔特科夫( 托秘 )的人了。”
此外还有两种分属于以上两个大类之下的子项。一种是以后要不要给人看或会不会给人看到,写日记的人一直没想好或吃不太准的,因此就有了像鲁迅日记中“夜濯足”那样的暗号,令后人聚讼不休;另一种,系只给指定者看的限量版。虽然《 莎菲女士的日记 》作为一部日记体小说非给人看不可,但小说中日记的读者,却有明确的指定性:“自然,这日记,我是除了蕴姊不愿给任何人看。第一因为这是为了蕴姊要知道我的生活而记下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二来我怕别人给一些理智的面孔给我看,好更刺透我的心;似乎我自己也会因了别人所尊崇的道德而真的感到像犯罪一样的难受。所以这黑皮的小本子我许久以来都安放在枕头底下的垫被的下层。”至于莎菲女士后来之所以又扩大了指定读者范围,系因“苇弟近来非常误解我,以致常常使得他自己不安,而又常常波及我……我无法了,只好把我的日记给他看。让他知道他在我的心里是怎样的无希望,并知道我是如何凉薄的反反复复的不足爱的女人……”
博 客(2)
人为什么要写日记( 博客 )?答案也有两种:一、心里有话但不方便跟别人说。托翁尝言:“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这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秘密,别人不该对它有任何要求。”又借《 复活 》里聂赫留朵夫的行为加以佐证:“这天聂赫留朵夫探监始终没有成功,就回家了。想到明天将同玛丝洛娃见面,聂赫留朵夫心情十分激动……内心好半天不能平静。他一回到家里,立刻拿出他好久没有动过的日记本,念了几段,就写了下面这些话:‘两年没有记日记,原以为再也不会干这种孩子气的玩意儿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孩子气的玩意儿,而是同自己谈话,同人人身上都存在的真正的圣洁的我谈话。这个我长期沉睡不醒,因此我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主哇,你帮助我!’”
其二,心里有话,不方便或不舍得跟自己说或只跟自己一个人说。如“专以示人”的曾国藩、胡适之日记,又如《 围城 》里的方翁“……精神上的顾影自怜使他写自传、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这些记载从各个方面,各种事实来证明方翁的高人一等。朋友来了,翁常把日记给他们看……”。
博客作为一种电子版的私人日记,性质上介乎于“既可以给你看,也可以不给你看”之间。技术上,日记的主人牢牢掌握着随时向访问者关闭或者开放的权利;动机上,则游走于“给人看”和“给上帝看”,甚至可以培育出“没话找话”的精神境界。不论是把有价值的毁坏给“蕴姊”们看还是把无价值的撕破给“苇弟”们看,博客们都玩得得心应手。
非但如此,“评论”、“留言”以及博客主人对以上两者的回复,更开创出人类日记史上空前变态的局面,即偷窥和被偷窥双方可以进行持续的讨论。这种局面已经非常接近齐泽克对“受虐狂态度的基本悖论”的描述:“当他们最终完成严格意义的性受虐狂游戏时,性受虐狂经常地保持一种反思性的距离;他永远不会真正地付出自己的感情或者完全地在游戏中放任自己;在游戏中,他能够突然采取导演的姿态,发出准确的指令( 在这个点上多加一点压力,重复那个动作…… ),从而丝毫不‘破坏幻觉’。一旦游戏结束,性受虐狂者会重新采取一种令人尊敬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并且开始用一种平常的、事务性的方式同至高无上的贵夫人谈话:‘谢谢你的帮忙。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见?’” ( 齐泽克《 快感大转移——妇女和因果性六论 》)
为了不至于陷入这种过于激情化的悖论,我通常不回复任何评论和留言,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这个游戏的好玩,即:“我知道你在偷窥,但是我假装不知道——我认为,这就是博客、尤其是庄雅婷这类博客的终极乐趣所在。这种快乐,只会抱怨“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日记,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的托尔斯泰们永远体会不到。每一次看博客和写博客的时候,我的耳边都会响起李嘉欣在《 堕落天使 》里的这一段旁白:“看一个人丢掉的垃圾,你会很容易知道他最近做过什么事。每次他都会来这个酒吧,看来很喜欢这里的清静。有时,我会坐在他坐过的位子上,因为这样,我好像感觉和他在一起……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我知道怎样可以让自己更加快乐。”
我怀疑,不管是写哪一种日记,也无论是哪一种写日记的人,潜意识里的快乐都是一致的。猫捉老鼠,人毕竟是传播的动物。换句话说,如果托太不是那么执着地要看老公的日记,托翁的日记说不定就不会记得那么勤,内容可能也要空洞乏味得多。一个人有了日记( 隐私 )还不够快乐,缺了潜在的读者,快乐就不会完美。在这个意义上,托翁的快乐大于鲁迅,鲁迅的快乐高于莎菲,而庄雅婷以及万千博客们的快乐,则远在他们之上。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你的明白?
有声电影发明以后,电影里的人不仅开始说人话了,而且,同一部电影里也开始出现说着各色人话的各色人等。对白里之所以会蹦出几句外语,通常是为了渲染某种异国风情,一般也只是做个引子,点到为止。段子说,英语作文课,老师出的题目是“当黑羊碰到白羊”,起首提示曰:“One day the black goat meet the white goat on a bridge……”
一中国小学生偷懒,灵机一动,挥笔写道:Then the black goat asked the white goat: “Can you speak Chinese?”The white goat answer: “Why not!”
接下来,羊儿们就全程以中文问答了……
电影里对外语的处理,基本都是这个路子。好莱坞电影里偶尔冒出几句西班牙语,都会打上英语字幕( 每到这种时刻,台版HBO的中文字幕就会忠实地同步出现“西班牙语”四字 ),但毕竟也就只限Then the black goat asked the white goat,接下来,一概以英语对答如流。对中国电影观众来说,电影里的外语可以被分成两类,即外语原版和“译制腔外语”,后一种类别,即不管是“他好像说了世界革命万岁”(《 列宁在1918 》,俄语 ),“嘿,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叶赛尼亚 》,西班牙语 ),“一直向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追捕 》,日语 ),除早期译制作品都有明显东北腔之外( 主要都是电影里苏联人,也包括《 牛虻 》里的意大利愤青 ),在声调上一概都表现为一种让中国观众深信这就是从老外嘴里说出来的充满了外语情调的现代汉语。
此外,中国电影里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外语,即日本鬼子说的话。抗日片里的鬼子,有时也讲日语,但一般只讲一两个短语,剩下的不是交给翻译官处理,就是改说中文,再佐以语气、表情、身体语言及剧情上下文,观众完全明白。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电影里的鬼子都爱讲一种“协和语”,即满洲国时代日本在东三省推行殖民教育时使用的一种以汉语为基础,混入日文词序的杂凑新语,是一种带有胁迫性的东北“洋泾浜”。在抗日片的影响下,“鬼子话”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的亚语言,王朔曾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