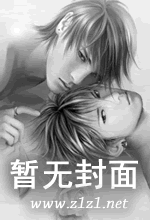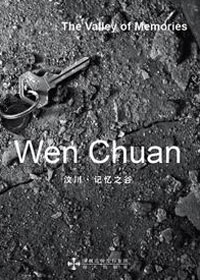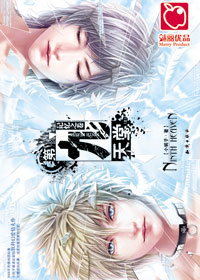藏书·记事·忆人-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长者之风,山高水长。虽然汪老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品德、修养,他的睿智、渊博,仍将垂范后世,激励来者。
。。
路甬祥、韩启德、徐匡迪的签名书
院士从政:路甬祥、韩启德、徐匡迪的签名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时代里,一批在科学技术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院士走进了我国领导层,徐匡迪、路甬祥、韩启德就是如此。由于这样那样的机会,我和他们都比较熟悉,因此,在他们的著作出版后,我都得到了他们的签名书。
。。
为国家创新体系铺路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德国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位来自浙江大学的年轻学者,正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攻读流体传动和控制方面的博士学位。谈话中,他提到浙江大学分给他一套不大的房子,他很是感激。不久后我就听说,他的创新性技术成果,同时获得了欧洲专利局、美国专利局注册,改变了沿用上百年的传统方式,推动了液压技术的进步。他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读取了一般人要5年才能获得的工程博士学位。德国方面很想把他留下来从事科研工作,但他客气而坚决地谢绝了。
我当时想,他的心中肯定有一个外国人无法理解的天平——祖国的一套小住房,要胜似国外的宽敞住房,同样,国外的酬金哪怕再丰厚,也比不上祖国的微薄薪金。因为,在他心中,任何事务只要与祖国联系在一起,哪怕原本轻若鸿毛,也会立即重逾千钧。
1997年我参加了党的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再次遇到这位当年旧识。畅叙过往,知道他回国后很快在浙江大学创建了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流体传动控制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之一、国家教委首批开放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完成了几十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他就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路甬祥。
在十五大报告起草期间,他多次提出知识经济时代,要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思想。后来,我知道,从路甬祥担任科学管理领导工作之初,就开始研究和倡导国家创新体系建设。1997年,55岁的路甬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成为郭沫若、方毅、卢嘉锡、周光召之后的第五任院长。上任之初,路甬祥就将“知识创新工程计划”提交中央。1998年2月,中央批准了科学院呈交的《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并把试点工作交给了中科院,这使中科院成为研究国家创新体系的排头兵。
此时正值世纪之交,20世纪科学技术取得了哪些辉煌成就?20世纪的科技创新有哪些规律?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文化、经济因素促进了20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破解这些问题,有助于缕清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有鉴于此,从1999年开始,中科院开始以“百年科技回顾与展望”为题,边总结边作报告。这是一项系列报告活动,其高潮是中科院建院50周年之际,面向社会举办的科学报告会,当时有包括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在内的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袂出席,一时盛况空前。
2001年9月,路甬祥将他准备演讲稿时搜集到的资料、图片,连同他的一些思考结果汇总,出版了一本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书《百年科技话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25日签名后赠给我。
路甬祥性格平和,很好相处。我邀请他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高级顾问,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有些学会的外事活动要请他参加,他在百忙中总是尽量抽出时间。至于是以学会高级顾问的身份,还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他总是听从我们的建议,随和而大度。当然,我也曾受他邀请,到中科院就新军事变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演讲。但愿我的演讲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
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路甬祥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要勇敢地生活,做生活中的强者”(1)
1999年,正在致力于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路甬祥在为“中国中青年院士文集”写的序中这样说: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21世纪,中国将要在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科学和教育的腾飞,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沿着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的轨道不断前进。中国科技界,包括正在成长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应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韩启德院士文集》是“中国中青年院士文集”中的一本。
我是通过韩启德的夫人袁明和他相识的。早在1992年12月,我在一次宴请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丁时,袁明也在场,当时她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袁明和哈丁将他们合编的《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签名赠给了我。这本书是中美两国学者对1945-1955年间美国对华政策、国共两党对美政策、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局势等问题共同分析和研究的成果,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运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研究了导致中美关系敌对僵持的复杂原因,得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结论。这本书,使我对袁明的学术水平有了很高评价。后来,我受聘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而袁明恰好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因此,我就常常将她称为“领导”了。
通过袁明,我认识了韩启德。2002年5月5日,在一次宴会上,袁明将签名本《韩启德院士文集》赠送给我。
收到这本书后,我照例概略地浏览一番内容。韩启德长期从事心血管基础研究,在肾上腺素受体领域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公认,因此,这本荟萃了韩启德代表性论文的集子,也主要围绕这一领域,专业性很强,读起来难度很大。但是,《韩启德院士文集》卷首有一篇万余字的学术性自述,既讲述了韩启德的成长历程,又讲述了他的学术经历,细读之后,让人不禁对他的奋斗精神大为钦佩。
早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韩启德就立下了从医之志。那一年,韩启德先是得了猩红热,刚好一点,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炎,他昏迷了三天三夜,被抢救过来后,又住院三个星期。用韩启德的话说,当时的医疗条件虽然有限,但护理工作“极其完美”。由于他必须绝对卧床,所以护士就从服药到吃饭全部喂到口,以至于他出院后,永远忘不了这些白衣天使了。巧合的是,7年后,当他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时,报到时体检的地方居然就是他当年住院的地方。
1968年底,在持续高涨的“文革”浪潮中,韩启德大学毕业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被分配到陕西临潼,成为一名赤脚医生。早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为自己立了座右铭“要勇敢地生活,做生活中的强者”,立志要成为一个能够战胜自身缺点的人。面对缺医少药的农村医疗状况,韩启德用上了自己全部聪明才智。
刚到农村的时候,韩启德只在学校学完基础课程,临床课根本没有系统学过。当时他所能做的只有仔细观察病情,并对照病情翻阅从上海带去的有限几本教材。遇到危重病人,他经常亲自护送他们到大医院救治,然后自己也留下来学习大医院医生的治疗方法。门诊看过的病人,只要他没有把握,就骑着自行车上门随访。靠着勤奋和自学,等到他离开农村的时候,方圆几百里都知道了这样一位“韩大夫”。他不但能够做白内障、鼻息肉、扁桃体、阑尾炎、肠梗阻、疝气、大隐静脉曲张、计划生育手术等,还能做胃大部切除、胆结石和甲状腺手术,甚至可以开展兔唇修补等成形手术。由于不少农民习惯于中医诊治,他又自学了中医中药和针灸,掌握了中西结合的治疗手段。他也不满足于农村原有的简陋医疗条件,陆续创造条件,建起了手术室、化验室、心电图室等。
艰苦的环境,对于意志薄弱者来说可能意味着坟墓,但对于意志坚强者来说,却是磨石和熔炉。韩启德说,在农村行医10年,他为无数病人解除了病痛,成为一名备受群众欢迎的全科医师,然而更重要的是增长了学习和工作的能力,尤其是如何克服困难,创造条件,打开工作局面的能力。
“要勇敢地生活,做生活中的强者”(2)
1979年至1982年,他在西安医学院攻读研究生。1982年至1985年在北京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担任教师。1985年至1987年受邀到美国埃默里大学药理系担任访问学者。在美国,他先是从事神经肽Y(NPY)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随后转到α1-肾上腺素受体(α1-AR)亚型研究中,在国际上首先证实了α1-AR包括A、B两种亚型,引起巨大反响。1987年,他谢绝许多美国教授的邀请,回国开始白手起家地创建实验室。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有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唯一的仪器是借来的一台多导生理记录仪。几年后,这个试验室已经有一千平方米面积,上千万元固定资产,数百万元科研基金。
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韩启德开始担任行政职务。他先后担任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欧美同学会理事会会长等。2003年3月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6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
匡扶正义、迪吉平安(1)
1984年5月的一天,在英国BSC的Reby厂,一位中国工程师和英籍厂长争辩起来。
“现在必须马上停止钢包喷吹处理,否则可能冻包。”中国工程师认真地说。
英籍厂长凑近操控室自动测温记录看了看,说:“没问题,温度超过了1650摄氏度。”
但中国工程师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动测温也有可能不准,请相信我。我用炼钢镜做过无数次判断。”
他们争辩的内容,是这炉钢是否达到了合同规定的1650摄氏度以上。这炉钢将用于生产能够抗硫化氢腐蚀的厚壁钢管,根据技术要求,其硫含量应低于,因此在采用喷射冶金过程处理时,出钢温度应高于1650摄氏度。现在,操控室自动测温记录显示,炉内温度已经达到了规定标准。但这位中国工程师用自带的炼钢镜看了之后断言,温度只有1600摄氏度左右,甚至更低,于是他提出停止钢包喷吹处理。
“但愿这次是你的眼睛不准。”英籍厂长用了一句英国式的幽默,然后就准备按原计划喷吹。
“如果你真要坚持的话,那么,我也要坚持一下,”中国工程师说,“我要坚持的是,这炉钢不应列入供货计划。”
英籍厂长显然还没有领会中国工程师的严肃态度,他拿起笔来,在炉前记录上写道:“徐教授认为这炉温度不够。”然后笑着将笔递给中国工程师,“请你签个字吧。如果温度不够,责任当然在我。但我相信,这炉钢没问题。”
中国工程师毫不犹豫地接过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徐匡迪。”
结果,果然有接近200吨钢水冻在包中,造成了一次较大的事故。从此以后,每次出钢时,徐匡迪的炼钢镜都会被用来看一看温度如何。由于这副炼钢镜是徐匡迪从国内带去的,所以又被称为“中国眼镜”。
徐匡迪是一位优秀的工程技术专家,他是我国特殊钢生产和电冶金、喷射冶金领域的专家,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2003年5月当选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他还是英国皇家土木工程师协会荣誉会员和英国皇家工程院荣誉院士。但我认识徐匡迪的时候,他已从科研一线走到党政领导岗位上。在上海市,他先后担任高教局局长、计委主任、副市长、市长等职,是我国第一位院士市长。作为科学家,他是一流的,作为政府领导,他也政绩突出,广受拥戴。
在他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我每次到上海,他都会抽出时间款待我这个军方人士。我很早就知道他外语很好,外交能力很强。有一次,我陪同他会见外国代表团,他直接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宾交谈,对于一位不是从外交领域成长起来的领导人而言,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后来,徐匡迪调到北京,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我们的接触更多了。徐匡迪是中德对话论坛的中方主席。这个论坛是根据中德两国领导人的共识而成立的,轮流在两国举行。其中,2006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会议,2007年7月在柏林举行的第三次会议,我都受到邀请,并且积极与会。对于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工作,徐匡迪也非常支持。有时候,我们的外宾请他接见,他在很忙的情况下也总会抽出时间。2007年4月23日,我们邀请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访华,徐匡迪在上午开会,下午出差的间隙,还抽出中午时间与赫尔佐克共进午餐,令我很感动。
在北京,我们的住处相距不远,甚至徐匡迪还曾经和夫人遛着弯儿就到了我们家。这时候,我也会和夫人沏上清茶,请他们在院内小坐,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聊个痛快。有时候,他还会随手捎来一些可口的上海小吃,增添茶兴。
2005年4月,《徐匡迪文选(钢铁冶金卷)》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很快得到了签名本。对于钢铁冶金知识,我几无所知,但书前一篇《我的学术生涯》生动而翔实地记述了徐匡迪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的治学、科研历程,我非常喜欢。本文一开始讲到的故事,就载于《我的学术生涯》。另外,在这篇学术自述中,徐匡迪还以题外话的方式,讲述了他的名字的来历——
匡扶正义、迪吉平安(2)
1937年日军侵占淞沪后,徐匡迪的父母随着难民潮向我国西南撤离,当时徐匡迪的母亲正身怀六甲。当年12月11日,在浙赣交界处一座古庙里,徐匡迪早早地来到了人世。在没有医生和助产士,甚至农村的接生婆都找不到的情况下,父亲在母亲的指挥下为徐匡迪接了生。为使徐匡迪铭记国仇家恨,遂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