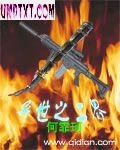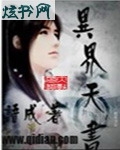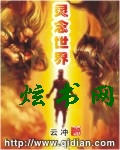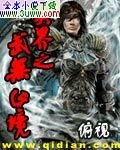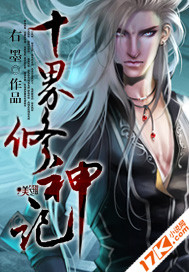后美国世界-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它对其他国家漠不关心,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奉行*裸的现实政治主张,而是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依据的不是抽象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是按照一种作为指导哲学的实用主义思想行事的。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明(3)
西方商人经常抱怨说,中国同行似乎不太尊重规则、法律和契约,他们的伦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事而异的;如果中国商人或官员认为法律是“一头笨驴”(借用一位英国人的说法),他们就会对其置之不理、予以变通或者干脆要求你另起炉灶。可以说,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中,对某种抽象观念敬若神明是不可思议的。对他们来说,社会关系和信任远比书面载明的义务重要。微软公司曾经长期无法促使中国政府贯彻它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直到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系,并明确表示愿意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提供帮助时才达到目的。一旦微软公司让中国政府确信其动机是好的,那些法律就开始得到贯彻执行了。很少有中国人真正内化了这样的观念:抽象的规则、法律和契约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重要,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和法律发展道路之曲折和复杂,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文化传统也影响着中国人对待谈判的态度。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指出:“中国人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气功’观念基础上的。‘气’是‘风水’的构成要素,也是人体内的基本成分,通过针灸或中药进行调理。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广意义上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它把世界的结构视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力,这些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不是通过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发挥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也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韦勒说道。这种思想有时过了头,甚至显得有点愚蠢。然而,当你与中国人谈论他们的思维方式时很快就会发现,像“气”这样的概念居于他们思想意识的核心地位,就像道德“造物主”和自由意志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位置一样。众所周知,外交政策受许许多多普世性力量的驱动,但基本的世界观无疑决定着人们认知、行为和反应的方式,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但是,文化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中国的过去及其内在独特性都是由它的现代史塑造的,即西方的冲击、共产主义对传统的塑造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仰危机,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其近年来使传统与现代性相调和的努力。当你与中国经济学家们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并不主张以儒家学说推动经济增长或遏制通货膨胀。中国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非常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西方式的。当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为所动,这一事实更多地体现了民族主义而非文化的影响。(请问:美国什么时候在外国的压力下改变过经济政策?)在许多领域里,中国人都实行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分析家也以“基督教儒家弟子”自居,意思是说他们并非福音主义的皈依者,而是具有西方思想观念的中国人,致力于使中国的政策体现更广大的目标和价值观。中国与其他所有非西方国家一样,为了在21世纪兴旺发达起来,将会酿造它自己的“文化鸡尾酒”,其中既有东方成分,又有西方风味。
崛起势不可当(1)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文化的独特性,而是其影响力的普遍性。中国自认为是一个致力于和平崛起的国家,它的行为也充分体现了谦卑精神和不干涉原则,并希望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然而,历史上许多崛起的国家也都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到头来仍然以颠覆既有国际体系而告终。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当一个国家的权力增长的时候,势必按捺不住加强对环境控制的诱惑。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它一定会加强自己对政治、经济和领土的控制,从而按照自身的特定利益改变国际体系。这里最关键的论点是:历史上的大国都认为自己有着最良好的意图,但无一例外都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不断扩展的利益。而中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二号强国,自然也会把自己的利益大大地向外扩张。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意图无关紧要。在杂乱无章的国际政治世界上,意图与结果没有直接的联系。(1914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打一场世界大战。)这样的世界就像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所有的公司都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提高价格,但却造成了与意图相反的体系性结果—价格下跌。同样,国际政治也是一个没有单一最高权威的体系,国家的意图并非总能准确地预知它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正因如此,才有了罗马人的至理名言:“欲求和平,必先备战。”
中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崛起,将取决于中国的行为和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造成的一系列效应。鉴于中国的现有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不能指望神不知鬼不觉地跻身于世界舞台上。例如,中国到处寻求能源和原材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正在快速增长中,消费的能源和各种商品自然会大量增加,因而需要找到稳定而可靠的供应来源。其他国家都在购买石油,中国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问题在于中国的规模。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在如此庞大的规模基础上进行的,这会使它不可避免地改变博弈的性质。
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相比吴建民等老一代外交官,新一代外交官都对中国的新权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令一些中国观察家担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势必会渗入中国人的头脑里。2005年,李光耀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经含蓄地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他担心的不是中国的现有领导层,甚至也不是下一代领导人,而是下一代的下一代,因为他们将出生于稳定、繁荣和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年代。“必须让中国的青年人明白,他们需要让世界确信:中国的崛起不会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李光耀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说道。他指出,自*以来,促使中国领导人保持谦卑的,是关于毛泽东所犯错误的痛苦记忆。李光耀接着说:“年青一代生活在和平与增长时期,对于中国不堪回首的过去没有切身的感受,因此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因为自命不凡和意识形态狂热酿成的错误是至关重要的。”
截至目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以商务活动为中心,尽管如此,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中国正致力于同非洲国家加强经济联系。非洲大陆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而这正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对于建立新型的贸易关系,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都持欢迎态度—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之间没有纠缠不清的殖民历史和交恶经历—双方之间商务活动因而蒸蒸日上。中非贸易额年均增长50%左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则增长更快。近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创历史最高纪录,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非洲国家都把这一成就归功于它们同中国建立的新型关系。而且中国也费尽心机,多方向非洲国家展示善意。200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主持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全部参加,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由总统或总理亲自与会。这是有史以来在非洲以外召开的最大规模的非洲峰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承诺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在两年内使对非援助规模增加一倍;在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一个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以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取消非洲国家欠中国的多数债务;进一步向非洲国家开放市场;在今后3年内为非洲培训万名各类人才;并在非洲大陆新建医院和学校。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崛起势不可当(2)
中国在亚洲的表现则更加老练,更好地发挥了外交手段和软实力的作用,这里也是中国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最为关注的地区。过去20年来,中国娴熟的外交在亚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悄然发生了一场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与许多东亚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但到2007年夏季,中国已经开始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当被问及希望哪个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受访者选择的是中国而非美国,尽管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就连在澳大利亚,分别支持中国和美国的人也大体持平。
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亚洲地区扮演的建设性角色越发清晰。从那以后,中国在亚洲的外交活动更加老练,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方式更加耐心和低调,收到的效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目前,中国外交强调要有长远的眼光,要从战略高度进行决策,而不能采取一种说教式的态度。中国采取了一种更加和善的外交路线,动辄慷慨地提供一揽子援助(往往超过美国的援助水平),还迅速地与东盟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长期以来,中国不愿参加多边主义安排,近年来却尽可能地参加这类活动,甚至还参与创立了一个亚洲自己的多边安排—东亚峰会。东亚峰会具有明确的区域性组织的性质。目前,东南亚国家也对中国持欢迎态度。明显亲美的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阿罗约就公开表示:“我们很高兴把中国当做自己的老大哥。”
中国与所有邻国政府的关系都反映了这一变化。例如,越南人对中国没有任何特别的好感。但正如一位越南官员对我说的:“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客观存在,也是我们的最大出口国。”这一状况意味着:越南政府和人民必须务实地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我参观过的所有越南书店,都在突出位置陈列着中国领导人的文选,包括*、*和*。
在2007年到越南之前,我先去了日本参观访问。当时正值中国总理*对日本进行2007年的国事访问,期间我耳闻目睹他表现出了同样的克制。*对中日紧张关系的许多方面都做了淡化处理,而是突出强调两国关系中的积极方面—方兴未艾的经济联系。
从战略层面看,由于中国执行一种“和平崛起”的政策,中国若一如既往地对东京拒不妥协将有害无益。那样做只能使中国拥有一个敌对的邻国,而这个邻国又有着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队,它的经济规模仍然相当于中国的3倍。更明智的做法应当是:与日本开展经济联系和更多的合作,同时更多地打入日本市场,获得更多的日本投资和技术,从而逐步赢得压倒日本的优势。在中国台湾问题上,近年来,中国认识到时间在自己一方,因而采取了一种更加明智、更加温和的路线。为此,中国内地采取了几个非常聪明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削减向岛内独立意识最强地区的农产品征收的关税,从而增强了台湾对大陆的依赖。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其基本战略目标就是在有关台湾的任何冲突中迅速取胜。换言之,经济增长和全球化使中国北京步入了一体化的轨道,但同时也赋予它进行军事和政治对抗的实力。
龙和鹰:对抗,竞争还是合作?(1)
与中美关系相比,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都相形见绌。或者换句话说,只要不引起美国的介入,中国面临的任何潜在问题都将无关紧要。如果美国不介入,一场关于台湾问题的战争也可能是激烈的,但只有在演化成中美直接对抗的情况下,这种战争才会具有影响深远的全球性后果。反过来,来自中国的挑战对于美国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当世界上的头号强国面临崛起国的挑战时,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常紧张的。虽然任何一方都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中美两国都对这一前景忧心忡忡,并且都在为可能出现的麻烦制定预案。30年来,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为了争取与美国合作。中国这样做有着多种实用主义的原因。首先是反对前苏联的战略,其次是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愿望,然后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最后是为了办好北京奥运会。然而,中国年青一代的精英们越来越认为,从多个方面看,他们的国家需要自我定位为华盛顿的竞争者。而在华盛顿,也向来有一部分人把中国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和理想的下一个全面威胁。当然,他们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战争或冲突迫在眉睫,只不过是指出两国关系有陷入紧张状态的可能性罢了。中国和美国对此如何应对,将决定它们未来的关系和世界的和平。
目前看来,全球一体化的力量取得了胜利,无论对北京还是华盛顿来说都是如此。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需要向美国的市场销售货物,美国则需要中国出资购买其国债—这正是核时代相互确保摧毁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的翻版。此外,中美两国的核武器还发挥着威慑作用,这也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力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这一事实推动美国和中国形成了一种联盟关系,这种关系从纯粹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表现了相当的合作姿态。就对于处理美中关系的立场而言,小布什可能是最具意识形态敌意的总统,如小布什总统在他的整个任期内,不遗余力地赞美*,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利用美国的实力实现他的目标。但尽管如此,他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一再与中国政府站在一起,警告中国台湾不要企图走上分裂的道路,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总统就中国台湾问题发表的最强硬的言论。虽然小布什总统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