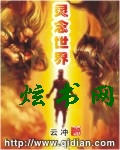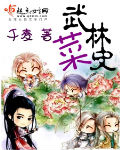世界电影史-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随后,有人以为这部影片的整个剧情可以用心理分析来解释。例如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插曲:主人公想要拥抱他所渴望的女人,结果却被两根系着南瓜的长绳和两个修道士及一架堆满烂驴肉的大钢琴所阻挠,未能达到他的**。按照这些注释家的解释,这些比喻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即“恋爱”(由主人公的冲动来表示)和**(由南瓜来表示)受到宗教的偏见(由修道士来表示)和资产阶级的教育(由大钢琴来表示)的束缚(由长绳索表示)”。
其实布努艾尔和达利写这个剧本时,他们故意追求一些令人惊奇的怪诞的道具,并没有想使这些道具具有什么象征的意义。这种对惊人的、激烈的、使人难以忍受的效果的追求,和爱森斯坦的“杂耍镜头”的原始观念很相近似。因此,这两种手法,虽然出于不同的先锋派别,但在理论方面却有共同的来源。
《一条安达鲁狗》虽并不含有什么暗示的意义,但却经常地应用超现实主义的、甚或古典的比喻法。例如被一片浮云分成两半的月亮,用来比喻被割破的眼睛,由此引出那个眼睛被剃刀一下子划开的有名画面。
影片《幕间节目》最突出的是轻松愉快的即兴式的描写,作者对死亡的蔑视是通过滑稽的葬礼和追逐场面来表达的。但成为超现实主义者的达达主义者却不是这样,他们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即:自杀是不是一条出路?他们对这问题如此急于求得解答,以至有一个达达主义者竟吞服了安眠药。在《幕间节目》中,皮卡比亚开玩笑似的向布尔林瞄准的假卡宾枪,到了《一条安达鲁狗》中就变成了演员皮埃尔·巴契夫手中用来残酷地打死自己的魔术手枪。前一影片是一出轻松愉快的滑稽剧,很象学生的起哄;而后一影片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发疯似的绝望,一种无政府主义的骚乱,它同时向列宁和**喇嘛求救,对金钱与劳动、宗教与理智、西方世界与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诅咒。
所有这种超现实主义的“世纪病”,在《一条安达鲁狗》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成了盲目反抗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写照。这种无力的愤怒呼声所表现的真实情感,使这部影片具有一种人间悲剧的气氛。
以上这些特点在《诗人之血》一片里是找不到的。在这部影片中,让·谷克多在造型方面虽受到某些超现实主义的电影或诗的影响,但人们却不能把它称之为超现实主义的影片,因为作者只是利用了技巧的多样化来表现他所惯用的主题。作者对那些穿短披肩的小学生的热爱,对天使或青年英雄的崇拜,对特技摄影以及技巧效果(包括焰火)的极度偏好,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这部矫揉做作、炫耀技巧的影片的特征。女性在这部影片里也占有相当地位,但它所特别刻画的乃是一个戴夹鼻眼镜、心理变态的老女教师。让·谷克多的手法给人的印象乃是一个对自己、对社会都感到满意的玩弄艺术的人的那种虚饰做作。这部影片是由诺阿叶子爵在摄制曼·雷伊的《赌城的秘密》一片以后出资摄制的,在此片以后,他还资助布努艾尔摄制了《黄金时代》一片。
《黄金时代》这部新片进一步加强了《一条安达鲁狗》中对先锋派初期那种无故炫耀技术的作法。影片在格调平凡而近乎庸俗的画面中间,协调地穿插了一些从新闻片和从一部描写蝎子生活的纪录片中剪下来的片断。这种“客观的”展览就象大百货公司的商品陈列,超现实主义者把这些平庸的形象剪接在一起,用来表现他们所谓的“优美的骸体”的奇特蒙太奇。
影片《一条安达鲁狗》,使人感到好象走进一个竞技场,到处都是马、枪、剑、喊叫声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道具。但到《黄金时代》一片摄成时,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家安德烈·布列顿却声言今后应该用精神分析来解释劳特雷阿蒙的那句名言。照他的解释,手术台象征着床,缝纫机象征着女人,而雨伞则象征着男人……
布努艾尔和达利所写的《黄金时代》的剧本,是试图用弗洛伊德、劳特雷阿蒙、萨特和卡尔·马克思这些人的学说来说明世界。导演甚至想借用《**宣言》中的一句话“利己主义计较的冰水”来作为他这部作品的名称。但加斯东·莫笃所饰的影片主人公,却和马尔多罗尔或芳托马斯同一类型。他用鞭打一个瞎子来表示反对慈善,伪装为社会服务来攻击社会,而且沉溺于肉欲的、兽性的和近乎神秘的爱情而不能自拔。
愤怒和泛**主义在这部影片里表现得非常突出,它并且有意识地应用暗示的手法。例如那些幼稚得象中学生的戏谑而不象心理分析的性的象征;或那种所谓“革命”的比喻,表现一个高贵的社交场所,忽然冲进一辆垃圾车,车上坐着几个喝得满面通红的抬土工人。《黄金时代》虽因内容极度混乱而令人看了感到不快,但它却标志着一种思想觉悟的开始。布努艾尔一直要到他抛弃掉了形式主义的技巧和超现实主义的比喻以后,方才在他那部具有社会意义的纪录片《无粮的土地》里为无政府主义的反抗与绝望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出路。
这部由爱利·洛泰尔和皮埃尔·于尼克协助拍成的影片,描写西班牙一个最穷困的名叫犹尔德的地方。它在动物片和旅游片那样客观的形式下隐藏着作者对社会严厉的控诉。在今天看来,《无粮的土地》正说明并预示了西班牙的内战。那次内战期间,长枪党人①枪杀了布努艾尔的友人——胡安·维森斯和迦尔西雅·洛尔加,而萨尔瓦多·达利则在纽约替佛朗哥的大使画像。①1933年10月佛朗哥组织的法西斯政党。——译者。
这种演进和分化,乃是所有先锋派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在电影界,使先锋派转向纪录电影的这股潮流,并不是在《无粮的土地》出现时才开始的。早在产生先锋派的时候,纪录主义的潮流就已经和德国的抽象派,“纯粹电影”或法国的超现实主义一起涌现出来了。
这个趋势不久就代替了其他各种趋势。抽象电影当时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它把彩色的几何图形和古典音乐结合在一起。华尔特·罗特曼的门徒奥斯卡·费辛格在德国把《第七、第八练习曲》、《绿色乐章》和杜卡斯的《魔术师的徒弟》、勃拉姆斯的《第五号舞曲》拍成影片以后,又在美国应用上一方法,杰出地摄制了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和葛许温的《蓝色狂想曲》。费辛格这种独创性的尝试,以后被沃尔特·迪斯尼在他的《幻想曲》第一集(即巴赫的《赋格曲》和《托卡泰曲》)中,加以抄袭和庸俗化。这种影片样式当时却颇有发展的希望。
与此相反,达达主义的电影或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则以《黄金时代》这部影片而告结束。今天只有美国某些落后于时代的人们,才会对这种电影感到新奇。先锋派运动到达好莱坞很晚,它是随法国人罗伯特·弗劳莱试拍的卡里加里式的作品(即《好莱坞号外》、《零度的爱情》)而传入好莱坞的。抽象电影曾因摄影师拉尔夫·斯坦纳和玛丽·爱伦·布特、刘易斯·约可布、约瑟夫·希林格等人试拍的作品而在纽约流行过一时。玛耶·德连晚近摄制的影片,也就是旧日超现实主义陈腐的遗迹。汉斯·里希特在曼·雷伊、杜向、卡尔德、麦克斯·爱恩斯特、费尔南·莱谢尔共同合作下摄制的《钱能买到的梦》,也颇有价值,但这部彩色片实际上也仅限于采用一些二十年前甚至更早以前用过的主题或造型的题材。它在1945年只是综合了过去的一些经验,而不是复活一种已经消失的影片样式。
阿尔倍托·卡瓦尔康蒂摄制的《只有几小时》一片,可被认为是先锋派中纪录主义潮流的首次表现。这部影片用一个相当灵活的情节来显示一个大都市从早到晚的情况。卡瓦尔康蒂摄制的另一部根据一个民间歌谣改编的影片《小莉丽》,则已预示了他第一部大型片《在码头上》中的那种“平民主义”,后一影片乃是一部继承德吕克的《狂热》和让·爱浦斯坦的《忠诚的心》的传统的作品。卡瓦尔康蒂在开始时与其说是一个纯先锋派的人物,倒不如说他更接近于让·雷诺阿,后者当时在电影中致力于表现一些适合于他的妻子、即女演员凯塞琳·海斯林(曾主演雷诺阿第一部长片《水上姑娘》)的演技的传奇、幻想和怪诞的故事。
根据左拉的原作摄制的《娜娜》,是雷诺阿在德国制片厂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导演的一部长片。但是这部有他一部分投资的作品在上映收入上并不成功,因此,他以后不得不改而摄制一些商业性的影片(如《穷乡僻壤》和《古城比武记》等)。这种情况正和他的朋友卡瓦尔康蒂摄制《弗拉卡斯上尉》一样。但雷诺阿曾替“老鸽笼”摄影场摄制了一部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卖火柴的小姑娘》,在这部影片中,他企图用摄影场的布景、模型和巧妙的摄影手法,来创造一个梦幻的世界。可是雷诺阿在模仿梅里爱和表现主义者的技巧上却赶不上他模仿左拉或斯特劳亨的技巧那样成功。
让·格莱米永在无声电影末期导演了两部长故事片。他的《灯塔看守人》一片并不是一出闹剧,而是一部得益于苏联和德国的纪录片经验的作品,片中两个人物几乎只在灯塔和它的楼梯的布景中活动。但此片同《马尔东纳》一样,没有获得广大的观众。
苏联电影的兴起,加速了先锋派趋向于纪录电影一途。它给予先锋派的电影以人物和物体应同样重要的观念。代表先锋派末期的两部影片,就是以具有社会性的人作为主题的:拉贡布(曾任雷内·克莱尔的副导演)摄制的《郊区》,几乎完全以纪录片形式来描写巴黎的贫民生活;让·维果摄制的《尼斯的景象》,则是一部激烈抨击社会的作品。
在德国,先锋派电影受维尔托夫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汉斯·里希特又把影片《幕间节目》中的一些手法,应用到他的一部以兴德密斯①的音乐为基础、具有讽刺性幻想的杰出影片《帽子的游戏》(德文原名《午前的幽灵》)中。但他在影片《赛跑交响乐》中,却采取了“电影眼睛派”的手法,用动作的类比把一些从群众中拍摄下来的镜头讽刺地联结在一起。他从1926年宣布“我们要有政治性的影片”以后,就开始在先锋派电影中采取一些社会性的题材(例如影片《通货膨胀》)。以后,他还在苏联拍了一部反纳粹的半纪录式的影片《金属》。但人们如果因此认为唯美主义的先锋派电影必然会走向政治性的先锋派电影,那就错了。因为华尔特·罗特曼受苏联电影的影响比里希特更深,可是他在放弃摄制《作品》这类抽象化的影片以后,却按照“电影眼睛派”的原理,用所谓“客观的现实”的片断,制成了《柏林——一个大都会的交响乐》和《世界的旋律》这两部影片。①德国现代作曲家。——译者。
对“室内剧”和摄影场技巧感到厌倦的卡尔·梅育曾计划摄制一部既没有演员也没有故事情节的影片《柏林》,想用一些户外拍来的镜头剪辑起来,表现德国首都的一天的生活。罗特曼在摄影师卡尔·弗洛恩德的协助之下,实现了这个计划。他在《柏林——一个大都会的交响乐》中,特别致力于创造一种运动对位法,并且把视觉上的各种主题象管弦乐似的结合在一起。
这位擅长表现抽象概念的导演,在他只表现一些物象或者把高架电车的运动按照对角线和平行线的形式结合起来时,常能得到很优美的效果。可是他把工人进入工厂的镜头和一群羔羊驯顺地被牵进屠宰场的镜头剪辑在一起时,这种比喻就带有一种侮辱工人的意味,而使动作的类比作用反不甚显著。罗特曼并没有想到把工人比成羊群,这和他使豪华的酒馆和饥饿的孩子们的镜头交错出现而并无攻击社会的意义,正属相同。他不过是依照一种机械的结合,把这些东西联结在一起,就象他把交响乐队、游艺场的音乐、舞女的大腿、卓别林的脚和飞驰的自行车竞赛者等镜头结合在一起,也是出于这种机械的结合一样。
这种致力于细致描写主题的作法,和德国大学教授喜欢作详细分类的癖好,实属同出一辙。在《世界的旋律》一片中,这种作法表现得几乎使人不能忍受,影片被分为各种章节,从睡醒、起床、洗澡、梳洗打扮一直到吃早饭、做深呼吸运动等,都一一详细地加以描写。有些镜头是在世界各地摄制的纪录影片中挑选出来,然后再按照构图的类似、主题和动作的类似而剪辑起来的,可是人们却很难从这种剪辑技术中发现有什么艺术气味,因为这种技术上的巧妙不能掩盖影片主导思想的幼稚和贫乏。他把整个人类处理得和动物一样,在一定的时间里做着吃食、游泳、行走、爱抚和哺乳等等相同的动作。罗特曼如果不把人类主要的活动处理得象军队生活那样刻板的话,则这部影片也许能成为一部带有一些人情味的作品。
罗特曼虽然采取了“电影眼睛派”的客观性,但他却以动物性的人来代替社会性的人,并以此作为客观性的内容。另一方面,在《世界的旋律》一片的伴奏中,他对于语言和杂音、呼喊和音乐、人和机器,一概都赋予一种相同的情绪作用,就象他在那部称为“没有形象”的影片《周末》里把各种声带结合在一起一样。后一部影片可以说是无线电广播剧的前驱。
罗特曼在暂时回到音乐抽象化的老路和他导演的《钢铁》一片遭到失败以后,给戈培尔拍摄了各种纪录片,并协助莱尼·里芬斯塔尔摄制了《民族的节日》。他在拍了一部歌颂希特勒的坦克部队进攻法国的影片《德意志机械化部队》以后,就死在俄国战线上。
《柏林——一个大都会的交响乐》是一部最值得注意的作品,它和维尔弗利德·巴斯的《柏林的市场》,尤其是和描写小职员休假生活、稍带辛酸味的杰出半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