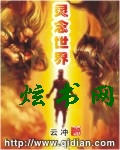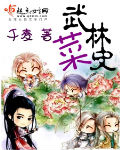世界电影史-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说关于一个导演的作品专述早在1920年就有一些先驱者从事此项工作——在法国最突出的是路易·德吕克——可是这些出版物却给电影创作者的影片目录规定了形式。以前,一个影迷,甚至一个电影史家要知道那些重要的日期真是困难重重。《画面与音响》出版的第一期影片目录是专记述查尔斯·卓别林的作品,标明他第一部影片的制作日期为1914年1月。而外国研究“夏尔洛”的专家,如法国的皮埃尔·勒普洛翁等人前此曾把卓别林开始拍片的日期定为1912年,这是因为他们未能研究美国的同业杂志所致。
(6)1945年以来:这时关于电影创作者的影片目录大大增加,它们是由各种杂志或出版商刊印的。
五花八门的影片说明书(它们的不同样式直到战后才统一起来)也大大增多,尤其在近十年更是如此,电影学会、电影俱乐部以至各种文化组织都发行这种说明书。它们不是用来记述影片创作者,而是记述影片而印行的。仅以用法语印行的来说,这类说明书在1946年至1962年间就出了1500种(根据让·朗博特收集的资料),有的说明书只是打印的一页纸,但很多说明书却是铅印的,长达十页或更多。
我们可以把意大利人首先印行的出版物(《多角丛书》)称之为“影片分析”,这些小册子按镜头号码次序分析影片的蒙太奇,它们刊登一些从影片的拷贝翻印出来的照片,描述每一个镜头长多少米,合多少秒,等等……
这类出版物由于公众的冷淡不能继续出版。然而,自1955年以来,电影爱好者的增多又促进了影片分析的出版(法国在这方面尤为人注目的是《前台》杂志社发行的这类出版物),它依据正片拷贝在放大机下进行分镜头的研究。这类出版物的科学价值也许不如1946—1947年间意大利的出版物,但仍不失为一种参考材料,而且比起1920年以来专为“影迷”刊行的《影片故事》那种编辑极其草率的商业性出版物来,要严肃得多。
在许多国家,电影研究者、史学家、影评家、电影爱好者以及电影俱乐部的领导人等都出版了影片目录、影片说明以及影片分析,相形之下本国影片的目录却为数不多,这类目录主要是靠电影公司来出版的。
手稿资料
要深入研究一部影片,一个重要资料是它的原始电影剧本。一部长片的电影剧本可以采取“技术性分镜头剧本”的形式,付印几十份,分发给技术人员和演员,1920年以来——那时这种剧本显然还未十分流行——有些电影剧本以原稿或文学剧本的形式由作者交给书店出版。
不论手稿是打印还是付印成书,这些电影剧本都是拍摄前的工作计划,在拍摄或剪辑过程中都会作出重大的修改。举早期这类出版物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流浪女》的剧本是路易·德吕克于1923年付梓的,里面就没有影片本身含有的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一个孩子玩的气球,向着观众迎面飞来,愈来愈大,最后变成大特写。这个画面是在拍摄时临时加进去的。
因此,我们不能把一个电影剧本或一个分镜头剧本看作是“一部纸上的影片”,而只能把它看作一部影片的拍摄计划,最初草图或草稿,影片本身才是主要的文献,它使人们能够按镜头、按场景一米一米地进行分析。不过这种分析也要格外小心,要有若干保留,其道理将在下文说明。
至于其他手稿,诸如导演、演员、制片人、技师等留下的档案材料对史学家来说,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这类材料常常在电影创作者还活着时就遭到毁坏,更多的散失于他们死后。例如,路易·卢米埃尔的档案材料除了那份1895—1896年间的信件抄件之外,似乎早在他初期拍摄影片时就丢失了。百代公司有关1910后十年间电影生产的档案材料在这次大战结束时还存在,可是不久就散失和毁坏掉了。
最后,还要谈一下图片资料:如广告、剧照、节目单等等,这些资料即使刊行的数量很大,也仍然很快地被散失掉,而且在各国的档案里也很少将它们当作保存的对象。然而我们要特别指出:1904年后,美国为了实行版权法,许多印在纸带上的影片一直到1910年还保留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里,梅里爱、鲍特等人的许多早期影片也就因此而被保存下来。
二、口述的原始资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闻记者收集与刊登在报上的访问记可以看作是口述的原始资料,虽然它们多少都经过它们作者的转述。
在这类新闻资料之外,近年来还出版了许多电影创作者的访问谈话,谈论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长期中完成的工作。这些访问谈话因此成为真正历史性的调查材料。
1950年以来,这种访问谈话在抄录成文之前常通过录音机录制下来,这大大增加了材料的可靠性。从前,史学家们和电影界人士只可通过速记或按音记录的材料来调查电影先驱者的情况,现在则最经常地采用录音机,这样,在书面资料之外又增加了磁带录音这样的声音资料,它的好处是把那些电影大师们的声音保存下来。
关于这些口述的证明,要注意到它们大多是即兴谈话,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尤其是谈到久远以前的事情更是如此。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至四十年过去之后,一个电影创作者的记忆与想象会互相混同,把一些传闻或一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当作真有其事。例如,乔治·梅里爱就多次声称,甚至还这样写过,说他导演了4000部影片,这个数字比实际情况,也就是比他的目录上记录的影片数夸大了五倍到十倍。
对于任何一份口述的证明材料,不论它是调查的记录,还是速记材料或是录音带上的资料,都应把它和同时代的书写资料与印行材料相比较,仔细鉴别。
这不是说那些文字材料都应永远看作是“货真价实”,毫无差错。在雷内·克莱尔于美国拍摄的那部影片《明天发生的事情》中,主人公每天晚上都收到一份次日早上出版的报纸,他获悉自己在数小时内即将毙命,然而他却幸存下来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伪造的消息。电影界伪造的消息为数很多,绝不比普通的新闻报道要少,所以我们要备加小心。
对书写材料、印刷品、手稿以及口述资料的评论,判断它们的作证价值,长期以来已成为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因此对这种评论在这里无须再作深入研究,在这方面,无论是电影史或是一般历史,都运用同样的方法。
但我们对胶片上原始资料,对影片的画面与音响,却需要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分析。
三、胶片上的原始资料
对于电影史家来说,影片是一个基本的要素,其重要犹如绘画对于美术史家一样。任何一个美术专家都深知,博物馆储存的一幅作品同它刚从画家工作室送出来时是不一样的。它会老化、会退色、会破损(象伦勃朗的那幅《夜之圆舞曲》那样),也会受到修补以至复制①。
①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的画家和雕刻家。——译者。
一个电影史家更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影片在它们上映期间会遭到删剪和改动,这种删剪与改动常常比文学作品在手稿或付印时的删改更大,有时几乎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因此人们要问:胶片上的原始资料是否真正保存下来呢?
影片的寿命是否比纸张、羊皮纸或画布更短,尚未得到证明,但影片的保存确是更为困难。倘若条件不好(温度、湿度等方面),胶片就会产生化学变化而致完全毁坏。更多的情况是胶片毁于疏忽、事故或因贪利放映太多。
图书与期刊,至少从一百五十年以来在所有的大国由于法定存档的结果,一直被保存下来,可是直到1964年,系统地保存长片与短片的国家却非常之少。当然,制片商常将他们的影片底片库存若干时期,但是一旦当这些影片被认为失去其商业或放映价值时,它们也会遭到销毁的下场,以便“腾出地盘”和回收生产胶片的原料(赛璐珞和银)。
企业的倒闭在这方面也起到作用。大家都知道,1920年左右,乔治·梅里爱面临破产,只好将他全部底片论重量拍卖出去。安全法规有时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从1950年起就规定,必须完全使用不燃性的胶片拍片,结果导致了大批数量可观的赛璐珞正片与底片完全被销毁。
1945年后电视业的发展表明,一些被人们认为永远“失去放映价值”的老影片居然在荧光屏上重新得到它们在大银幕上失去的地位。这种情况促使人们对老影片更为重视。但是,在这些影片底片被卖给电视业的专门部门之后也会引起对影片的删剪。例如,为了重新剪辑,以便放映时间由100分钟减到45分钟,必然要毁损原来的影片。在上述因素之外,再加上事故和战争,影片的毁坏在有些国家在某些时期中可能达到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以至百分之九十九。
这些损失是无可弥补的。如果人们知道1895年至1900年间摄制的卢米埃尔的影片是代表一个宝藏的话,那么不妨设想一部在凯撒、孔夫子、亨利八世、梅迪西斯、德川家族、路易十四或加里波弟时代演出的影片即便是低级商业性的作品,它100米的价值该有多大!毫无疑问它会推翻我们对过去几个世纪的社会风俗、人的姿态、服饰、语言和表达方式的概念。
我们能否确信我们在艺术问题上对于当代的或比较久远的影片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呢?我们能否把握自己不象17—18世纪的教会机构或行政机构那样行事呢?这些机构把罗马式或哥特式的壁画、建筑与雕塑视为野蛮的东西,下令加以摧毁。1921年倘若有一批第七艺术的卫道士们受命筹办一个电影博物馆的话,他们就一定会把路易·费雅德的影片一笔勾销,因为他们把这位当时曾是电影艺术主要大师之一的人物看成是一个“杂货商”。
各种各样的电影资料馆尽管资金短缺,为了尽快装饰门面,只注意收集一些有名的杰作,但是正如亨利·朗格卢瓦经常一再说过的那样,它们在原则上应该保存所有的影片,不仅要着眼于它们的文献价值,也要考虑它们的艺术价值,因为这些影片的同时代人并不总是判断得那样公允的,这就需要未来的史学家与评论家在21世纪来发掘第七艺术中的格列柯、保罗·乌切洛、凡·高和杜阿尼埃·卢梭①。
①格列柯(1540—1614):生于希腊,先到意大利、后定居西班牙的画家;保罗·乌切洛(1397—1475):佛罗伦萨的雕刻家、画家;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杜阿尼埃·卢梭(1844—1910):法国画家。——译者。
那些幸免于当时破坏的影片也会受到重大的改变。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回想一下,一部电影作品要经历多少个连续的阶段。首先它是拍成片段的底片,然后集中起来进行画面与音响的剪辑,形成影片的最后底片,最后按照不同国家印出几十部或几千部的正片拷贝。如果这些拷贝大多散失的话,甚至连原始底片也丢失的话,还可以通过翻印的办法从一部正片拷贝中翻印出“复底片”,由此再洗印出别的正片拷贝。
关于影片的声音部分,可以分为所谓的国际声带与对话声带两部分,前者专录一般声音与音乐,后者在配音译制中代之以另一条声带,由另外的演员配上与原版片不同的语言。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默片时代的各种不同情况,看看各影片资料馆保存这类影片的情况如何,史学家们是怎样观看这类影片的?
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谈:(一)无声片时期的拷贝;(二)根据这些原来的拷贝翻印出来的影片;(三)根据原来底片重印的拷贝。
(一)无声时期的拷贝
这类拷贝常常是无价之宝,堪称为电影方面的古籍,但如果放映次数太多,就会使它们迅速毁损。所以需要翻印之后方可在电影博物馆里向观众放映。
但是,这些原来的无声片拷贝最好能供研究人员与史学家们观看和研究,当然要有极其严格的条件,就象图书馆里借阅手稿那样严加控制。依我们之见,观看这种影片应该不用放映机,而用看片机(人工的要比电动的好)。
为研究人员准备的这种设备可使他们象读一本书那样来考察一部原来的拷贝,而不再需要在黑暗的放映厅里观看。这种看片机能够在一个画面上停下,可以倒退重看,也可以多次从头开始来看一场戏或一个镜头,而不受每秒钟16格那种机械节奏的限制。在这种看片机上还可以附加一个计米器,这样就能够精确地对影片的剪辑作出分析。
凡是专门研究原来拷贝的人绝不要忘记,这种拷贝由于事故,或者出于故意,内容可能有改动。
(1)事故造成的改动
一部影片在放映期间会断裂或者变质,这样就要剪去一米或数米。这些删剪在原来的拷贝上可以从粘接线上看出,除非象常见的情况那样,损坏的部分是在一本影片的末尾。
这些删剪常常造成场景的前后倒置。有个巡回放映商放映百代公司的《基督受难》一片达二十多年之久,他跟我讲起这样一件事:他这部影片的拷贝损坏太多,常常断片,粘接的工作是由他的孩子们去做的。因此,有一天放映时,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场面竟出现在他受审于罗马总督庞斯·比拉特和登上喀尔维山①之前。
①喀尔维山:传说为基督受难之地。——译者。
如果影片所表现的是一个象上面那样众所周知的“剧情”的话,恢复原来蒙太奇是容易做到的,但在旧拷贝的再剪辑中,类似的错误还是会发生的。
(2)故意作出的改动
无声片时代,一部影片由两个因素构成:画面以及中间插入的作为对话与解释词之用的字幕。为了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影片字幕当然要译成上映国使用的语言。
但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