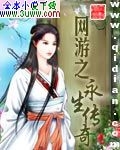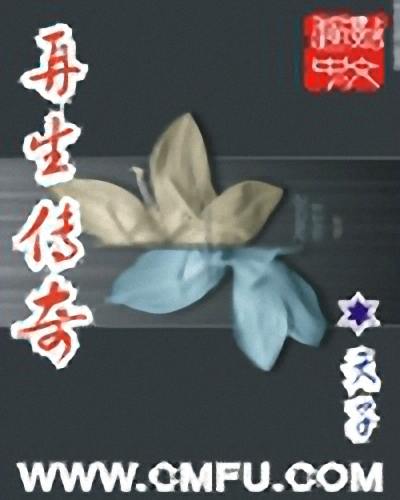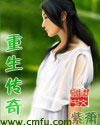安徒生传-第7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世纪50年代安徒生游经慕尼黑时,除了看望考尔巴克,还要拜访巴伐利亚王室。1852年,他收到了第一份官方的邀请,去参加马克斯国王将于慕尼黑南部的施塔恩贝格湖的王室狩猎城堡中举办的宴会。慕尼黑南部的施塔恩贝格湖位于慕尼黑西南向着巴伐利亚有积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方向。安徒生驾着活泼的四轮马车远远地就可以瞥见那里的山脉。
马克斯国王很有学识;曾在柏林和哥廷根学习并多次到意大利和希腊游览。他对科学极其感兴趣,对丹麦和其文化颇有了解。1852年6月他们首次见面,国王就向这位丹麦作家吐露他长久以来就想到哥本哈根的海湾去尝试时髦的盐水浴。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个经常谈论的话题。尽管马克斯国王在艺术方面的热情不如他父亲———讲究吃喝的路德维格一世,但他对安徒生的作品非常熟悉,曾读过《即兴诗人》和一些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童话,如《小人鱼》和《伊甸园》。
这一切都是健谈的国王在一次富有艺术气氛的航程中告诉安徒生的。航行的目的地是位于慕尼黑南部的施塔恩贝格湖的浪漫的罗森尼塞尔岛。马克斯国王在岛上修建了一座四周有赏心悦目的玫瑰园环绕的别墅。在途中,安徒生朗读了《丑小鸭》。国王用一束来自岛上古老的花树上非常美丽的花作为感谢。在安徒生眼里消除了王室和普通人之间区别的另一种独特而敏感的友谊,现在开始蓬勃发展了:
“我独自和国王坐在长凳上。他谈到上帝所赐予我的一切,谈到人类的命运。而我说我不愿做一个国王,因为国王承担的责任太大而我无法胜任。他说首先上帝得提供力量,然后一个人才能做他所能做的。我们的交谈热情而私密。返航途中,我又读了《一个母亲的故事》、《亚麻》和《缝衣针》。清澈的湖水,带着白雪和阳光的蓝色山脉,让我们上岸时感觉置身童话般的世界。喷泉跳跃着,国王感激地向我道再见。我见到了两个年少的王子并吻了他们。”
。 想看书来
考尔巴克和马克斯国王(2)
7岁的路德维格王子和4岁的奥托王子此后得到了充裕的时间听这位丹麦的作家讲述天鹅和鹳的故事,尤其是王储路德维格,他的兴趣要更大一些。1865年,他18岁时成为臭名昭著的路德维格二世,一直到1886年他过早而神秘地死于慕尼黑南部的施塔恩贝格湖,这个年轻古怪的路德维格以理查德德?瓦格纳慷慨的赞助人著称。同时他还是不切实际的野心勃勃的建筑狂。他耗尽了国家的财库就为在巴伐利亚南部建立许多奢华的童话城堡。而浪漫的天鹅和鹳只能在庸俗的装饰和家具上才能扮演重要角色。所有这些城堡中最为出名的是位于慕尼黑以南与奥地利毗邻的非常高大的斯科劳斯?纽施万斯坦。路德维格二世把塔建在高山地形上一个如此显要庄严的地方,这使其在高度、规模和装饰方面都远胜于500米外他父亲的黄色城堡。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曾于1854年6月访问过较小的霍恩施万高城堡,那里是路德维格二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安徒生在马克斯国王和王后玛丽娅?赫德维格(前普鲁士公主)善解人意的陪伴下度过了令人愉快的3天,陪同的还有两位年轻的王子,路德维格和奥托。安徒生差一点就决定待在慕尼黑了。他的嗓子发了炎,脸上又长了个疖,有几天他到哪儿都得敷上软和的膏药,围上围巾———甚至去剧院都不例外。但是安徒生从不拒绝一位国王的邀请。经过了艰苦的火车旅行来到奥格斯堡,他又登上了去福森的马车。短暂停留之后,一辆皇家马车已经等在那里,准备送这位丹麦作家走完风景如画的最后几公里。最后他终于来到了皇家旧天鹅堡城堡的庭院,由自己的男仆带到房间里。随后他立即被马克斯国王邀请上了去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马车,在那里他们再次谈论了安徒生的生平和作品。在此期间,马克斯国王从1847年起开始阅读安徒生的德语自传。国王满怀着敬仰之情,主要是因为安徒生本身是这样一个纯洁自然的人民之子,克服了重重困难,随着时间的过去,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一切———马克斯国王严肃地说———都源于安徒生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安徒生没有否认国王的说法,他的确从信仰中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安徒生的生活正在翻开另一个难忘的篇章。趁男仆还没有熄灭避暑别墅的灯火,他拿出日记本记录了对这一天最后的印象:
“这是个温暖、宁静的夏日傍晚。一只蚊子叮在我的脸上,国王把它赶走了。喝傍晚茶的时候我朗诵了《柳树下的梦》和《完全是真的》。国王很早就离开了,王后陪着我们,送给每位女士一朵杜鹃,也送给我一朵生长在阿尔卑斯山上的花。晚餐我们吃的是国王打的野味和王后捉的一条狗鱼。她真是美丽动人,看上去聪慧异常;她和我谈了很多,我们谈得很愉快。我还见到了两位小王子。等我上床睡觉时,已经差不多12点了,整个人都觉得筋疲力尽。”
在前一天的长途旅行中安徒生带回了一束野花,装在用天鹅剪纸做成的盒子里,送给了王后。安徒生不仅答应第二年再来,而且将为圣诞节写一篇长篇童话,背景就是这个美妙的天鹅之家,坐落在巴伐利亚的皇家城堡。这个童话没有写成,但是他和国王夫妇一直保持联系,并经常在各种场合遇到他们。1854年安徒生做客时,就给两位王子讲了很多童话故事,还给他们做了一些锡兵和单腿站立的苗条舞女的剪纸,此后王子们经常谈起安徒生。王储路德维格对安徒生的童话特别感兴趣,对《坚定的锡兵》及其主人公丧失生命是如此着迷,以至于当发现他的3个玩具士兵的脑袋不见了时,非常难过。“3个勇敢的小锡兵死了!我真不知道安徒生知道了会说些什么。”
路德维格王子根本不需要担心,因为安徒生一点也不知道。这位丹麦作家在1860年慕尼黑的一次戏剧表演上最后一次见到巴伐利亚王室时,只匆匆瞥了王子们一眼,那时他们已经长大了。安徒生去世之前一直与巴伐利亚王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95年11月,安徒生被授予无上荣耀的“马克西米利安科学与艺术奖章”———该奖项一向只颁给德国人。丹麦和丹麦人又一次发现,德国人总是愿意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破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背叛奥斯特(1)
安徒生于1956年8月开始着手完成他的小说《生存还是毁灭》。此前他刚从不到6年内的第五次德国远行归来。当时他待在格洛鲁普庄园。在那里他也读了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书,例如弗雷德里克?法布里的《反唯物主义信件》。安徒生赞扬了这本书在认知上的价值,说:“它对我的启发很大,但它没能明确地将我所有的唯物主义论断都清除掉。我的经历更多一些,对精神和物质有同样的认识,但我心中两种无形的东西此起彼伏。”这是毋庸置疑的。在1856~1857年安徒生最全身心地投入到《生存还是毁灭》上的那段时间,他曾被鬼魂弄醒。它们使庄园里的钟楼响起来了。幻象在模糊和黑暗中涌出。昏昏欲睡的安徒生一会儿认为自己在君士坦丁堡或日本,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因为油腻的扑克牌的刺鼻气味而感到窒息。有天晚上作家梦见自己在坐着写作时,书上的字突然间将纸引燃了。
“存在的”是否比“不存在的”更真实和确定呢?“存在”代表着什么呢?这些便是安徒生于1857年5月出版的《生存还是毁灭》一书中的孤儿尼尔斯?布莱德不得不深思的问题。这些哲学问题提出后,人们对现代科学及其与艺术的关系的看法开始转向肯定。这一点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安徒生就在游记《在瑞典》中提了出来,并将这种想法告诉了奥斯特。在游记末尾,有一首致《诗歌一般美丽的加利福尼亚》的赞美诗,其中说道:
“科学的阳光将穿透作家明亮的眼睛,使他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小和无穷之大中所蕴含的真理与和谐。这将净化并丰富他的才智和想象力,并展示给他超越这些话本身的新形式。就算是个人的发现也将引发这种探索之旅。当我们将人类世界置于显微镜之下时,将看到一个多么童话般的世界啊。在新式喜剧和小说中,电磁学将成为主线。多少幽默的故事将涌现出来,就像我们这些渺小而又骄傲的人类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从一个银河系到另外一个银河系来观望宇宙一样。”
在1851年奥斯特去世后的几年里,安徒生作了许多旅行。而且大部分的时间他都用在了思考而不是写作上。渐渐地他开始对奥斯特及他的《自然中的神灵》越来越持批判态度。上帝的影响对他又起了作用。一方面,在写给B*9郾S*9郾英吉曼的信中他说,利用上帝赐给我们的判断力可以很容易地对上帝做出认识和评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也很难做到。至此,他没有疑问了。他在《生存还是毁灭》一书结尾中写道:“信仰来自于上帝,并非思考所能得到!”这本书包含了最多的了解安徒生作品理论体系的钥匙。
像作者大多数的长篇作品一样,这本小说在审美上不能算作是完美的作品;与此相反,它只是一堆混杂的信条和观点。许多深奥难懂的哲学和宗教问题被提了出来,就像同时向空中抛了无数的小球。其中也有许多是关于存在的问题,不过没有给出什么实质性的答案。15年之后,评论家乔治?布兰迪斯从丹麦作家中找出了他们超越自身而参与社会的证据。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不光掀起了一场论辩,而且把现代人自身当作了讨论对象。
我们的信仰和知识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有没有永恒的生命?当躯体的生命之火熄灭时,灵魂的余烟是否也散去了呢?这些都是在《生存还是毁灭》一书中被大胆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本书主人公尼尔斯?布莱德及其犹太情人埃丝特,需要面对的难题。直到3年战争和一场霍乱大流行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尼尔斯?布莱德与读者见面时是哥本哈根圆城的一名守卫的儿子;一贫如洗。突然有一天他成了孤儿,孤零零地一个人被留在了世界上。牧师杰普特斯?莫勒鲁普成了这个富有才华而又敏感的孩子的庇护者,并将他带回了斯克博格的家里。牧师的女儿鲍迪欧迅速对这个收养的兄弟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不久,人们发现这个天生虔诚而又好问的尼尔斯希望像他继父一样做牧师。但是他在哥本哈根学习神学时接触到了新时代的无神观点。尼尔斯迅速投入到了对单细胞的研究之中,不再关心什么更深入的看法。现代科学用一种全新而又激进的眼光来看自然及人类的存在,这改变了尼尔斯的生活观和世界观。像霍尔伯格作品中的埃拉斯穆斯?芒特纳斯一样,尼尔斯回到了日德兰半岛,这个真诚地等待着他这个收养儿子的家里。他被当作异教徒迎接了回去。当他承认说自己不再想做牧师而是想当一名医生时,这一点被进一步证实了。当他与犹太姑娘埃丝特订婚后,那些旧的宗教体系彻底垮掉了。埃丝特和他一样是一个爱思考的年轻人。但与他不同的是,她完全相信灵魂的不朽。当尼尔斯?布莱德在战争中与死神亲密接触时,他更加笃信所有这些信仰上的想法了。在他回到家康复后不久,埃丝特得了不治之症。她临终之时,尼尔斯又回归了他强烈而又坚定的对上帝和永生的信仰,这也是他儿时的鲜明特征。在正统基督教的教义里,这是一个悲剧爱情故事的“美满结局”,但是这对读者来说完全不容易接受。尼尔斯的信仰转变相对于前面150页的内容来说显得比例失调。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尼尔斯?布莱德走向成熟和现代观点的发展历程:
txt小说上传分享
背叛奥斯特(2)
“相信我,我们对自我和情绪的掌握,不会比我们对那些使我们肉体和灵魂分离的物质的控制强多少。我们的各种情绪随着血液的循环而出现,这正是为什么我大胆地相信并断言,我们对情绪稳定性的把握并不比没受过训练的动物强多少。”
安徒生选择在1857年奥斯特去世6年后向读者给出的结论,看起来更像是直接放弃了以自然科学而非宗教为基础的生命观。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地看一看小说匆忙完成的最后几章的字里行间,我们会发现它不仅仅是展现尼尔斯内心一系列矛盾的力量那么简单。小说最后的场景或许更应该被理解为表现出信仰和科学已经不再在尼尔斯内心争战,因为它们已经融合为对上帝在自然中的抽象存在和自然科学的具体存在的一致认可。与所处的时代实际相脱离的信仰是盲目的,尼尔斯得出结论。他从他死去的妻子埃丝特那里学到了这一点。在她的灵床之前他看到了圣光,从而了解到自然科学对人类的客观理解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关于现代人类的孤立的知识,正如喜欢唠叨的尼尔斯所说的,它是“无止境的摸索,与时代脱节,其唯一的论据就是上帝;没有上帝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这个观点与安徒生在1855年12月末写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信中表达的观点完全一致。在新年来临之际———屋外大雾弥漫,冰冷刺骨———他谈到了他要在新小说里采用的“物质主义”的研究。作者的观点与那些没有生气的生命观信徒完全不同:
“整个虚假的系统已经被演绎到了极致,然而也还只是一个系统而已,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种绝望的存在。人类成了所有造物中的小小的一颗螺丝钉;神———甚至上帝———都消失了;多么可怕!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我来说,科学阐明了神的启示;我睁大双眼朝着别人盲目追寻的目标走去。上帝会容许被他自己赐予我们的感官所看见。自然和圣经之间的和平和和谐才是我所追求的。”
19世纪50年代后期,安徒生像他小说末尾的尼尔斯?布莱德一样,甚至比奥斯特更过分,想把自然中不知名的引导力量称为“上帝”,而不是仅仅称之为“自然中的神灵”。在这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