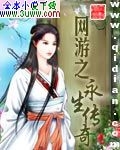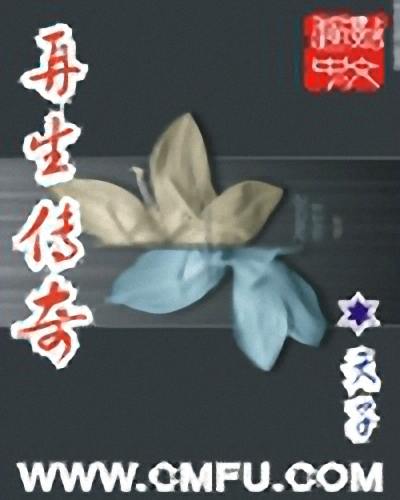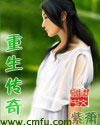安徒生传-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831年5月19日,安徒生在汉堡写下的第一封用信鸽传回的信中,他异常小心地打开了那扇通向梦想宫殿的大门。从修辞意义上可以说,在这封信中,他给朋友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他希望的话———用文字把自己纳入到作家正在拉开帷幕的一场浪漫演出中。从安徒生的信中可以看出,科林现在不仅可以公开他已经感激并接纳安徒生的热情,还可以表露自己对这位作家的专一情感。事实上,这封发自汉堡的信正是安徒生为这种敏感而不可告人的男人之间的友情进行铺垫的演习,也体现了作家的天才。正如克尔恺郭尔《非此即彼》中的色情骗子所言,唯一的窍门不过是含糊其辞,听者在听的时候可以从某个方面理解一件事情,但马上会意识到,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翻译这些言语。安徒生在信中所做的是,首先告诉自己的朋友———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处在内心的悲伤之中,但却在信中回避是谁或是什么让他的内心在过去几年中如此痛苦。然后他又极其谨慎地让自己不至于揭开这种痛苦的深层次原因,而仅仅说,他一直非常压抑,很多次,他都试图让朋友了解他的私人问题,但每到这个时候他却欲言又止。“但是,我非常的恐惧;我害怕你也许根本就不想接受这样的事情。”
信中弥漫着神秘的色彩,而在模棱两可的语言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狡猾的目的:引诱收信人———爱德华?科林,让他在不知不觉间把发信人所暗示和隐藏的一切写在自己的信中。当收信人被诱入陷阱、让自己的名字和言语置于这种痛苦之中的时候,发信人就可以利用自己设下的诡计,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纳入到无限的可能性之中,而不仅仅是实现与里伯格?沃伊格特的分手。发信人———安徒生的字里行间,上演着一场从来没有公开的爱情戏剧,由于信文一直略去具体的人名和性别,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其中所涉及的很可能是男人。在这段时期安徒生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错综复杂、涉及性别角色和恋爱目标的游戏。例如在诗歌《那就是我所说的她》中,就出现了一场在人称代词方面如同捉迷藏般的真实游戏。
在这些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中间,安徒生终于在发自汉堡的一封信中扯下了自己的伪装,跪在科林的面前,说出心中那永远也不可能被误解的一句话:“用du称呼我吧!”同样,他永远也不可能面对面地对行为端庄、一向中规中矩的科林说出这样的话,只有远隔通过无数信件搭建起来的海洋和高山,他才有胆量说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短短的一句带着感叹号的句子“用du称呼我吧!”便让安徒生对爱情的畏惧和担心跃然纸上。在这些年里,安徒生信中的语言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言语中的情感也日渐升华,正如安徒生所写的那样,当他敞开自己的情感,说出内心深处梦想的那一瞬间,他“怦然心动”:
“在所有人中,只有你才是我最尊敬的真正朋友。因为你一直这样善待着我,亲爱的科林。我真的需要一颗敞开的心,我的朋友,但是,让我这样爱着的人必须同样也有一个这样热情的灵魂。我必须这样地去尊重你,而在我所喜欢的其它那些人当中,却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灵魂。我还有一个要求。你也许会嘲笑我,但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取悦于我的话,想告诉我,你同样地尊重着我———假如我值得这样的尊重,那么就用du称呼我吧!我希望这样说,不会让你生气。我永远也不会当面向你提出这个请求,但现在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不在你的面前……你生气了吗?你根本无法想象到,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我的心狂跳不已。”
但是,像爱德华?科林这样刚刚毕业的法律学生,是不可能被轻易蒙蔽的,对于安徒生的请求,他的反应是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不”。在1831年5月28日的一封回信中,科林提到,他已经清晰地注意到安徒生的痛苦,甚至要求了解其中的缘由。但科林绝对不会容许安徒生继续用花言巧语来诱惑自己,而且从来没有说出这个所谓痛苦的缘由。只有在安徒生要求他用非正式的“du”相称的这件事情上,科林才毫不含糊地给以直接回绝。事实上,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一丝的希望。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林是坚决捍卫传统男人美德的人,比如自我控制、责任感和勇气;他憎恨男人之间破格的感情关系。还有一点同样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安徒生来说,重复这样的请求是毫无意义的:
用“du”称呼我(3)
“在这里,我真诚地把我性格的每一个方面向你一一袒露。只有这样,你才不至于误解我———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对于你要求我们用‘du’彼此相称的请求,我希望借此机会说出我的看法。正如我曾经提到的,安徒生,我发誓,我现在所说的都是实话!……在我们的关系中,这种称呼上的改变有什么目的呢?难道是把我们之间友谊的信号传递给其它人吗?那只是表面上称呼而已,对于我们双方都没有任何意义。难道我们的关系还不够快乐、有益于我们双方吗?为什么要从这种拘泥于形式上的变化开始呢?形式就其自身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但却有可能会像我说过的那样,带来不愉快的感觉……对于你的要求,不存在任何会让你发怒的事情;我不会误解你。我只是希望你同样也不要误解我。”
直到收到这封在感情形式上没有给他们之间的友情留下任何改变希望的信之后,安徒生才最终在前一年的冬春之交,披露了自己痛苦和悲伤的表面原因。1831年5月11日,安徒生在柏林写了一封信,对科林真诚的答复给予感谢,同时,安徒生又强调,他还是希望用敞开的心扉,真诚地对待“我真正、也许是最真诚的朋友”。然后,他最终说出了那个给他带来痛苦的人的性别和社会地位。但是,这个谜语还远未结束,因为他依然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去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个富有、美丽而且风趣的女孩,我们之间彼此坦诚相待。但她已经订婚了,现实条件迫使她嫁给一个仅仅为了她的财产而娶她的男人。在她结婚之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她留给我的只是几句话:她要我把她当作妹妹,要我忘记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的原因。哦,我竟然像个孩子那样地哭了。”
对于任何一个像爱德华?科林这样几乎无所不知的哥本哈根人来说,这种半真半假的独白根本不会让他感到半点吃惊。在以前写给安徒生的一些信中,他已经说过,他有着一双对谣言明辨是非的耳朵。早在1830年夏天的时候,他已经听说了安徒生与商人沃伊格特的女儿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关系。这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里伯格为什么会借探望生病亲戚的机会在哥本哈根呆了几天,当时是10月和11月之间,她曾经在一天晚上遇到安徒生,并听到他朗读自己的歌剧《乌鸦》。
由于爱德华?科林当时正在日德兰半岛避暑,于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只能把他在德国旅途中写下的最后一封长信带回哥本哈根,然后才把这封信从哥本哈根寄出。这封信的结尾同样体现了作家一向的乐观态度,它表明,正处于如痴如醉状态之中的安徒生,似乎不仅没有忘记对方毫不客气的拒绝,而且还梦想着建立一种比以往更加亲昵的敏感友情:
“是的,在我的心中,那是我永远希望能向你倾诉的,你也许会一如既往地像现在这样对待我:一个兄弟般真正的朋友。要是我能让你阅读我的灵魂,那该会多好啊,那样,我就会如愿以偿地得到你。”
科林描写安徒生的作品(1)
至于1831年的冬天以及1832年的春天和初夏,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它事情,以及这段关系是如何发展的,我们无从得知。当时,安徒生已经通过给对方写信的方式,向爱德华的妹妹———路易丝发起了感情攻势。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信件解释为作家向整个科林家族示爱的方式,也可以看作是向爱德华表示敬意的策略。但是,和其它时期与科林家族内容全面、频率稳定的通信相比,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也许在那段时期里,信件往来根本就不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安徒生和爱德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哥本哈根。根据安徒生在1831年11月写给亨丽埃特?汉克的信来判断,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密。科林仍然坚持用正式的称呼(“De”);然而,在那段时间的初期,他似乎对安徒生百依百顺,作家也马上注意到这一变化,并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安徒生在1831年11月的日记中写道:
“我刚从科林家回来。那个二儿子,那个像哥哥一样让我一直爱戴的非常出色的家伙,待我亲密无间,他的温情融化了我的灵魂。我们彼此承诺,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成为一生中最真诚、最亲密的朋友。”
但是,包含1832年的夏天在内的那段日记和日志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段友情的发展到底如何,当时,这位处于高产阶段的作家,正在把自己的渴望和痛苦融会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文学创作中。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安徒生先后完成了《影子》和诗集《丹麦诗人杂评》。他还完成了根据沃尔特?斯科特小说创作的芭蕾舞剧《拉美穆尔的新娘》剧本,以及另一出歌舞剧《船》。其中后者改编自一个外国歌剧,剧中的男主角是性格内向但却知识渊博的商人乔纳斯,他声称自己在爱情方面是“一块死掉的石头”。他所面对的则是自己的老朋友,一个英俊潇洒的海军军官:爱德华———显然,此时的这个名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占据着安徒生的大脑和语言。
在安徒生爱上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的这段关键时期内,他们之间的情书甚至是所有书信往来都无从寻找。作者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责怪,因为在安徒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收集和保存了各种形式的文稿和书信。他用袋子、盒子和箱子把所有信件、明信片、手稿和剪报保存起来。在他的日志中,安徒生一直在尽可能地记录下他所发出的所有重要信件。尽管并非所有信件都能做到,但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还是有据可查的。基于同样的原因,安徒生在1830年到1875年期间接到的信件大部分得以保存,这些信件收集在爱德华?科林于1875年8月接收的文稿中,爱德华?科林随后对这些书信进行了整理。而安徒生所指定的另一位共同遗嘱执行人,莫里茨?G?梅尔基奥尔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安徒生在遗嘱中并没有允许梅尔基奥尔干涉这部分财产。当然,我们可以有十足的理由对此做出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个遗产受赠人———爱德华?科林一直对其朋友的遗愿置若罔闻。在安徒生于去世前1个月增加的遗嘱附录中,作家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所有手稿和关于安徒生的重要信件交由A?比尔和尼科莱?博使用,但之后应转交州议员科林,并最终作为科林的私人财产。”在去世之前,安徒生已经容许他的两个好朋友———编辑兼国会议员卡尔?斯蒂恩?安徒生?比勒和青年作家尼科莱?博,共同编写一本书信和童话故事合集。在经过了与爱德华?科林的一场对峙之后,这本合集便在1877年到1878年期间草草出版了,显然,爱德华对于这两个人阅览安徒生私人文档集的权利根本不当回事。
正如安徒生在最后一部童话《牙痛姑妈》中所写的那样,箱子里的有些东西最终总是放在原本不该放的位置上。在作家去世之后,决定箱子到底应该放在哪儿,箱子里面到底应该放什么,则完全取决于爱德华?科林了。他可以决定,哪些东西应该返还给写信人,哪些东西可以保存下来,充实到《科林书信集》中。有了“所有重要的手稿和信件”的法律依据,爱德华?科林就可以对到底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做出自己的评价———最终的分类很可能是在他的儿子乔纳斯的协助下完成的。此外,他还决定,为了便于比尔和尼科莱?博完成安徒生所希望的作品,可以允许两个人阅读和使用安徒生的书信。与此同时,科林告诉这两个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安徒生与科林一家之间的通信内容,因为他本人也想写一本关于自己的朋友———安徒生的书,而这些信件当然是不可或缺的素材。
于是,爱德华?科林马上承担起审查员的角色,他知道,在存放于盒子和箱子里的这一大堆信件中,他自己需要的是什么。1875年秋天,在对这些材料进行分类之后,科林写信给莫里茨?G?梅尔基奥尔,后者及其家人曾经在安徒生生命中最后的几年里照看过这位作家:“在此谨告知您及您的家人如下事宜,对于在安徒生手稿中发现的亲笔信,本人有义务对其中所有健在的写信人交还上述信件。我需要马上得到您的签名,并以此进行分类。因此,各位尽请放心,本人尚未阅读这些信件。”换句话说,多年来曾经给这位略显温情和敏感的作家写过信的所有人,现在都可以松口气了。所有这些轻率的举动,其中很多都与科林家族或是科林的朋友有关,现在都将回到最初的发信人手里,而不是被人们搜集、封装并保存起来,留给后人去研究安徒生的作品,去窥视他的私生活。早在19世纪30年代,爱德华?科林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他本人与安徒生之间的通信,总有一天会成为人们竞相追逐、让人羡慕的文字数据。这一点在1836年夏天一封畅谈未来的信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爱德华以一种颇具讽刺的语调重读了安徒生近期的一封信,他用眼光扫了一下,用德文就信中一个特殊而含糊的部分写下了这样一句对未来意义非凡的话:“当安徒生与科林的正式通信出版之时。”
科林描写安徒生的作品(2)
但是在1875年秋天,他还是把这些信送还给了发信人,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遗憾的决定。在对这些古老的信件进行了彻底但草率的分类并返还发信人之后,有一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在整个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