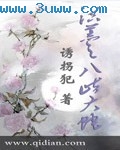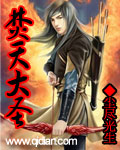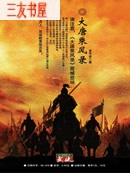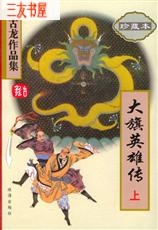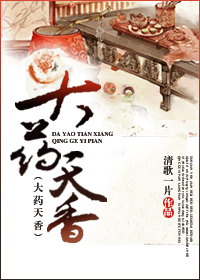论北大-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仔细看鲁迅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鲁迅首先是把“整理国故”看作是一种社会思潮。它当然与作为倡导者的胡适有关,但又包括了更广的范围,如鲁迅这里所说,既有胡适这样的“少年”,也有“老头子”,他们之间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如鲁迅这里所说的只讲“保存”而反对“求新”,就未必是胡适本人的意见;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考察,这样的差异就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关注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的实际作用,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中所显示出来的实际意义,而这种实际意义与倡导者的初衷未必一致。以前我们讲过鲁迅在五四时期批判儒家学说时,他并不关心与讨论孔子当初是怎么想的,即所谓“原初儒学”的教义,而是着眼于“儒效”,儒家学说在中国产生的效果;现在,他又把这样的方法来考察胡适的主张了。这本身也就很有意思:胡适正是以做孔夫子那样的“当代圣人”为自己的追求的。
那么,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整理国故”这一口号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怎样的呢?也在1924年,曹聚仁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有这样的描述与分析:“国故一名词,学者各执一端以相答应,从未有确当的定义。于是,那班遗老遗少都想借此为护符,趁国内学者研究国故的倾向的机遇,来干‘思想复辟’的事业。”见1924年3月2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胡适的朋友陈源后来也说,胡适作为“民众心目中代表新文###动的唯一的人物”(这话自然有些夸张),他自己研究国故不要紧,“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哑起来,那就糟了”。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3卷63期(1926年2月20日)。其实,早在1922年,周作人就写过文章,指出:“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如仍一切依照“中国的旧说”,“整理国故”就“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他特别提醒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强调“现在所有的国粹主义的运动大抵是对新文学的一种反抗”,而且会发展为“国家的传统主义,既是包含着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思想界的倾向》,《周作人自选文集·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88—89。胡适当即写文章反驳,认为“国粹主义”“差不多成了过去了”,周作人举的许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64、66。不过,胡适自己后来还是发现了他的倡导所带来的弊端的:“现在一般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集》卷4《胡适文存》3集,页114。他同时又写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整理国故与“打鬼”》,也就为了作一弥补吧。但这已是1927、1928年,也就是鲁迅等提出批评三五年之后;而胡适公开承认这样的“可悲的现状”本身却是表现了他的坦诚,说明这确非他的本意,这里所发生倡导者的初衷与实际效果之间的错位,真是“最可悲叹”的,这也算是胡适的悲剧吧。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2)
现在,再回到1924年鲁迅的批评上来。鲁迅的观点其实是很明确的:作为个人,或出于兴趣,或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要“整理国故”,甚至要“读死书”,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拿“整理国故”作为一面“旗子来号召”,进而引导青年,以为“大家非此不可”——这正是胡适的要害所在,也正是鲁迅要加以辩驳之处:在鲁迅看来,它是会扼杀人的生机,并使“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的。
于是,又有了1925年“青年必读书”的事件。这本是由《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活动引发的,在这之前,胡适和梁启超都分别开过关于“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针对胡适的,至少是他对“整理国故”思潮的某一反应吧。他先回答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交了张白卷;但又加了一段“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卷3,页12。
鲁迅的这一意见在当时以至今日都引起很大的争论。许多人都以此作为鲁迅“全盘否认传统”的证据,似乎是鲁迅的一大“罪状”。但如果仔细读原文,就不难看出,鲁迅在这里主要不是讨论“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学理问题,而是一个“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什么”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讲过的鲁迅的基本命题“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延伸。在他看来,当下的中国青年最要紧的是要做“活人”而不是“僵尸”,是要“行”而不是“言”,这就必须和实际生活相联系,而不能脱离实际生活。正是从是否有利于现在中国青年的生存发展的角度,他对“中国书”与“外国书”对青年人的精神的影响与作用,作出了不同的评价。而他认为中国书总是使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却并非一时偏激之言,而是他长期考察、思考的结果:大家该记得,早在二十世纪初鲁迅对中国文化就有过不“撄人心”的概括与批判。《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卷1,页70、71。这更是他最为痛切的生命体验与人生记忆;因此,他反复强调“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卷1,页302、301。——可以看出,鲁迅不是以指导者的姿态出现,更不是把自己当作“前途的目标,范本”,他是将心交给青年,把自己痛苦经验告诉年轻人,不希望曾经纠缠自己,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痛苦的古老的鬼魂再来纠缠年青的一代,期望他们不要重走自己的老路,而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自己与前人的新的路来:他依然坚守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卷1,页135。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他担心,如果号召青年人都读古书,钻到故纸堆里去,而青年又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与科学方法,结果“进去了”却“出不来”,被故纸堆所俘虏,就可能由“活人”变成“僵尸”:对此,他确实有“大恐惧”。
后来,鲁迅又把这种鼓励青年钻故纸堆,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倾向概括为“进研究室”主义,进行了更为尖锐的批判。在1925年的《通讯》里,他这样写道——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3)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通讯》,《鲁迅全集》卷3,页25。
这里说的“学者”是应该包括胡适在内的——但查胡适的著作,似乎并没有“进研究室”这样明确的说法;1919年6月29日胡适曾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一篇《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引用陈独秀的说法:“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来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17。但这一说法似与鲁迅概括的“进研究室”主义无关。所以这仍然是对一种思潮的概括,它大体包含两个含义,一是鼓励年轻人钻入研究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和社会实际、现实生活脱离,闭门读书;另一就是读死书,使人成为“书厨”,结果思想“逐渐硬化,逐渐死去”。鲁迅后来说,“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读书杂谈》,《鲁迅全集》卷3,页462。
一个月以后,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把“进研究室”主义置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专制体制中来考察它的实际作用,就提出了更为锋利的批判。他说,专制的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被统治者)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绝对服从自己,另一方面又要“贡献玉食”供自己享受,这两者是可能存在某种矛盾的:“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注射在臣民的身上,既使其知觉神经“完全的麻醉”,不能思想,但保留运动神经的功能,还能干活,也就是“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鲁迅指出,这样的替统治者着想的“良药”,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就是“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还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类。《春末闲谈》,《鲁迅全集》卷1,页215、216、217。——这样的批判,已经跳出了具体的人和事,真正把“进研究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揭示了它的实质:初初一听,似乎提得太高,似难接受;但仔细思索与回味,却不能不承认,它是击中了要害的。
(五)
我们已经说到了在“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不妨再从五四以后胡适与鲁迅对青年的几次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的比较中,对这一问题作更深入的展开和讨论。
先说胡适。五四之后他连续对北大学生作了几次演讲。——作为今天北大的学生,重听几十年前北大讲台上的声音,这大概也是很有意思的。
在1920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胡适明确地提出,北大要真正成为“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必须“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他说——
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普及和提高》,《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36、437。
1921年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又有一个讲话,谈到“年来因有种种的风潮,学校的生命几致不能维持,故考试不严,纪律也很难照顾得周到”,因此强调要“严格考试”和加强纪律。接着又针对“外界人说我们是学阀”,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想要做学阀,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做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另一方面要造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目的。《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38、439。。 最好的txt下载网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4)
1922年,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适再次表示“最感惭愧的是(北大)在学术上太缺乏真实的贡献”。他引用龚定盦“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句,强调“国立大学不但要开风气,也是应该立志做大众师表的。近数年来,北大在‘开风气’这方面总算已经有了成绩;现在我们的努力应该注重在使北大做到‘又开风气又为师’的地位”。《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47—448。
不难看出,胡适对北大学生的引导和要求,显然有两个重点,一是要以“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求高等学问”,“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同时建立严格的制度与纪律:这与我们前面所说的蔡元培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即是要致力于学院化、体制化的建设工作。这样的追求和努力,就使得胡适成为中国的现代学院派的最主要的代表,其影响自是十分深远。另一方面,胡适又号召学校里的师生“要当学阀”,这当然也指他自己。这就是说,胡适提倡学院派的学术,其意并不在纯粹的学术,而是要通过学术造成一种“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借学术“实力”来影响社会,“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即所谓“为(天下)师”,进一步利用学术权力来取得政治权力,用后来胡适的一篇演讲中的说法,就是“社会送给我们一个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做事”《学术救国》,《胡适文集》卷12《胡适演讲集》,页454。,“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因此,他对北大学生的期待,不是一般的专家,而是有“势力”的“学阀”,而且有可能还要当“领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培养“精英”,技术精英与政治精英,而这两者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我们再来看鲁迅。鲁迅在五四以后主要有两次演讲,一次是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娜拉走后怎样》;一次是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未有天才之前》。此外,在同时期的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