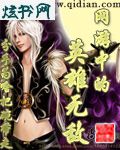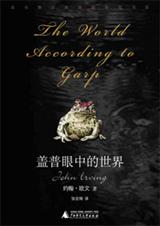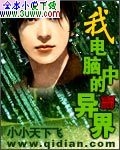诗意中的生意:晴耕雨读-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征服中原到鸦片战争的二百余年里,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家不大的公司在吞并了另一家颇大的公司后经常会做的那样,一直怀着极为警惕的心情做文化整合。
但由于高管团队(朝廷)迟迟未能打出有感召力的新的旗帜,或扶持有代表性的新人物、新楷模,最终还是让下属在心里暗暗不服。这样一种管理方式,与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大帝国的现状相比,已极不合适。
全世界都会见到同样的情况。一家大报(或新闻机构),一定要有自己的明星记者和评论员。一家大证券公司,难免要有自己的明星经纪人和分析家。一家大企业,假如只有一位CEO成天在场面上晃来晃去,而没有明星销售员、明星设计师、明星物流主管,企业内部的人心里也会隐藏着一些酸味。
顾雏军玩格林柯尔的时候,就有香港分析家说过,此君是以“个人代团队”(OneMan Team),惯于只手打天下,等什么时候他身边有了国际投资者瞧得起的干才,才能考虑他公司股票的长线价值。否则他公司怎么好,都只是他个人跟市场讲故事而已;真的怎么样,谁也说不清。可惜直到最后,顾老板身后也未曾出现像样的职业经理人的身影。
民企器量狭小,或情有可原(因为都是小人物出身),但很多大国企的情况好像也是这样,尽管它们的销售已相当可观、业务已相当国际化。中石化、*有什么人才实力?人们对它们的了解可能还比不上性质保密的宇航事业,或基本未改制的铁路部门(铁路部门还有指挥青藏铁路项目的一班人)。
至于华为、中兴一类如云间道士的企业,人们只知道它们那里人才济济,但大概不会像比尔·盖茨那样,在离任三年前就选拔出有名有姓的接班人来。
人们不免心里打鼓:难道现代中国企业家都是看清朝皇帝电视剧长大的吗?
。 想看书来
拿什么取代你,我的帝国?
越读清末的历史,越感到那时的人们,面对西方的扩张,从朝廷策论到战场对应,往往既可笑又可悲,完全是不着边际。现代人不禁要问:一个自古以来崇尚学习、重视学问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国中无人”的尴尬局面?
有人说,一个原因,就是清朝前后二百年的文字狱所造成的意识麻木、思想空白。正如敏感人士龚自珍总结的: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咏史)
所谓“田横五百”,是汉初的一群不愿接受刘邦统治的人,此处可理解为争取自主命运的精神。为什么这种精神再也见不到了呢?诗人责问。
全诗的意思,是谴责两种人的存在让社会窒息:一种是盘踞权位、飞扬跋扈的贵族;另一种是那些把社会责任感抛到脑后,埋头私利的士大夫。“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形容的就是那时的文坛风气。
龚自珍还有很多关于人才的言论,都代表了一种文明的危机感:国家没有了勇于坚持自我的人才;社会没有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能力。龚先生最愤懑的表达,就是毛泽东曾引用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实际上,从龚自珍开始,那些身处体制边缘的有识之士,包括后来办洋务、搞改革的那些人,似乎都在为大清朝准备后事。也许他们本来没有那么想(古人到底想些什么,我们现在也只能猜测),但他们似乎有意无意中都在哼着一首“拿什么取代你,我的帝国”的小曲。即使他们死心塌地要挽救大清朝的命运,但真正的贡献,却是启动了文明的传承和对外的交流。
虽然史家说今日中国对清代的继承少之又少,其实中国人重新开始对外学习,却是从那时开始的。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也会想到改革开放中的很多企业,经过了三十年,团队也散了,经营也败了,留下来有用的东西除了空空如也的厂房和一片土地之外,实在说不上其他。但也有些企业,能在危机中聚集起革新人才,几经转折,或许连所有制都有了很大变化,但工人仍在上班,生意仍在壮大。
在那些“本应”失败却未失败的企业里,起码也会有一两个人不顾别人怎样指责、怎样打击,仍会不断地为变革奔走呼喊,身体力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诸葛亮的困境
现在,佩服诸葛亮的人变少了。一说起诸葛亮,不少人觉得他其实也就那么两下子。
其实诸葛亮也是没有办法——倘若他不跟刘备去,也不能给曹操和孙权打工,那两边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不管刘备个人素质有多少问题,好歹他还能对诸葛亮以及身边几个兄弟大致以诚相待。
也就是说,在当时那个条件下,不管诸葛亮跟了谁,充其量也就干到这个地步,实在无法有更伟大的作为。他能跟司马懿那号人吃同一锅饭吗?他到东吴去,谁又会把他当回事?
汉朝崩溃而后是一段很长的动荡年代。各方豪强水平都很低,都没有形成有纲领、有实力、有感召力、又有一个稳定核心的政治集团,自然也都不可能建立和管理一个统一国家。几百年后,在大唐帝国行将崩溃时,从温庭筠对诸葛亮的惋惜里,人们也能读到这种无奈: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牙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过五丈原)
所谓“空寤主”是说诸葛亮白白给刘禅(也就是那位“扶不起的阿斗”)上了那么多课,呕心沥血也抵不上蜀国高层干部谯周在大敌当前下对刘禅劝降的一番话。这里也包含国中无人、治无所赖的意思。
温庭筠的这首诗,在1976年周恩来逝世、*再度遭到贬谪、毛泽东病重期间,曾在北京的高层老干部中间传抄一时。笔者曾目睹他们读这首诗时的凝重神情,但尚不解其中缘由——因为年轻时缺乏历史知识,连谯周是谁都不知道。
另一点耐人寻味的是,第二句中的“柳营”云云,借用了西汉名将周勃的典故。这位老军人在反击吕后掌权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此一时彼一时,相隔两千年,情节、人物不可一一比照了。
在为诸葛亮遗憾的时候,人们总或多或少要责难刘备一番;而刘备则不免要替他那个据说不争气的儿子受过。唐人刘禹锡就有“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蜀先主庙)的感慨,把阿斗狂批一顿。
不过,刘备给蜀国留下一个阿斗,诸葛大师又留下了什么?难道就是那位劝降的谯周吗?“蜀中无大将”(其实也就是“国中无人”)可能并不是他的本意,但却是一个实际情况。作为顶尖的聪明人,诸葛亮看不到这一步棋,简直就不可理解了。
说到这里,唐人李商隐也按捺不住地摇头哀伤: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无命复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筹笔驿)
诗中“储胥”指木栅栏。“管乐”指春秋战国时管仲、乐毅一样的治国才干,“不忝”是不愧的意思。“梁父吟”是诸葛亮爱哼的一首曲子。而“关张”当然是关羽和张飞——他们本身才能就有限,死去之后,蜀国还能怎么办呢(“复何如”)?
实际上,诸葛亮并未能够为蜀国培养或引进什么能发挥显著作用的贤者。明人魏学洢也惋惜道:“南阳虽子房,谁为酂与韩?”说即使诸葛亮的才干可比得上张良(子房),又有谁可以在蜀国扮演萧何(后封为酂侯)与韩信的角色呢?用现在的话说,显然蜀国没能凑得起来一个像样的“管理团队”。
相比以上诘问,唐人崔道融简直就是不给面子的批评了:
玄德苍黄起卧龙,鼎分天下一言中。
可怜蜀国关张后,不见商量徐庶功。
(过隆中)
还记得因母亲被曹操劫持,不得已从刘备身边离去,告别时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的徐庶吗?为什么到了诸葛亮为相的后期,就不能给蜀国物色几个至少像吕蒙、陆逊的人才呢?与崔道融同时代的陈陶也曾经指出:“近来世上无徐庶,谁向桑麻识卧龙?”是不是明星太亮,掩盖了其他星星的光辉?或者诸葛自觉还不够亮,因而身边容不得再有星星?
宋朝的“皇家国防大学”教授何去非对诸葛亮的批评最为严厉,有“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的评语。
诚然,诸葛亮是一个忠臣。所以不论是温庭筠还是李商隐,都不愿那么直截了当地说他的不是;去瞻仰他生前去过的地方,也都是满怀敬畏。而在安史之乱中仓皇逃难的杜甫,狼狈得经常连饭都吃不上,企盼忠臣的心态当然更加热切。杜甫的蜀相诗是大家最熟知的,也是对诸葛寄托了最大信任的,似乎若不是诸葛亮早逝,蜀国就能对付得了司马懿: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
另一篇对诸葛亮有特色的纪念,是清人陈作霖的一首词。那是写来吟咏诸葛亮所引进的一种叫蔓菁的植物。蔓菁是类似白薯的一种可充饥的东西,又名大头芥,也被称为诸葛菜:
将星落后,留得大名垂宇宙。老圃春深,传出英雄尽瘁心。浓青浅翠,驻马坡前无隙地。此味能知,臣本江南一布衣。
(减兰·诸葛菜)
据说蔓菁原本是作为军士口粮而在各处营地栽种的。直到“*”期间,笔者当知青时都吃过。可惜蔓菁种了一茬又一茬,它的传播者的事业却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缅怀历史的“两条路线”
政治越黑暗的时候,文化人对历史的态度就越显得清高——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参与它的机会了。明清时代的咏史怀古就老是带这种酸味。
在明代,有刘昺的“旧梦风云销侠气,繁华看破知荣辱”(满江红·寄水北山人徐宗周);孙友篪的“行人欲问前朝事,翁仲无言对夕阳”(过古墓)云云。
在清代,有朱彝尊的“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卖花声·雨花台);施闰章的“六朝流水急,终古白鸥闲”(燕子矶);沈传桂的“兴亡事,山河坠瓦,消得阮郎愁叹”(永遇乐);江开的“且搁下,砺带山河,好明日,新丰沽酒。笑虎视龙兴,都付阳关烟柳”(长亭怨·由函谷至潼关作)等等。一位叫龚胜玉的清朝人,把这一倾向推到了极致:
检芸编,几行青史,闭门消尽秋雨。江山零落如残弈,付与渔樵共语。评跋处,有多少,英雄割据争龙虎?烟飞云集,算绣岭宫前,延秋门外,往事若朝露。思往事,减得愁怀几许?纷纷成败休诉。横戈跃马今安在?总被大江流去。归何处?君不见,北邙高卧麒麟墓。君须记取。看谁是谁非,低回掩卷,一醉论今古。
(摸鱼儿)
这里已是酸味扑鼻。汉唐历史已被简化为“英雄割据争龙虎”而已。“谁成谁败又有什么好说的!”作者聪明人似的唱道:“记住吧,各位!横戈跃马的人都是一样下场!倒是我们作为后人,偶尔来侃侃往事,喝喝小酒,岂不潇洒!”
以上诗篇和诗句,从艺术上说,在同时代算得是上乘的,但都与唐人咏史怀古作品有了很大不同,那就是自动与现实保持距离,因而也缺少了对时政的警示,更缺少像杜甫、李白、李商隐、杜牧等人那种恨不能把脑袋都磕出血来的激情投入。
唐人吟诵历史,是为了参与现实,是知行合一。但到了明清时期,当权者压制批评,士大夫基本上参与不了什么,有时想起来参与也摸不着要领,所以也就不屑于参与了。唯一剩给他们玩的游戏,就是玩“酷”了。而最“酷”的龚胜玉,就“酷”到了把历史当成下酒小菜。
听人们怎样追述历史,就能看出他们的精神世界,也能看出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的感受到的动力和压力。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现代人。有人鼓足了干劲要创造历史,因为心里有太多不服气的地方;但是在他们身边,总是另有人吃饱了喝足了,摇着扇子调侃历史,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文采。
强制逻辑的结果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曾有很多人(六国贵族)想刺杀他,但都没有成功。可为什么他的庞大帝国,竟然被陈胜、吴广这些劳工、奴隶一下子捅穿了,从此垮下去,一发不可收拾?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它的组织模式,也就是它推行的强制奴役。
曾有学者把社会组织分为三种“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形式,一曰“强制”(Coercive),二曰“计算”(Calculative),三曰“合作”(Cooperative)。在强制的组织模式里,人们工作的动力只有恐惧。而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就是他们知道惧怕也没有用了——按照秦朝的规定,自己已经必死无疑,不妨以不怕死的心态面对命运。
更重要的是,天下的陈胜、吴广还有成千上万。据说建秦陵时一度征用劳工达70万之众,加上修长城征用30万到40万人,还有其他开公路、挖水渠的浩大工程,想必当时全国的壮劳力已被征用得所剩无几。这些工程的残酷程度,从当时“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的民谣中,不难想见。
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力量,惧怕的效益有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它的曲线就会陡然下降。秦统治下,这个临界点就是陈胜、吴广的出现。这算得上是中国社会管理上的一个“潜规则”。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只会是一人奋起、天下响应,一处突破、全盘瓦解。这样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