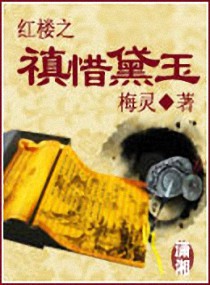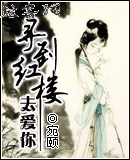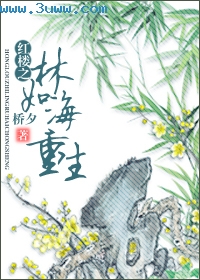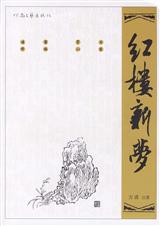读遍红楼-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实录其事”,不仅无人“命”雪芹删去,反说“此种文字亦不可少”。庚辰本眉批特加说明:
一部书中只有此一段丑极大露之文,写于贾琏身上,恰极当极。
又云:
看官熟思写珍琏辈当以何等文方恰也。
此段系书中情之瑕疵,写为阿凤生日“泼醋回”及“夭风流”宝玉悄看晴雯回作引,伏线千里外之笔也。
三段脂批,前为“已卯冬夜”,中为“壬午孟夏”,末为“丁亥夏”,均为畸笏所批。
前人说读《红楼梦》既贵心细尤贵眼明,我质愚才拙,只是注意到那多官的名与号颇有些弦外之音,寓有几分讽刺的味道。
多官,借以讽刺那个时代官多,官多必然是吃皇粮的人多,老百姓的负担就重,故古人说“官多则误国”。庚辰本在“名唤多官”四字下批道:“今是多多也,妙名。”说明作者取多为姓,以官为名,意在讽刺,非泛泛之笔。更令人惊奇的是在“都唤他作多浑虫”下面又批道:“更好。今之浑虫更多也。”如此一来,我们将多官的名与号合在一起就成了“官多浑虫”!
姓名字号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但在《红楼梦》一书中,姓名字号大多是作者精心之笔,即使小人物的名字号看似信手拈来,其实仔细推究内中也多寓有褒贬之意。这就是大作家的匠心独运之处——连一个小人物的名号也可以带给我们那个时代的某些“信息”。
翻开古今中外历史,官多易乱,官多为患的教训多不胜举。《红楼梦》以一个小人物的名号唤醒世人,可见曹雪芹之苦心——他告诫世人:
官多浑虫!
2005年12月17日
。。
寻根究底终存疑
——《不自弃文》非朱熹所作
读过《红楼梦》的人大都记得第56回薛宝钗和贾探春那段谈笑风生的“对讲学问”的故事。皇商小姐薛宝钗嘲笑了颇有政治家风度的贾府三小姐探春,说她“没有看见过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但是,曹雪芹很会卖关子,在这里并没有让宝姑娘说出这篇《不自弃文》载于何书,那个“朱夫子”是否就是鼎鼎大名的朱熹。结果害得红学家们考证了二百来年,也没有得出个子丑寅卯。然而,这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曾被一位研究者务考出来,断定《不自弃文》的
作者是朱熹。其根据是:(一)《佩文韵府·拾遗》“弃”字条下有“朱熹有《不自弃文》”一句,(二)清刻本《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的《庭训》中收有《不自弃文》。由此看来,似乎《不自弃文》作者朱熹说可以定论无疑了。其实不然。理由有三:
(一)《不自弃文》的思想、文风与朱熹思想、文风不一致。《不自弃文》主要是讲“天下之物”“有一节之可取且不为世之所弃”,即“天下无弃物”。如文中说:“顽如石而有攻玉之用,毒如蛇而有和药之需。粪其秽矣,施之发田则五谷赖之以秀实。灰既冷矣,俾之洗浣则衣裳赖之以精洁。食龟之肉,甲可遗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鹅之肉,毛可弃也,峒民缝之以御腊。推而举之,类而推之,则天下无弃物矣。”用贾探春的话说,就是“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很显然,这种“天下无弃物”的思想,同道学家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论”是不相容的。朱熹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在南宋王朝做官,晚年讲学。他的生活实践无法使他产生这种“下无弃物”的思想。《不自弃文》叙述生活中的许多具体的事物,内容充实,文字朴实易懂。而朱熹遗留下来的其它著作,都是一些抽象的、虚伪的道学教条,而他的文字枯燥无味,僵硬晦涩,与《不自弃文》的文风迥别。
(二)从南宋至清初,所有朱熹的文集、别集中都没有收入《不自弃文》篇,惟朱熹的第十六世孙朱玉编的《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收入此文。但是,清人曾经指出过,朱熹文集有真赝并存的现象,这一点是不该忽略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四《朱子全书》条内就说:“其记载杂出众手,编次亦不在一时,故或以私意润色,不免失真,或以臆说托名,全然无据。”我们查朱玉编的这部《朱子文集火全类编》中就有把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改题《家居要言》而编在《大全类编》的《庭训》类里,列在《不门弃文》之后。《家居要言》开头便是人们都熟悉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沽;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云云。文字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苦》全同。由此可以看出,朱玉编的《大全类编》中听收的文章实有“托名”之作,并非全是朱熹所著。
(三)如果上面的怀疑是有逆理的话,那么又如何解释《佩文韵府·拾遗》中“弃”字条下的注呢?对此,我们只要查一下《朱子艾集大全类编》和《佩文韵府·拾遗》的成书时间就清楚了。《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年),而《佩丈韵府·拾遗》则从康熙五十五年始编,至康熙五十九年王掞撰《拾遗序》方告竣。《大全类编》成书在前,《拾遗》成书在后,而朱熹文集、别集的其它版本又均无此文,故《拾遗》“弃”字条下。‘朱熹有《不自弃文》”之说可能来源于“大全类编”。假如《红楼梦》注释者将《不自弃文》作为注释条目的话,我主张指明其出自《大全类编》,而作者俘疑。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处理,可能更稳妥一些。
1974年3月25日
无为有处有还无
——“水月庵”在哪儿?
《红楼梦》第16回正文“谁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儿私逃进城”句上,甲戌本有眉批:“忽然接水月庵似大脱泄,及读至后方知紧收。此大段,有如歌急调迫之际,忽闻戛然檀板载(截)断,真见其大力量处,却便于写宝玉之文。”(庚辰本此条作侧批,文字略有出入。)第93回又写到水月庵,回目作“甄家仆投靠贾家门,水月庵掀翻风月案”。从《红楼梦》正文和脂评中可以看出,水月庵(别名馒头庵)是小说中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场所,因而“水月庵”颇为研究者所注意。
那末,小说中的水月庵究竟是作者虚拟呢,还是有所本?它的原型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呢?根据笔者目前已查到的材料存,至少有以下三处地方的水月庵(寺),可供进一步讨论。
(1)江苏长洲县的水月庵:叶燮《己畦文集》记载:“长洲县界东北有泽日著湖,湖旁有村日著村,有释氏之宫名水月庵,明成化问有拙愚上人创庵于此。”
(2)曹寅奏折中提及的水月庵:康熙五十年七月初四日,曹寅的奏折中况:“菩提子,织造局内所种四粒,已出一颗,枝杈叶色相同,惟叶下有刺,少异于众。万寿庵、水月庵两处所种,亦俱于六月内各出一颗,与扬州香阜寺所生无异。”
(3)北京有四处水月庵:据1926年7月商务印书馆编洋所编印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第八、十两编中记载,北京西单牌楼西南闹市口、宣武门内西城根太平湖东坡两地均有水月庵;东四牌楼北五条胡同路有水月寺一座。此外,今人苗培时在他的《慈禧外传》中还提到西直门内北小街有水月庵,庵中有老尼悟静。
曹雪芹童年时代是在江宁织造府度过的,他把记忆中的水月庵写入小说中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如果我们联系《红楼梦》中所提到的一些地名,如小说中有“鼓楼西大街”、“化枝巷”(西单北甘水桥附近、德胜门内三不老胡同)、“兴隆街”(崇文门外)、“天齐庙”(西城门外)、“天香楼” (什刹海旁)、“清虚观” (地安门外后海之北旧鼓楼大街)等等,对在北京写作《红楼梦》的曹雪芹来说,更具体,更直接一些。所以,我以为《红楼梦》中的水月庵同人们讨论的大观园一样,是艺术化了的地名,它的原型取之北京的几处水月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978年6月20日
txt小说上传分享
错改一字意不同
——汉南,还是“满南”?
《石头记》早期评本中的戚蓼生序本和蒙古王府本第41回回前都有一首七言律诗:
任呼牛马从来乐,随分清高方可安。
自古世情难意拟,淡妆浓抹有千般。
诗末署“立松轩”。
《红楼梦》版本研究者经过考订,认为脂评本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立松轩本”。友人郑庆山同志对此曾撰专文详加论列,这里就不再引述了。
最近,有牵拜读了庆山兄的新作《立松轩本总说》(载《北方论丛》1983年第1期),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立松轩修改、抄写和批评了《石头记》,他是一位可以和脂砚斋、畸笏嗖鼎立的并且是同一个时期的大批评家,可惜我们还没查到他的历史资料。“立”如果是他的姓氏,他就可能是满人(满人用汉姓)。戚序本将“汉南春历历”改作“满南春历历”,不知蒙府本是否如此。如果蒙府本也象戚本那样写着,当然就是立松轩的改笔,可为他是满人之一证。
读了庆山兄的大作后,我查阅了戚、宁、蒙、甲辰四个脂评抄本,结果戚宁蒙三个版本均作“满南春历历”,甲辰本则作“汉南春历历”。如果以庆山兄的判断,自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满南春历历”之“满”字,“是立松轩的改笔”;立松轩是“满人”。对此,我却有点不同看法,在这里同庆山兄商榷。
首先,研究过《红楼梦》版本韵同志都知道,传世的早期脂评本都是些过录本,其间由于抄工水平之优劣,文字讹舛衍夺是不胜枚举的。如所举“满南春历历”一例,庚辰、甲辰诸本均作“汉南春历历”,戚宁蒙本显系“汉”“满”两字形近而误,并非立松轩因自已是“满人”而将“汉南”改为“满南”,这道理是无需多说的。
其次,“汉南春历历”第五十二回薛宝琴所念,全诗是: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
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
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
其用“汉南”一典,语出北朝庾信《枯树赋》,诗圣杜甫就
有《柳边》诗云:“汉南应老尽。灞上远愁人”。如庆山兄所说立松轩“是一位可以和脂砚斋、畸笏叟鼎立的并且是同一个时期的大批评家”的话,立松轩怎么可能如此不通,仅仅因自己是“满人”而硬将一个熟典“汉南”改为无法解释的“满南”呢!?
如果以上两点看法尚有几分道理的话,我以为“立松轩”是满人用汉姓的说法也就值得再研究了。我甚至还疑心,“立松轩”三个字不过是从唐诗中借来的一个“署名”而已,他的真实姓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而“隐去”了。
1983年2月25日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字一句见精神
——“可怜见的”浅说
《红楼梦》第29回写贾母率领阖府子孙到清虚观打醮,一个小道士因剪灯花躲闪不及,撞到管家奶奶凤辣子怀里了,竟然被打了一通。王熙凤贾府众婆娘媳妇一阵吵嚷,惊动了老太君贾母,询问出了何事。于是下人们如实禀告缘由。
贾母听说,忙道:“快带了那孩子来,别唬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那里见的这个势派。倘或唬着他,倒怪可怜见的,他老子娘岂不疼的慌?”
接着下文又写道:
贾母命贾珍拉起来,叫他别怕。问他几岁了。那孩子通说不出话来。贾母还说“可怜见的”,又向贾珍道:“珍哥儿,带他去罢。给他些钱买果子吃,别叫人难为了他。”
曹雪芹在这一小节故事中,通过贾母之口,前后用了两个“可怜见的”,把这位史太君写得格外安详、慈爱。寥寥数笔刻画贾母形象,如见如闻,真不愧是大家手笔。
“可怜见的”,“怪可怜的”意思,向人乞怜之词,等千“可怜着”。陆澹安《小说词话汇释》中说,“《通俗编》):‘《元史·泰定帝纪》)即位诏,有薛特皇帝可怜见嫡孙等语。’元曲中亦常用之。《陈州粜米》四折白:‘大人可怜见!我不曾与他,我则当的几个烧饼吃哩。’”《元典章》,“博作怜,说至元时,勘属孔夫子…的田地,皇帝可怜见,分咐各处秀才每年那田地里出的钱粮修庙祭”;又说,“大德时,江淮百姓辫食,典卖孩儿们,皇帝可怜见,交官司收赎。”由上各例可知,“可怜见”一词为北方俗话,如今民间口语中。尚可听到。一句俗话,在曹雪芹笔下,竟画出了一位老太君的神情口气,可谓随手拈来无不妙!
1982年9月20日
青山掩幛碧纱厨
——“磐纱橱”考辨
《红楼梦》第3、7、26回,曾写到“碧纱橱”、“纱橱”,为使读者了解它的式样和用途,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通行本《红楼梦》中作了这样的注释:“碧纱橱——帏幛一类的东西。用木头做成架子,顶上和四周围蒙上碧纱,可以折叠。夏天张开摆在室内或园中,坐卧在里面,可避蚊蝇。”但有的研究者说:“这个注释是把碧纱橱说成床上的木架蚊幛了。这种解释要么是出于顾名思义,要么是把时间推得太远了,的确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写过‘纱橱’,那是她那一首著名的《醉花阴》:‘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接着,论者在引了黛玉进府时贾母关于安置住处的一段话后说:“黛玉进荣国府时值严冬,蚊蝇早已敛迹,蚊幛一类东西,大可以收进仓库里了。”那末,“碧纱橱”究竟应该如何注释呢?据有的研究者考证。“碧纱厨,正规的写法是‘碧纱橱’,它是清式建筑内檐装修中隔断的一种,亦称隔扇门、格门。”又据清代《装修作则例》,可写作“隔扇碧纱橱”。
论者对“碧纱橱”的考证不能说不对,但就其引证的材料来说,却不过是人文本《红楼梦》注释的一个补充。换句话说,人文本对“碧纱橱”的注释并没有错,至多是不全面而已。据笔者所见一些资料说明,即使在曹雪芹的时代,或者说《红楼梦》中所写的“碧纱橱”并非就一定指的“隔扇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