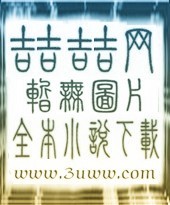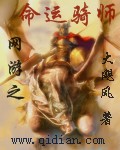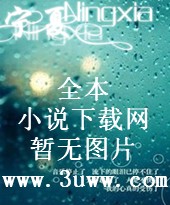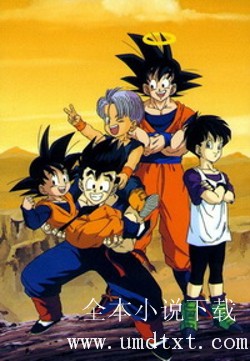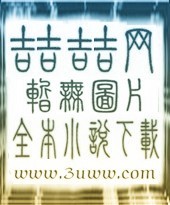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
康增进也 。
兼容并包之例二:“国粹”刘师培。
北京大学的教员中,刘师培也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人物。首先,在政治上“历史复杂”而有污点。他于188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1901年18岁时考中秀才,次年又考中举人,1903年进一步参加会试,未中。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撰写《中国民族志》、《攘书》,并和林懈合著《中国民约精义》等书,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担任《警钟日报》主笔,并成为以章太炎为思想领袖的光复会首批成员,自称“激烈派第一人”。《警钟日报》遭封禁前后,刘师培又参加“国学保存会”,是该会刊物《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他的学术著作大多发表于此报,被视为“国粹派”领袖人物之一。1907年2月,刘师培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时又接受日本社会党人影响,思想转向无政府主义,办“社会主义讲习所”,出《天义报》、《衡报》等刊物,宣传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08年,在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时期,刘师培变节,叛离同盟会,投入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幕下。辛亥革命以后,又投靠袁世凯,成为谋求袁世凯复辟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一员。1917年受聘于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门教授。1919年1月,《国故》月刊社成立,刘为总编辑,对抗新文化运动潮流。同年8月,病逝。
刘师培在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上,也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学者。他既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又是西方文化思想的积极传播者;既是国粹主义干将,又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先驱。1936年出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收录刘师培一生大部分著作。此书被学术界称为“真知灼见和胡言谬说杂陈”,“国粹中有西化,西化中散发着国粹气” 。如何认识这种表面看似互不相容而又容于一体的现象呢?
首先,要搞清楚刘师培等人提倡的国粹主义是什么?国粹主义出现于20世纪初,国粹派1905年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宣传“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所谓“国粹”,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经典、历史、文化、文字等特有的东西,就中国而言,主要是指孔子的儒学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不过国粹主义者把孔子视为学术派别,而不是宗教精神领袖,如刘师培所言:“自吾观之,孔子者,中国之学术家也,非中国之宗教家也” 。综观刘师培谈论国粹的文章,既涉及孔子儒学,也谈到《尚书》的“民也者,君之主也;君也者,民之役也”(民是君的主人,君是民的仆役) ,墨子的“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庄子》的“以君主为人民之仆役” 等思想。也可以说,他是披着古人的服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甚至鼓吹“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 的主张。然而既是披着古人的服装,也就自觉和不自觉的有着浓厚的封建主义气味。正因为如此,当五四运动彻底批判封建旧文化的革命思潮兴起时,特别是反对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极端倾向,如有人连汉字也要废弃,刘师培等人怒愤之中转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封建旧文化的辩护士、卫道者。
国粹主义者并不反对学习西方,他们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不少国粹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相当了解,并且是积极的宣传者。他们主张“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也就是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要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以我为主加以研究。刘师培的可贵之处在于,学习西方的同时,冷静地看到了西方的问题方面。如他指出:“人类至于今日,失平等之权者,实占社会之多数。贵之贱,富之于贫,强之于弱,无一日而非相凌,无一日而相役” 。刘师培看到了问题,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国粹主义毕竟是比资本主义落后的思想武器,不能有效的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正是在这种矛盾、惶惑之中,无政府主义拨响了他的心弦,使他倾心于无政府主义,努力鼓吹通过取消政府,而实现:“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 的理想社会。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4)
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和学术思想,采取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采取名曰“阶级分析”实为贴标签的办法,都不是值得提倡的。知识分子,虽然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政治主张等各有不同,但做为知识的载体,这一点是共同的。文化的因素,在决定知识分子命运方面,往往比其他诸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蔡元培正是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并没有对辜鸿铭、刘师培这样的学者采取排斥态度,或拒之门外,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效果上看,也是好的。1915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冯友兰回忆说:
“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在六人
之中,学术界有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
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
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
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
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
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
2、“兼容并包”不是只包新不包旧
对于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 至今仍然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种认为“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其主导方面是为了促进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而决不是为旧思想、旧文化保留地盘 ”,即 “保新不保旧”;另一种认为 “‘兼容并包’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即 “主观上保旧也保新,客观上保新”;还有一种认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能最精炼地概括北大的传统”,“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即“教育必须承认个人和尊重个人的价值,因而必须赋与师生不受限制的学术自由” ,即 “不受限制的宽容与自由”。
蔡元培自己又是如何认识和解说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呢?
他在《致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1919年3月18日)中说: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
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
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
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2月10日)又说: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
实派,计学(即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论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
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
则,以大学之所以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
所及,持一孔之论” 。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年1月1日)一文中进一步表示: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
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
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
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
的文学;那时侯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
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
白话文也好,用文言文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
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
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
。。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5)
蔡元培上述言论表明: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是只“包”一部分,也不是“保新不保旧”,而是既“包”新,也“包”旧,既“包”唯物,也“包”唯心,包括“任何学派”。二、“自由”与“容”,不是“不受限制的宽容与自由”,而是有条件的宽容与自由。条件是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是在社会发展中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不是早已被历史与社会淘汰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三、蔡元培在表达自己的态度时,用语是“容”(容纳、宽容)、“悉听”等中性词汇,而不是“允许”或“不允许”、“保护”或“不保护”等词汇。前者是客观的态度,后者是用行政权力干涉的作法。蔡元培同意前者,不赞成后者。“兼容并包”的要意在于:容纳各种学术观点,宽待各种学术流派,从而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兼容并包”的灵魂,是思想自由。
3、李大钊、陈独秀谈: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之必需
思想自由,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伏尔泰提出的重要口号。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自由就是只受法律支配”。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对“自由”做了重要补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 不在枷锁之中”,他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与民主”,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蒙昧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人类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革命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一方面指出这一口号包含的历史的阶级的具体内容,即“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另一译‘在知识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由、民主”思想所包含的普遍价值,提出他所理想的社会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列宁由于他所面临的敌人常用“自由和民主”攻击社会主义,为此,他对这两个口号较多的时候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但也指出:“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
思想自由的主张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遭到封建专制势力的极力反对,他们视自由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其次,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同的反映,有的要求极端自由,反对一切社会的约束;有的担心强调自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面对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对和舆论的众说纷纭,革命民主主义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坚持高举自由与民主的旗帜,猛烈的批判封建主义。特别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谈思想自由问题,如《宪法与思想自由》(1916年12月10日);《议会之言论》(1917年2月22日);《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1919年6月1日);《哪里还有自由》(1919年11月16日);《自由与秩序》(1921年1月15日)等,从人类生存的需要、历史的教训、社会的发展、强权与思想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其思想至今仍不失生命力。
李大钊认为,人类的生存需要多方面的 吸取营养,包括各种微量元素、杂质,甚至某些菌类。只吃一种东西,即使再好吃,再有营养,生命也不会得到健康发展,甚至有枯萎的危险。他曾转述一段近乎戏谑的话:孔子与牛肉,释迦与鸡肉,基督与虾,乃至穆罕默德与蟹,其为吾人之营养品等也。吾人食牛肉、鸡肉等,在使之变为我之肉也。吾人食孔子、释迦、基督、穆罕默德,亦欲使其精神性灵,代为我之精神性灵而已。但人类为杂食动物,吾人为求肉之发育,不能不兼食牛鸡虾蟹,正犹为求灵之发育,不能不兼收孔、释、耶、回之说。李大钊在这段引言之后评论道:“斯言虽近谑,亦颇含有至理。以今世国民灵的消化力(即思想力)之强,绝非孔、释、耶、回中之一家所能充其欲望者” 。世界的多样化,人类生存需要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千差万别的不同个性,都要求思想应该自由。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6)
李大钊认为,思想自由的主要内容是:“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他列举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指出,不许出版或实行文字狱,禁止不了思想的传播,如革命时代的巴黎,“攻击时政之小册,传布街巷,正如蝴蝶,非复禁令之所能遏制矣”,“各国关于出版,初行检阅之制,然检阅由于官吏一人之偏见,每多失当,最足为文化之蠹”。信仰自由,也是人类精神上的自然要求,“古来以政治之权力,强迫人民专信一宗,或对于异派加以压制者,其政策罔有不失败者”。中国的专制政体虽经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大学课堂上,既讲诸子百家之说,也讲医药卜巫之术,有助于冲破思想牢笼,发展国家文化 。李大钊写这篇文章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他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指出检查制度的缺陷等思想,还是具有警世作用。
如果说李大钊早期谈论思想自由的文章,还存有理性化倾向,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再谈思想自由问题,则更显示出现实的针对性和理论上的尖锐性。如他于1919年6月写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指出,即使是“异端邪说”,当民众还不认识时,强行禁止,只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