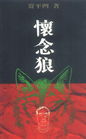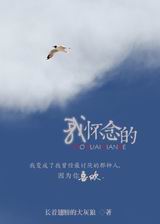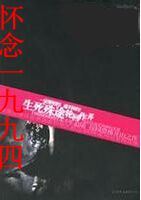怀念吴晗-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对我说,过去他对政治并不太关心,后来有些事情实在看不惯,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蒋介石国民党,压力就随之而来。他愤愤地说,他们愈不让我讲话,我就愈要讲,我的有些文章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吴先生是西南联大有名的进步教授,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加上目击时艰,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关怀祖国的前途,从争*、反*出发,逐渐靠近中国共产党,终于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这也是旧中国其他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共同经历的道路。
丁名楠 回忆吴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2)
1943年,我从历史系毕业了,对外国史、特别欧洲中古史很感兴趣,但苦于没有深造的机会,于是报考清华大学历史系作研究生。那时研究生的津贴实在少得可怜,连最简单的生活也难以维持。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介绍我去黄土坡中法中学兼课教地理,一面进修研究生的课程。这样生活是好了些,但失去的学习时间也不少。研究生修业期限一般为两年,我教了一年多的书,专业书读得不多,毕业论文连题目也没有定下来,心里很着急。一天遇见吴晗先生,他说:你搬进城来,回学校住吧。西南文献研究室刚成立,正需要人。那里报酬不多,但任务也不重,主要是搜集关于云南护国运动的资料,访问一些躬与其事的老人,笔录他们的讲话,不会占很多时间,可以安心读书。我同意到研究室工作。这个研究室设在北门街唐家花园内,唐继尧的墓就在那里,主人唐筱蓂是唐继尧的儿子。他特地为研究室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室内桌椅齐全,窗明几净,还陈列了几架古书。室外花木扶疏,群芳争妍,几株山茶树迎风招展,开花时鲜艳夺目,惹人喜爱。环境确是美极了。吴晗先生主持研究室,工作人员除我外,还有一位联大学生。研究室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全靠吴先生张罗,闻一多先生从刻字收入中,也资助过一些。闻先生还为我们刻了一颗“西南文献研究室”的精致图章。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访问了几位参加护国运动的当事人。他们年龄较大,但很热情。主要由于我们对云南地方历史很生疏,又缺乏可资参考的护国运动的资料书,既然自己没有研究,当然对被访者提不出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和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他们口述历史,有的海阔天空,不着边际,有的又过于繁琐。对他们提供的口头材料,我们无法核实,难以辨别真伪,工作进行得不顺利,心里感到不安。但吴晗先生并不介意,仍然鼓励我们继续搞下去。我到研究室工作后,发现有人夜间或星期日在研究室开会,起初不知道是什么人,后来才明白吴先生联系的*人士,常借研究室作为叙会的场所。原因是唐家当时在昆明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国民党特务对其有所顾忌,没有敢于轻举妄动,进行捣乱,在那里开会比较安全。因此西南文献研究室对昆明的民盟等*党派的活动起了某种掩护的作用。日本投降后,吴先生离开昆明,西南文献研究室也就不存在了。
吴晗先生去世时,年才60岁。他身体素来很壮健,工作热情又高,如果不是遭受*、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一定能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江青一伙尽管夺去了他的生命,但吴晗先生作为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的形象一直活在人们心里,那些残害他致死的恶魔将世世代代受到中国人民的唾骂而遗臭万年。
写于1983年9月21日(中秋)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 想看书来
李曦沐 追念吴晗先生(1)
吴晗先生是我们西南联大历史系的教授,在西南联大和昆明的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们敬爱的老师。我在西南联大学习四年,师生之谊最深的就是吴晗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主要不是在课业研修方面,而是在政治活动方面。今年是吴晗先生诞辰100周年,“*”中被*致死40周年。缅怀吴先生,不由得想起亲聆吴先生教诲和与吴先生接触交往的一些往事。
吴晗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明史专家。他在西南联大不仅讲授专史,还讲授全校各院系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我在1941年下学期入校读一年级的时候上的中国通史课就是吴先生讲授的。吴先生不仅向我们传授历史知识,还常常在讲课中联系现实,借古讽今,抨击当时国民党统治的*,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政治激情。给我们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在联大发生倒孔运动前的一堂课。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当时,包括联大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内的一批名人,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都无法及时撤离;而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却垄断中航公司的飞机抢运他的私人财物,甚至把他家的洋狗也运回重庆。重庆《大公报》于12月22日发表社论《拥护政治修明案》,透露了孔祥熙用飞机运洋狗之事,舆论大哗,吴晗先生对此十分气愤。他在给大一学生讲的中国通史课上尖锐地抨击此事,说中国古代有“蟋蟀相公”,现在又有“飞狗院长”,把孔祥熙和南宋的贾似道、南明的马士英这两个奸臣联系起来,更激起同学们的愤慨。1942年1月6日,联大住在昆华中学的一年级同学首先行动起来,发起示威*。他们走到新校舍校本部后,二、三、四年级的同学也参加进来,上千人一起走上街头。后来,住在拓东路的工学院同学也前来汇合,沿途又有云南大学和一些中学的同学加入,形成浩浩荡荡的队伍,高呼“打倒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在昆明的主要街道*了三四个小时。*后,全市各大中学校纷纷停课,联大、云大学生自治会都发表宣言,发出通电,声讨孔祥熙。在贵州的浙江大学和在四川的武汉大学的同学也积极起来响应。这就是当时在整个大后方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的“倒孔运动”。吴晗先生对这次运动的发动是投了一把火的。
吴先生进一步公开和同学走到一起的标志,是1944年5月3日晚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晚会。1941年皖南事变后,整个大后方笼罩着白色恐怖,昆明虽然好一些,但也在这个阴影之下,倒孔运动活跃了一阵以后又归于沉寂。1944年春,抗战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4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一个月内郑州、许昌、洛阳相继失守,继之湘北日军南侵岳阳,前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联大学生忧心如焚。在此之前,这年3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节”,以黄花岗起义的3月29日为青年节,也引起同学们的强烈不满。那时,我正被同学选举担任联大历史学会主席,同室好友、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马识途(在校时名为马千禾)找到我(在校时我名叫李晓),建议我们历史学会在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的时候举办一次时事晚会,并指名让我们请吴晗、闻一多、张奚若、周炳琳、沈有鼎等几位教授参加,发表讲演,当然还要请上我们的系主任雷海宗教授。按照老马的意见,我们提前几天贴出海报,宣告5月3日晚在联大最大的教室南区10号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晚会,欢迎同学参加。结果来的人出乎意外的踊跃,能容几百人的教室挤得满满的,连室外也站满了人,会议中途下大雨,听众也不肯离去。会议由我主持,请几位教授讲话。周炳琳、闻一多先生讲了自己亲身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张奚若先生把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了对比,说“五四”是一场思想革命,它的价值远在辛亥革命之上。吴晗先生以“五四”精神讲到当前青年的任务,提出要打破思想上文化上的束缚,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束缚。因为有的教授在发言中说学生的天职是读书,过问国家大事,不免幼稚,容易冲动,是国家的不幸。闻一多先生又起来痛加批驳,并表示自己愿意“里应外合”和同学们一起来摧毁毒害我们民族的封建思想。同学们也慷慨激昂地争相发言,表达了对时局的焦虑和对现状的不满。有的建议通电全国学生以实际行动争取*,有的要求政府确定“五四”为青年节,有的站在窗外的同学也把头伸进来大声疾呼。会场气氛之热烈,情绪之高昂,热情之高涨,为几年来所未见,一扫皖南事变后的沉闷气氛。这次晚会成为联大爱国*运动掀起新高潮的起点。吴晗、闻一多、张奚若等几位教授,也是在这次晚会上,在广大群众面前,亮出自己的战斗旗帜,从此不断地参加爱国*运动的群众*,可以说是无役不预。吴晗和闻一多两位先生更是参加了我们每一次示威*,成为和学生一起战斗最多、同学最信赖的老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李曦沐 追念吴晗先生(2)
吴晗先生不仅积极参加同学们的公开活动,他和昆明地下党和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也有密切的联系,并共同商讨运动中的问题。在校外,他同南方局派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同志以及楚图南、周新民、李文宜等老同志有联系,参加了他们发起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后又参加了*同盟。在联大校内,同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后与袁永熙有联系,和“民青”的联系更密切一些。当时“民青”有两个支部,第一支部同他联系的主要是洪季凯(后改名洪德铭);第二支部同他联系的主要是许寿谔(后改名许师谦)和我。我们都是历史系的学生。
在联大读四年级时要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导师就是吴晗先生。由于同吴晗先生在政治活动中接触较多,他知道我既在联大上课,又在中学教书,还有些政治和组织工作要做,时间很不充裕,所以对我很宽容,给予很多照顾。毕业以后,我受地下党派遣,去滇南*农村办小学,做群众工作,所以没有参加“一二?一”运动,直到死难四烈士出殡前才回到昆明,先后在天祥中学和云大附中教书,做地下党和“民青”的工作。这期间,和吴晗先生仍时有过从。下乡前和回昆后都曾去看望过他和闻一多先生。他们两家人住在同一院内的斜对门,志同道合,相濡以沫。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吴先生家的墙上挂着闻先生用篆体字给吴先生写的条幅,上联“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上款是“辰伯兄补壁”,下款署“一多”,生动地反映了两人的亲密关系。那时在昆明街头已经出现特务们的大字报,称吴晗先生为“吴晗诺夫”,称闻一多先生为“闻一多夫”,暗示他们是拿苏联卢布的红色分子,阴谋以此给加害他们制造借口。后来闻先生终于惨遭杀害,吴晗先生因为离昆较早才幸免于难。
联大于1946年“五四”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平津复校,联大师生分批北返。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同我谈话说东北解放了,我是东北人,要我回东北工作。于是我同联大最后一批北上的同学一起,于7月11日离开昆明。途经上海时,我去吴晗先生的弟弟吴春曦先生家看望了吴先生,他听说我要去东北,又知道我申请读清华研究生已获批准(联大有规定,四个学年各门课程的分数总平均超过85分的可申请入三校的研究院作研究生),就说要我留在清华,帮助他工作。我说自己在学校“已经红了”(即在政治上已经暴露了)不宜再待下去,他未再坚持,告诉我闫宝航先生正在上海,准备搭苏联船只去东北解放区,最好能与他同行。他介绍我去找了闫宝航先生,闫先生说什么时候走还不一定,于是我继续同联大复员同学一起到了北平。路过南京去*代表团转组织关系时,钱瑛同志要我到北平后,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找我方代表李秘书长。当时军调部国共双方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内外都有特务监视,根本无法与我方人员联系。这时我想到吴先生已到北平,一定会与我方人员有联系,于是找到他。他介绍我去找了刘清扬先生,经刘联系,徐冰同志接见了我,我才又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得到指示,去了东北。
北平解放时,我在旅大高级师范学校任校长,1949年春,到北京招聘教师,同时参加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会上见到了吴晗先生,他非常高兴地领我到北京饭店他的住处,在那里同一些名人同桌吃了一顿午餐。后又到清华园他的家里去看望他和夫人袁震先生,看到久病的袁先生已经康复,容光焕发,吴先生更是神采奕奕,感到解放在他们两位身上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直接效果,心中非常高兴。1950年年末,我调到旅大市委工作,不久吴晗先生到了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同志请他吃饭,要我这个学生给老师作陪。以后到北京开会,在北京饭店理发室又见到在那里理发的吴先生,我说常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说虽然忙,以后还要写下去。此后就没有再见到吴先生。
1966年年初,我到北京出差,帮助在京治病的*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同志办一点事。当时正在批判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欧阳钦同志这位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入党的老革命家很不以为然,和我说“这样批判,谁还敢研究历史?”这时,北京市委也曾派人来找我调查吴晗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情况,我就自己所知如实给他们写了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北京市委还是很想全面客观地了解吴晗先生的情况,希望能据此给予正确对待和处理的。后来,我在东北局被打倒,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打倒吴晗的门徒李曦沐”。在批斗我的大会上,专案组长在发言中说道:我们去北京找了吴晗,他正在扫地。我们问他认不认得李晓,他说:“认得,东北人,小个儿,很精神。”你们看,隔了这么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学生,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吴晗先生的消息。原以为劫后还可重逢,哪里知道,这位全心全意拥护党,奋不顾身地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最后参加了党的爱国学者、*斗士、忠诚党员,竟在罪恶滔天的“*”中成了祭旗最先倒下的牺牲者,连他多病的妻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