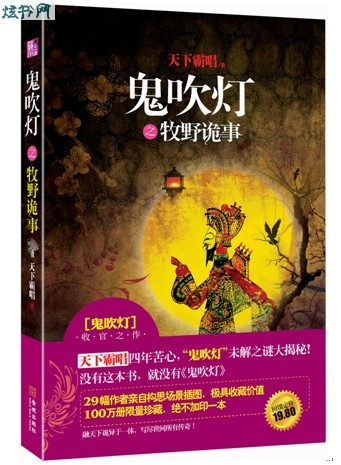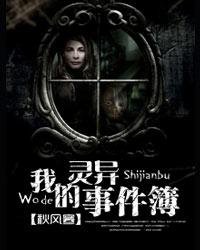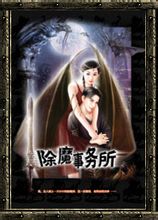二流堂纪事-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熊熊的火光,使他像孩子一样兴奋,他盯住通红的炉火,眼珠闪亮得像钻石喷射的光彩。我那时怎能体会到这晶莹如水晶的人,内心怎会有如此凄凉的况味。
在添取柴火时,我说:“可惜我们不会跳舞,否则,这火光,这情调该多么迷人。”说着,我把他一抱。我惊呆了。他也满面通红,嗫嚅地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
尘无,尘无! 你有五十斤或六十斤重么? 你怎能擎得起夏衍交给你的接力棒,你怎能挑得起生活给你的沉重的负担!五十年后,我看了他的“学生”盛里予所写的文章《轻尘》,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灵感。
虽则是短短的四五年间,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疾书。他写了多少,谁也无法统计,即使他活着,恐怕他自己也心中无数。
他把黄金年华献给党的革命文艺事业,而把《浮世杂拾》填补他自称为软弱的内心一角的自留地。
在尘无最后的日子,正是烽火漫天时候。病魔缠扰不已,小小的故乡海门容不下身轻如燕的一个小民,如今,这个人跃马挺枪,驰骋在辽阔的战场上,战功赫赫。何况两党又已合作抗日,他回去略事休憩,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一个雪珠纷飞的黄昏,朋友们送别尘无于苏州河畔,护送的是他的弟弟尘笠。面前一条长长的白带似的河水,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看着他的背影,刚理过的平头,清新隽逸,活脱一个小鲁迅(好友们平时对他的戏称),还是穿着一双陈嘉庚式帆布胶底鞋。一阵冷风吹来,一串不祥的联想搅乱思绪,大家看着他上船,看着小轮离岸,悄悄往回走。几双轻微的足音,在寂静的夜空中沙沙作响,各人默默走着,谁也不想说一句话,各人心中翻滚,有人眼眶里含着苦涩的泪。
尘无在《浮世杂拾》中写的寂寞的小街,冷落的荒园,漂泊的旅人,无依的少女,疾病、衰亡,秋风夜雨,夕阳烟柳晚晴天……这种情调不正是此刻各人的心境么!
此后,故人星散,家国沦丧,隔年就传来爱友、斗士尘无的噩耗。写至此,泣不能抑,是为传。
(去年返京,夏公孙女送我一本《王尘无电影评论集》,阅罢,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在我写此文前,周明君早已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报刊的浩瀚大海中艰苦游泳,寻尘无当年随意署名的遗作,这是多么艰巨的精神劳动,使他终于捞到了三十万字的巨大篇章。虽然这仅仅是尘无遗作的一部分,但也已经非常不易了。在周明君的文章中,我也知道了这位数十年前便辞世的老友,在“文革”中也难逃浩劫,孤坟被掘翻。这是什么缘故,据我的记忆,他从来没有惹过蓝苹,或者说,他的笔触不屑碰到蓝苹,他没有这种低级趣味。是不是他的名字时常和唐纳、和夏衍摆在一起惹了她?! 章泯曾因回答她“素不相识”而逃脱一死,早死的尘无竟无此幸运。
作为尘无最早的老友之一,我对周明君表示真挚的感谢。我已年老力衰,不知有否有心人愿为尘无在故乡立一小小纪念碑出力,让新知旧友为他树立一点永久的纪念。)
一九九五年九月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曲难忘(1)
——忆音乐家盛家伦
空庭飞着流萤,
高台走着狸猩,
人儿伴着孤灯,
梆儿敲着三更。
风凄凄,雨淋淋,
花乱落,叶飘零。
在这漫长的黑夜里,
谁同我等待着天明?
我形儿是鬼似的狰狞,
心儿是铁似的坚贞,
我只要一息尚存,
誓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啊,姑娘啊!
你是天上的月,
我是那月旁的寒星。
你是池中的水,
我是那水上的浮萍。
你是山上的树,
我是那树上的枯藤。
啊!姑娘啊,
只有你……
只有你……
…………
三十年代的上海西区,徐家汇三角地南边一片菜地,我出了家门,沿着菜圃的阡陌往前走百几十步路,便是新华影业公司的摄影场。那天,我有事要找吴永刚,和他通了电话,他说他这天不拍戏,想听听金山和胡萍演的《夜半歌声》中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主题歌的录音。我听他一说,就勾引起想听这歌声的念头。我急切地走着,离录音间还有一小段路,便已听到传来悠扬、委婉、凄厉、悲怆的歌声。
多么迷人的歌声!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是指此么? 当然不是。但对我来说,确是难忘的一曲,对家伦来说,这是他生平绝唱,一“曲”令人难忘。
三十年代的国产电影,有的连对话也请人代替,代唱则更多,金山在《夜半歌声》中的歌,便是由盛家伦代唱。
我有幸就在这一天认识了家伦。假如他卸下金丝眼镜,把西装换成古装,他就活脱像《西厢记》的张生、像梁山伯……
我在心里唱了一句:“美哉少年!”
“八一三”,日寇把侵略战火燃烧到了上海,我被分配到一个战地服务队。一年后,我到武汉,潘汉年、郭沫若把我安置到中国电影制片厂。我住在郊区一个私人别墅内,制片厂就在附近。别墅内有个小食堂,导演、明星们请了一个姓汪的厨师为他们烧饭。我时常在吃饭时听到明星们在谈:“家伦说汪师傅哪个菜做得很好”,“明天请汪师傅做那天给家伦烧的那个菜”。
从一些明星的口中,家伦好像一本菜谱,我想此人一定是个美食家。他在哪里呢? 我一打听,才知他已被派先出发到重庆去了。
我到重庆时,他早已开展一个时期的抗日宣传工作了。他利用制片厂摄制工作的间歇,把一些一时闲着的演员,组成了歌唱队,连活动布景一起,装在卡车上到各个热闹中心——大、小梁子及小什字等处唱抗战歌曲,有时在现场就对广大观众教唱。那时,在重庆运用歌唱对抗日宣传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在摄影厂内,家伦首创了用电影纪录抗战歌曲短片,在正片之前加演,教观众唱歌。这无疑也推动抗战歌曲的广泛流传,从而鼓舞了民众的抗战情绪和斗志。
家伦是那样热情地工作。但在那频繁的演出中,他却是从不参加演唱的。那是为爱护歌喉吗?似乎不是,他为新歌谱曲,他用口吹的哨子,比一支笛子还要显得高亢悦耳,而且他在作曲时,也以口笛代替钢琴。
我来到重庆已五六天了,仍是从明星姑娘口中在传诵着关于家伦的功德。真可以说是口碑载道。但又听到有些人怨他太严,太古板,太固执。
那天是星期一,是歌咏队的例行假日,我在食堂碰见家伦,他瞪大双眼注视我一阵,然后表示惊异、高兴、欢迎。
我那时是一个闲人,每周开一次会,参加讨论剧本,此外无所事事。我便时常跟摄影队出外景,随着歌咏队出发,沿途兴高采烈地东看看西看看,也想尽量帮着干活。
我发现了,由于工作的劳顿,家伦明显地消瘦了。我们约了四五个人联合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包饭,每月每人九元。这小馆的菜肴质量并不下于名菜馆,譬如我们的四菜一汤,那个汤基本上是全鸡全鸭,除一盖碗沱茶外,豆腐脑随便吃。家伦有时下厨直接点菜。
日寇侵略的烽火虽然胶着在贵州以东一带,但敌人想速战速决。于是,他们从诱降改变了策略,竟然用狂轰滥炸,企图逼降。
我那时在出版《救亡日报》航空版,小印刷所被炸毁了,香港的好友又力促我去另搞出版。家伦正好和应云卫导演的《塞上风云》摄影队同去塞北,既为影片作曲,也完成搜集民歌的愿望,我们便各自南北而分道扬镳了。
我到港后适我哥也来港,他与我友商妥叫我去仰光主持一家“公司”。于是我又转搭轮船赴越南转昆明飞到缅甸。我在临行前接到家伦的信,他已动身随《塞上风云》摄影队到塞北去了。
他们经过延安的时候,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也看到毛泽东和应云卫比赛吸烟,毛只吸三口,一支烟便燃烧到手指捏住的边沿,应云卫立刻认输……后来,听他们说起而传为佳话。
陕北边陲的榆林,那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邓宝珊,他是国民党开明的高级将领,和共产党是很友好的。当《塞上风云》摄影队到达榆林时,邓将军热情接待他们。因此他们拍摄外景的所有困难的问题,都很顺利地得到了帮助和解决。
一曲难忘(2)
邓宝珊从他的秘书那里知道这个摄影队,既是国民党军委会属下的单位,又是靠拢共产党的左翼艺术家。他想赠送他们一点零用钱,但是不能做得太直露,感到为难。还是他的副官足智多谋,他给他们安排了几桌麻将耍乐,在每个座位上都放上二十块银元,说明不论输赢都是各人的,只是借此助兴罢了。
不久当副官离开以后,家伦很诚恳地与大家商量,麻将照打,不管输赢,玩它一晚,打完把钱放回原位,主人对我们的招待已经非常丰盛了,我们应给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他们这样做法不仅使邓宝珊感到非常赞赏,也赢得了司令部里人们的尊重。同时邓将军对家伦通晓天文地理是很钦佩和赞赏的,因此,他每次因公到重庆,总要前往看望家伦,或者邀请他作客,欢聚畅谈一番。
家伦对婚姻问题总是抱着他自己固有的态度。有一次,某将军有一爱女,颇属意招家伦为东床佳婿,但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想方设法委婉地谢绝了。(我前年曾遇此小姐,她已与一位科学家教授结婚,几次想戏问她知否此事,但碍于在科学家面前不敢贸然启齿。)
家伦有三好:好吃,好看书,好议论天下事。在上海的时候,有位年轻的女事业家,对他狂热地单恋,约他参加舞会、看戏,甚至听音乐会,他都是一个“不”字。后来知道了诀窍,叫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只请他一个人。他来了,二话不说,举箸便吃,但只是蜻蜓点水似地吃了一下。吃毕,他开了口:“嗯,不错,营养够了。”拿起大衣,拜拜。后面一个娇嗲的声音追来:“家伦呀,家伦呀!”他很客气地加了两句:“再见,再见。”
夏衍老人套用波斯古国的国名大食,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大食国王”。这名称不太恰切,他是精食,再好的美馔,他是从不暴吃的。
虞静子有一次请家伦吃饭,她烧了一只鸡,大家都吃得很有味,他吃了一口,立刻吐出来:“死鸡。”那鸡果然是死后再加工的,这不免使大家感到惊讶和叹服。
家伦的家世大概有美食家的传统。他的曾祖父吃鸭子只吃鸭掌,即架起一块薄铁板,围住,把一群鸭子赶上去,铁板下烧火,鸭子在上面跳,血凝向脚下,然后斩下鸭脚,炖而食之。抗战胜利前一年,忽报他父亲在北碚去世,前此谁也不知他父亲住在重庆。他去办完丧事回来后,我问他是怎么死的,他说:“吃……。”突然感到暴露了“家秘”,不说下去,我也知道了。不久,发现特伟(漫画家、上海美影厂长)和盛舜也是他的叔叔,还有一个小婶婶,两个十几岁的小叔叔,还是一个小小的家族呢。
四川,真是名实相副的天府之国,八年抗战,大量的政府机关、商人、学生、文化界、难民等等争先恐后地蜂拥入川。前线吃紧,后方紧吃,物资丰富,永不匮乏。除土产外,军援的大铁罐牛油、克宁奶粉、SW咖啡也在市场上偷售。我买了几罐放在床底下。
重庆是举世闻名的三大火炉之一。“二流堂”有一间是男人集体睡通铺,像北方农村的长炕,可以睡八个人,家伦、沈剡等是基本睡户,吕恩的父亲来看她,也睡在这长铺上。我因房间让给方菁母女,也和他们同睡。因为天热,白天家伦便在铺边地下摊开一条竹席,躺着看书。那地方离开藏的牛油、奶粉、罐头太近,这些东西对他诱惑力太大,使得他不时伸手去抓一把往口里一塞,当然不包括咖啡粉。在香港,他也睡过靠床边的地板上看书,因为床底下有一箱苹果,看着书抓个苹果往嘴里一咬。有一次,用力太猛,把门牙嵌到苹果上去了。他也不修复,因为那只牙对吃并无大碍,只是他此后再也不吹口笛了。
谁也不知道家伦究竟读了多少书,就说“读万卷书”吧,但有人说,万卷恐怕也不止。你和他议论什么,他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对手都是当代的名学者:翦伯赞、侯外庐、乔冠华、胡风、陈白尘、沙梅等等,至于一遇上音乐家那更是他行内的话题了。
家伦在几经颠沛流离之后,在北京那个被叫做“二流堂”的楼上数百尺的房间里,堆积如山的书籍又有多少,更不要说他在抗战前的藏书了。那时他买、借、拿、看、偷的书都有。上海南京东路沙逊大厦楼下有一家洋人的大书店,他可以站在书架前看一整天,站得太累而觉得书又太可爱,爱不释手,他便把书带回家。当时有一说:“偷书不算贼”。有一回,他遇到一个书呆子、穷教员,胆子太小,不敢下手。在他怏怏走出书店大门时,家伦把他不敢下手的那册洋书塞在他手里,那人对神偷手的感激之情是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除了吃美食,议论天下大事,以及一些非常必要的事花时间之外,他所有时间都用在看书。重庆的夏天,就像蹲在大火炉旁,人们都找个阴凉的去处。一次他全身脱光仅留一条三角裤,靠在“炕”上看书,他似乎看得入迷了,有个女明星进来,他没有发觉。女明星坐在他身边,他还是不知道。女明星用手轻轻地在他的滑如凝脂、柔若无骨的胴体上抚摸着,他仍未感觉到,一直到读完一篇,他突然放下书,瞪着眼睛,全身登时白中带青从下往上直至脸上,倏地变成玫瑰色,同时用高亢的声音喝道:“干什么! 干什么! ”女明星一惊,花容失色,捂着脸抽噎着飞奔出门。
一曲难忘(3)
然而,家伦最出名的仍是美食家。这一方面出名也有好处,朋友们每逢有好吃的,其中必有此人。数不清有多少朋友喜欢这个人物,但也有人说他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