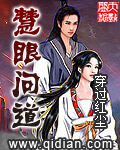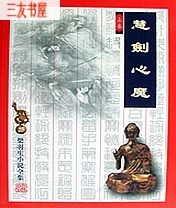生命的智慧-第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儿了呢?出在两个人的记忆上!日本人的记忆和舒先生的记忆出现了落差。而这两个记忆的问题,带给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在认识上的不同。
我想一定是写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觉言有未尽,特意又补上一段“附记”:
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你看,他并没有说他自己是老舍研究会的前会长,而是关西老舍研究会的一名委员)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又往前推了吧?孟姜女在春秋时候的那个原型在哪儿呢?
这些证据还没完,还有。而且这个证据只要一看,可能更愿意相信它的权威性。因为这个证据的说者是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当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先生。他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年龄已经很高了,大概80多岁了。他50年代在中国曾做过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刚才说到《明报月刊》刊登了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那篇文章,同期还刊登了马悦然的文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文中提到,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和他的妻子是我“当年的亲密知交。”你看他这样说。而我们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亲密知交,就像束星北谈到的那个“熟识”问题。文章还提到,由于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因为诺奖评委会有一个规定,一旦当了院士,成为评委,就要守口如瓶50年,直到档案揭秘。在此之前,任何一个评委都不能向外透露点滴。
。 想看书来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5)
“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 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我们看,一个后来的诺奖评委,在他回忆1966年情形的时候,又是这样的一种记忆。
然而,他在文章中透露,因为“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使他“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1988年沈从文先生去世之后——当时国内也一片惋惜——这个人因为理解中国人的诺奖情结,所以他违背诺奖评委的诺言,就1988年的事情做了一个披露。我们注意他言辞的表达,他说,“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可能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他并没有把话说死。因为每年的诺奖要在锅盖揭开以后才能知道那个人是谁,评奖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然后在这儿,我们再看另一个有趣的现象。马悦然的文章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也就是她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件事相吻合。我到现在,唯一没有找到的,估计也不可能找到的,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但是,我从常识性的外交礼仪来推断,瑞典大使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可能不会那么说。大家想一想,瑞典驻日本大使有可能在向日本人祝贺日本作家获得诺奖的时候向日本人说,这个奖原来不是给你的,是要给一个中国伟大作家老舍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他如果这么说,是否违反了外交礼仪?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违反外交礼仪的言辞是真实的,那前面的那个叙述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我找不找这个瑞典大使也就无所谓了。
然后,再来看那个马悦然。他说他是老舍夫妇的“亲密知交”。然而,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时,发现了一封时间标明写于1956年至1957年间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英文短信,只有一句话:“‘I am not Cao Yu;I am Lao 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的意思‘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意思是,我不多说了,你们找错了人。就这么简单。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多亏有舒济女士的注释,就能明白这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注释说,“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疑问是不是又可以出来了?如果马悦然和老舍夫妇是亲密知交的话,他难道不知道住在那个胡同里的是老舍而不是曹禺?这个历史也就非常有意思了,对吧?
最后剩一点儿时间,来不及梳理很多,就引两个西方有名史学家的话来结束,并让我们多元地来认识历史。一个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另一位还在世的是美国史学家保罗·柯文。看看他们的话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更遥远的、更幽深的一种思考。
保罗·柯文有几段很精彩的话。他研究义和团,跟我们国内某一时期对义和团的研究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也说到了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对义和团的研究及由此得出的结论,跟我们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有关系的。正因为如此,他强调,有时候我们并不在乎过去发生了什么,而只在乎怎样以今天对过去那件事情的认知,往过去的那件事情上附加。而了解这件事情的人,往往又是从已经附加的东西去了解。我们已经不知道原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一直认为,“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固定不变的事实材料,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去发掘并清楚地说明这些材料。从我做“老舍之死”的调查工作来说,其实也是这么一种过程。他还提到了两个这样的疑问,并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我们能不能认为被亲身体验的“过去”,比历史上重建了的“过去”更有价值,因为它更加逼真;或者认为,历史上重建了的“过去”,比被神话了的“过去”更有价值,因为它更加接近事实?
对于这两个,保罗·柯文毫不犹豫地做了肯定的回答。不论是前边我说的那么多的具体例子,还是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繁复、复杂、多元的“老舍之死”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口述史上,它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多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之间,有“共存、互扰、矛盾”;不同的声部之间也常有“遮掩覆盖”;也许还有人试图将自己的声音作为独唱,而将历史简单画上句号。这几种情况我们都碰到过,以上我们看过的那些事例当中,共存、互扰都有,彼此不承认;不同的声部都要存在,因为我们要听到不同的声部。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6)
然而,有的时候常常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声部被故意地遮掩覆盖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去想一想。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听独唱。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曾为此迷惑不解。我在采访“老舍之死”之初,是想按着古希腊的史学家对于“历史要追求真相”的那种认识来做的,而且觉得也能做到。有什么难的,只要找到当事人、亲历者、见证人一问,他们不会骗我,跟我一说就行了。结果看来不是这样的。我越来越被带入了历史的困惑当中。但逐渐地通过梳理历史,我的思路清晰起来了,不再困惑了。现在的重要性已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历史的细节真实还原,已不在乎这些人所说到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他们都是不同的声部。而这种“罗生门”式的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至少一种意义所在。
这种认识我是得益于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特别厚的一本书,读起来特别枯燥,要很艰难地啃下来,却受益匪浅。它是对大量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结果,这些文献资料来自于近代开始时期的那些情况不明的年代里,广阔的地中海舞台的每个角落。它写的太详尽了,都是史料,都是资料,完全符合史家的规范;但是没有用文学的笔法写,所以很枯燥。它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写。他认为写史的目的:“在于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在于提出它们的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我现在就要努力这么做。我在这之前所讲,就是要把这些深广丰富的内容提供给大家。他说:“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一个声部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排斥另一个声部、另一个伴奏,不让另一个存在。
不过,没有掠美之意,我与布罗代尔感到了同样的困惑,那就是“怎样才能在同一个时间内像通过一个透明层那样,看见被现实重叠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呢?”容易吗?不容易。太难了!通过追溯春秋的孟姜女那几个原型,来看重叠的那些层,如何能把它看得透明呢?我们看布罗代尔是怎么做的,他是“把某些语句和某些解释当作一再出现在本书的三个部分里的主旋律和这三个部分的共同的、熟悉的曲调来使用。我试着用这种方法来给人一个关于上述情况的印象”。我也是试图在历史的叙述中将各种不同的声部保存和呈现出来。我的两本“老舍之死”口述史,就是这样来呈现不同的声部的。
布罗代尔说,“但是,困难在于:不是只有两种或者三种对时间的计量,而是有几十种对时间的计量。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又牵连、包含某种特殊的历史……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历史”。这样能做到吗?布罗代尔是乐观的,他以为将来有可能会做到。而我悲观地以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掌声)
[讲演时间:2006年8月13日;录音整理:裴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