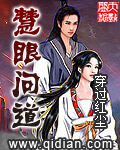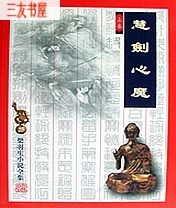生命的智慧-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我看见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方案,这个方案专门把每个区的人口密度都标出来了。一看,好家伙!前门大栅栏,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都已经四万多人了,这四万多人好不好?人口密度高好不好?
如果人口密度高,大家还愿意在这个地方呆着,就自有它的道理。这个地方肯定是水草丰美,有机会啊,有就业啊,能挣到钱啊,才能养活那么多人啊。
你可能会说那会儿北京人的住宅标准太低了,所以人口密度才这么高。但你以为他们心甘情愿被挤着呀?为什么遭这种“罪”他们还不离开呢?因为他们在这里能活下去啊。
如果人口密度与城市的繁荣是正比关系,就是一件好事情,不应简单地去套那个人均住宅标准,这样去套,完全是因果倒置。
四合院多为单层的庭院式住宅,由它组成的城市为什么能装这么多人?
你想想,一条六七百米长的胡同,一看就是一堵墙,它是院挨院建起来的,能趴房子的地方全趴满了,这个密度其实是很大的。
我和一位规划师谈这个现象,他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小区设计标准,建造塔楼小区,消防要考虑,遮阳要考虑,每平方公里能装上一万五千人就不错了,而且还有不少土地被浪费掉了,那里可能永远不会有一双脚踩上去。再看北京老城,所有能用的土地几乎都用起来了。而且,院子里都有空,都有树。
所以,我特别想把国际城市规划界这两派争论的学者召到北京开个会,劝他们不要争了,因为北京就能给出答案,这个古城既有密度,又能给你一个后花园,既是城市,又有郊野之气。这是13世纪中国人的智慧,是可以骄傲的遗产,它居然回答了当今人类城市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以这样的规划而建造的古城,在今天仍是合用的,只要我们采取一个与之配套的、正确的交通政策,在胡同两边的大街安排像波哥大那样的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就能够成功。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8)
我们从几百米长的胡同里走出来,有什么不可以?这个过程还会产生许多故事,也许那个小伙子和小姑娘就认识了。走到胡同口,公交车就在那里,四通八达,快速准时,大家就不用开车了,这是多好的生活方式啊。
所以,如此伟大的城市规划遗产完全可以在今天得以利用,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这样的价值,那就是数典忘祖了。如此巨大的精神与物质遗产,如果没有人能理解它,看懂它,这是多大的悲哀啊。事实上,这种规划理念在我们今天依然是有生命力的,是值得传承的。你看,北美那些好的城市,都是方格子棋盘式的道路,跟北京古城惊人地相似。
美国一位女记者写了一本书,说高密度的方格子道路好在哪儿呢?她说,在这样的路网里,她的孩子遇到坏蛋的时候,撒腿一跑,一拐弯,坏蛋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要是她的孩子在北京的二环路上被坏人追,就完蛋了,那里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老说北京的四合院都成危房了,所以要拆掉。(大屏幕)这是我从钟楼往东北方向拍的照片,北京的危房现在确实是个大问题。
有人对我说,王军,你干吗不去住啊?你老说要保护北京城,那些破房子你怎么不进去住啊?
我对他说,告诉你我的答案,第一,我当然不愿进去住。
他就哈哈大笑,你瞧你也不愿意嘛。
我说,第二,希望你换个角度来想,如果你是这个房屋的产权人,你怎么看?
他说,产权人?这些四合院还有产权吗?
我说,告诉你,它们有着新中国宪法保护的产权。北京市1949年成立的公逆产清管局,接收的是旧政府的公产,没收的是“反革命”的房产。清管完成后,1953年对私房发放了房地产所有权证,宪法是保护它们的权利的。当年,北京市发了证的私房将近旧城及关厢地区房屋间数的百分之七十。
我又问他,你买了房没有?
他说买了。
我说,好啊,这样吧,哪一天突然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你们家住进一批人,厨房住着老张家,客厅住着老李家,我王军作为市长到你们家深入调研,一看老百姓住得那么惨,就下令:拆掉!你同意么?
他傻了。
我说,北京的房子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发生了大量这样的问题,这些是历史遗留问题,依照宪法是应该得到解决的。
现在许多人都买了房,据建设部2003年统计,中国城镇房屋都是私有或自有的了,新老私房主都在同一个法律环境的庇护之下,谁不舒服,其他人都不会感到舒服。
事实上,有一些买了楼房的人,也遭遇了被强拆的情况。有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王军,我这房子能装修么?那是80年代的楼房,他还问我能不能装修,就是怕被拆啊,因为老四合院被拆完了,就要去拆老楼房了,虽然我的朋友已购得了产权,但他仍没有安全感。
四合院之所以危破了,就是因为被搞得谁也不敢买,谁也不敢修了,我买了、修了之后,被拆了怎么办?况且人家占了我们家房子,到现在还没有搬出去呢。
有一次开会,区政府的一些干部说老百姓强烈要求拆迁、强烈要求危改。我就对他们说,第一,是哪些人强烈要求拆迁和危改?按照北京市现在的拆迁政策,你要回迁,平均每户要交十五到十八万元,你交得起么?他们都是穷人啊!你不回迁,拿钱走人,平均每户能拿十到十五万元,这能在北京安居吗?政府说,你可以贷款,但他们多是低收入者,能逼迫他们这辈子不吃不喝把命都搭给银行吗?
我说,在这样的政策下,到底是谁在强烈要求拆迁呢?据我调查了解,恰恰是那些非产权住户,他们在外面拥有第二套住宅之后,对拆迁往往抱有强烈愿望,因为一拆,就能把不属于自己的房产变现为补偿款收入私囊了。危房改造岂能只满足这些人的利益?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旧城内的危房率仅为,房屋基本保持健康,为什么在后来的经济发展时期,城市的细胞——住宅烂掉了呢?而在以前,哪个皇帝抓过危旧房改造呢?没有啊!都靠老百姓自己修,不用政府掏钱。
曾经有一次政府想掏钱,但没有成功,就是清朝初期的时候,清兵入关,把内城的房屋全部圈占,把汉人赶到外城去住。圈占的房屋都成了公房,叫旗房,以分配的方式分给旗人住,但到后来,扛来扛去扛到乾隆皇帝那会儿就扛不下去了,盖房子修房子对政府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旗人又发生了分化,有的人必须靠典当房子生活,政府一打击,他就没法过日子了。怎么办?乾隆皇帝就把它“房改”了,向个人出售了,这样,每家每户就自己修缮了,当时规定房屋买卖只能在旗内进行。到咸丰皇帝那会儿,旗内外都可以买卖了,好比“央产房”上市,也走了这么一遭。
所以,应该通过确保住宅权利的稳定以及市场交易的公正来保持城市房屋的健康,我们中国有个词叫“源远流长”。什么是“源”?这个城市生命的“源”在哪里?就是它的细胞是要有生命力的。细胞的生命力在哪里?就是它的财产权必须是稳定的。只有这样,房主人才敢真金白银地去修他的房子,这个细胞才会有活力。“流”是什么?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市场,你要我王军的房子,我们得谈判吧,你不能拿推土机来吓唬我吧?只有这样,市场才会建立对房屋产权的信心,它们才会有交易价值,才会“流水不腐”。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9)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靠老百姓自我修缮,靠市场自由交易,无需国家财政支持就能够使城市的房屋基本保持健康。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剥夺或挤占受新中国宪法保护的私有房屋的情况,而且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所以,应该落实宪法,将这些房屋完全还给合法的产权人,保障他们的权利。这样,大量的大杂院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另外,对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应该建立产权交易的谈判程序,严禁行政强制力介入。这样,老百姓对自己的家就有信心了,就敢修自己的房子了。
这样,政府只需明确四合院和胡同的修缮标准,因地制宜地改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便可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实现街区及旧城的复兴,从而根本摒弃那种成片拆除的错误做法。
今天我主要就是想谈谈以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城市规划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第二,我特别想强调,交通政策和城市形态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三,如何认识北京古城,如何评价元大都的规划。最后,危房问题应该怎么看待,怎么解决。
好,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剩下的时间我全包了。王军的《城记》不仅仅是一部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变迁的历史记录,在这份历史记录的背后,有更多的内容是需要我们细细品味和体悟的。我挑出来三段,再给大家念念,看听后会有什么感悟。
第一段:“1951年8月15日,梁思成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能够‘在百忙中分出一点时间给我们或中央有关部门作一个特殊的指示,以便适当地修正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但很快,大规模的建设迫在眉睫。“梁思成陷入了复杂的心境,后来他甚至称毛泽东不懂建筑。”据原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口述回忆:“梁思成说:毛主席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但他不懂建筑,是不能领导建筑的。针对此说,彭真讲:我们开始也是觉得自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可是后来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照你所说,毛主席在军事上也不能说是内行,他不会开坦克,也当不了士兵。比如,梅兰芳他也只能唱青衣,他就唱不了花脸。可是他就可以当戏剧学院的院长。一个人不可能行行都会,但他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人。”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执政者说的话。
再看第二段,作为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吴晗怎么说:1953年5月,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简报称:“女三中门前发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为帝王庙牌楼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楼的戗柱和夹杆石多次被撞,牌楼有危险。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过陡,又有牌楼阻碍交通,亦属事故多发点。”于是,5月4日,北京市委就向中央提出一个拆除方案。5月9日中央批了,并指出为取得人民的拥护,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我们来看王军的描述:“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重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这都是我们这些在场作记录的同志耳闻目睹的事实。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那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感慨道,推土机一开动,我们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了。林徽因则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真情。’”若把此处的描写与吴晗在“文革”中的遭遇联系起来看,我们会怎么想?
再看第三段: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召集各方面人士1800多位,足足讲了4个钟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成《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向“三大主义”,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宣战。
5月1日,毛泽东征求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10)
这位在北平围城之时,带解放军干部请梁思成绘文物地图的政治学家,从1952年起担任了7年###部长。1956年,在一次学习会上,他就放了一炮:“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再往下念了。至少我从王军的这三段描述中感到了更多文字背后的东西,它已经超出了王军的这本书本身。
上个月,我和邓友梅、从维熙两位前辈应邀到苏州沧浪区做文化考察。没想到,现在的苏州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梁思成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理念,即“安居乐业”变成了现实,它以科学的以“文化立区”的“沧浪”模式出现在我的眼前。苏州的整体城市建设规划与发展亦然,“老苏州”、“新苏州”和“洋苏州”构成了一个崭新的三位一体的大苏州。
我和王军一样,也落下病了。我在苏州,又不由得想起了为老北京的建筑、规划伤心不已的梁思成,想到有多少热爱老北京,把祖宗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