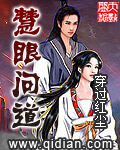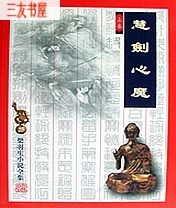生命的智慧-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41岁,亲身见证了大清的繁荣昌盛,引得龙颜大悦,乾隆当即为他出了个上联;“花甲重逢,更添三七岁月”,纪晓岚跟着出了个下联“古稀双庆,又加一度春秋”。扯得有点远了。毛泽东如果从遵义会议算起,也有41年,如果从建国算起,27年。执政时间不是最长的,但我们比的是诗词啊。
有史料可查的,帝王级的人物的著名诗文,最早的有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有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但都只有孤篇传世,而且到底出自何人手笔也不可考。然后就是刘彻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还有那个魏武帝曹操,是个准帝王,前面已经说过了。然后就是一代词宗李后主,婉约派的大师,我觉得客观地说,就婉约风格而言,毛泽东是写不过李煜的。毛的《虞美人·枕上》明显受了李煜的影响。另有个宋徽宗,开创了“瘦金体”,可以说在书法上和毛打个平手,但人家宋徽宗画画得好啊,你们去看看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里的《听琴图》、《芙蓉锦鸡图》,都堪称经典。他的工笔人物、工笔花鸟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地位的,达到了大师级水平。但他的诗词不如毛泽东。李煜和赵佶可以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有艺术才华的两个人,赵比李略输文才,李比赵稍逊丹青。1100年,南唐李后主为宋太祖赵匡胤所俘,时隔不久,郁郁而终。200多年后,宋神宗仰慕李煜才华,在生赵佶之前,专门观赏李煜诗画,当夜梦见李煜来见……这个坊间传说意指宋徽宗乃李后主的转世投胎。这真是一对冤家孽子,有浪漫轻佻的才子情,无经天纬地的君王才。李、赵之后,附庸风雅、舞文弄墨的虽然不少,什么朱元璋、康、雍、乾,但基本都不入流。跟毛不是一个档次。李、赵虽然在单项上比毛胜出,但是有个根本的不可比性,就是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没有做好本职工作,都是亡国之君。所以综合比较,毛是冠军。这是一个比法。
还有一个比法,不跟皇帝比了,比比大诗人怎么样。就和李白比一首词,《忆秦娥》。据考证,《忆秦娥》词牌为李白所创,原词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是一首好词,尤其最后八个字为王国维所激赏,认为“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说的是不错。
我们再看看毛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显而易见,毛词夺胎于李词,韵脚一样,风格迥异,一为高古悲慨,一为豪迈沉雄。毛词最妙处也在后面八个字,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他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23)
如果大家有傍晚登高望远的经验,看群山如浪奔来,在夕阳的晖映下由黛青到钢蓝到绯红再到血红,景象何其壮观。然后再由此想到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血战无数,血染山河,从江西到遵义,雄关如铁,都已迈过,但“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即便如此,也还要杀出一条血路,勇往直前。情景交融,衬托出了这首词的格调之悲凉,气韵之慷慨,意境之阔大,画面之壮美,色彩之艳丽,它的情感、力度,我认为比李白有过之。不是说毛泽东的诗歌才华超过李白,而是毛的战争生命体验为李白所未有。这就造成他们的重要区别,李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发思古之幽情,而毛泽东是一个亲历战争的统帅,以笔蘸血,用生命在写诗。这也是他和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骚人墨客的最大区别。我们不能总体上说毛泽东的诗词达到了李白的水平,但就说这一首,尤其是这个结尾,是超过李白的。
这也是一种比较,我们点到为止。
前面说了纵比,下面我们来说横比。就是把毛和他同时代人、同事、同僚作比较。我党我军的元戎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周恩来等都有诗词传世,而且多数人的创作量都远远超过毛泽东。也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比如周恩来的“大江歌罢棹头东,遂秘群科济世穷,十年面壁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朱德的“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叶剑英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更有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而毛的诗词就创作量而言不能算高产,目前胡乔木主编的权威版本和海外刘济昆的所谓全编都不过六十余首,我现在搜集到的约近100首,恐怕这就是全部了。但论艺术成就,毛诗比他的那些同志们恐怕要高出不止一个档次。至于书法,就更没有可比性了。
恰恰他们又非常具有可比性,一是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年龄相仿,文化背景相同。而且要说青少年时期读书的环境,这些人多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学习条件都胜过毛泽东。二是他们青年投身革命,斗争经历和毛泽东相仿,区别只在于毛是第一责任人,力挽狂澜也罢,日理万机也罢,主要的功绩都归于毛泽东,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大家的业余爱好都是诗词和书法,数十年不辍,临了一比,高下立现,不服不行啊!
所以,晚年毛泽东虽然犯了文革等重大错误,但并没有减损多少他的个人魅力。不少在文革中遭到冲击迫害甚至妻离子散的人物,时过境迁之后,不光没有怨恨之情,甚至仍然对他充满了崇敬和缅怀。最典型的是罗瑞卿,七年身陷囹圄,双腿残疾,1976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悲痛不已,坐着轮椅冲破阻力,参加了毛的追悼大会,并拄着拐杖以惊人的毅力站立了一个多小时,表达了他对毛泽东最后的忠诚和景仰。(56)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诗词为表征的巨大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一种势能,转化成了他多方面的优势,使他总是胜出一筹,先声夺人,以至于他有意无意地把这种优势作为一种武器和谋略。这一点在他的晚年体现得尤为充分,比如讲话总是把一些生僻典故信手拈来,而且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使人一头雾水,即便是历史学家,也常常需要经过考证,才能找到出处、原意,然后再来揣度毛的本意和动机,造成一种“从来天意高难问”的玄妙感。从而使人们仰之弥高,惧之日甚。
五、五个来源
前面我们讲了毛泽东诗词的高蹈和精妙,讲了以诗词为表征的毛泽东文化底蕴的深邃和博大,那么其文脉何来?下面,我尝试着从五个方面对此再作一探源。
第一,源自毛泽东的天赋个性。
前面我们在第三部分讲毛艺术风格的第一个特点“豪放大气”时,举了毛16岁的《咏蛙》诗为例,说明了他的霸气。这是与生俱来的,现在又有资料披露了毛更早的诗作,他13岁写的《井赞》: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57)
表明他渴望挑战艰险,搏击风浪的人生信条,他的远大志向从小就异乎常人,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些诗作今天其实都不可考,是否真正出自毛的手笔,大有疑问。但这并不重要,人们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为这些诗作和出自青年毛泽东手笔的《沁园春·长沙》和《湘江评论·发刊词》等诗文中的磅礴大气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这就是天赋个性。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多有论述,这里点到为止,而且,毛泽东的性格极富挑战性和斗争性,愈挫愈奋,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斗争和创作生涯中。这就要说到下一个问题。
第二、源自毛泽东的斗争实践。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就是毛自己的创作体会,他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相互发明、相互应证。首先是毛壮丽奇伟的一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绚烂奇谲的源泉,这一点,我在前面多有阐述,此处从略。其次,纵观毛60年的创作生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从量和质两方面来看,都大致可以说,他的创作,中青年时期胜于老年时期,建国前胜于建国后,战争年代胜于和平年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来作一个简单分析。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24)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在两首《沁园春》之间,即1923年到1936年约13年期间。而这十几年,是毛个人和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可以说,内忧外患,凶险莫测,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创作的条件和环境更加无从谈起。但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此中表现出来,巨大的压力带来巨大的反弹,毛的诗情空前迸发,前后写下了《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等经典之作。尤其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写出了《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等华彩篇章。相反,在延安十几年相对平和安定的环境中,毛反而诗情淡然,诗作甚少,除一首《沁园春·雪》之外,乏善可陈。
这种现象,毛泽东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1949年12月中旬,在迎接毛泽东访苏的专列上,苏联汉学家、翻译费德林当面向毛表达他对毛在长征途中所写诗词的赞叹时,毛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58)其实,如前所述,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使然。同时,也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文章憎命达”,“写忧而造诣”嘛。
第三,源自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我说的屈原代表的就是两千多年前的楚文化,所谓“吴头楚尾”,其风格就是比较瑰丽,浪漫,奇异,神秘,举一个时髦的音乐人的例子,那就是谭盾。现在谭盾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华人作曲家,大家可能听过他的电影音乐《卧虎藏龙》,交响乐《水》、《地图》,你可能记不住它的旋律,但那种神秘诡异可能让你挥之不去。但这也恰恰是打动和征服西方听众的要害所在。有一次,我在我们学院音乐系给研究生讲课,问到他们谭盾的音乐素材来自哪里,他们都摇头,我告诉他们,就是来自湖南湘西,来自湘西乡间古老的祭祀音乐,说穿了,就是两千多年前“吴头楚尾”文化的流风遗韵。青年谭盾曾插队湘西农村劳动,那种音乐浸透了他的灵魂,成为了他在异国他乡的音乐灵感和创作源泉。在今天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赞成鲁迅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还要再加一句,“越是古老的,越是现代的”,谭盾现在不就成了西方人所追捧的先锋作曲家吗?其实他不过是用西方的乐器和现代作曲技巧演绎和诠释了中国湘西最古老的音乐遗存。
当然,楚文化的代表首推屈原。在《离骚》、《九歌》、《九章》中所包含的想象浪漫的气质,文字华美的修辞,忧国忧民的情怀都为毛泽东所心仪和推崇,使屈原成为毛终身挚爱不渝的作家。他们二人之间的精神连接和承传,大家可以在毛泽东诗词中细细品味,如毛泽东在坐地巡天的艺术遨游,帝子乘风嫦娥起舞的瑰丽想象,倚天拔剑裁取昆仑的雄伟气魄,都颇得《离骚》、《九歌》之神韵。我这里再提供几个毛喜欢屈原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1)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特别喜欢屈原作品,如他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笔记《讲堂录》,共计47页,前11页就是手抄的《离骚》、《九歌》全文,还写有《离骚》的内容提要。到了建国以后,更是经常读《楚辞》,1957年专门搜集了《楚辞》的各种版本多达50 多种。不仅仅是读了,而是喜欢到把它当作一种藏品了。
(2)1958年1月13日的凌晨,毛给江青写了个便条,“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悟,心中喜悦。”时年,他已经65岁了,这天晚上睡觉前又重读了一遍《离骚》,而且读完又有所意会,有新的收获。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读《离骚》读几十年,读成百上千遍,叫做温故而知新,有了一点新的领悟,还特别高兴地与江青分享,可见其愉悦之情。(59)
(3)1961年秋,毛专门为屈原赋七绝一首: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60)
大家可以查一查,毛的诗词里专门写历史人物的一共就几首。写过鲁迅两首七绝;写过贾谊一首七律、一首七绝,这是长沙人;写过刘贲的一首七绝;还有半首《浪淘沙·北戴河》是写给曹操的。然后就是这一首写屈原的。至于他写给自己人,如丁玲、彭德怀、郭沫若、罗荣桓等就不在此列了。
(4)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临别时,毛泽###然把正在阅读的、有很多批注的《楚辞集注》一共六册收拢起来,送给田中。这是在外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