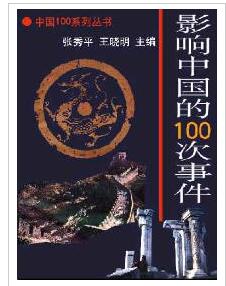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谁目睹过该炮的使用过程,或许会增加点难得的见识,那可比过年放鞭炮好玩十倍!
炮筒其实就是一段一头封死了粗钢管,封死了的底部侧面有个通内的小孔。而炮弹,则像个小小的没把暖水瓶,尖头上没有触发信管,但叨着根燃时三十秒的导火绳。
打炮时,用铁三脚架和炮盘支好炮筒,从小孔插进燃时十五秒的导火绳'比炮弹上的火绳短一半',露出外端,再从炮口往炮膛里填装黑火药,捅压实,将火绳的里端包埋住。黑火药每包半公斤,临时拆封倒入。如要打远,就拆封倒进三、四包或四、五包;打得近,则拆一包半或两包即可,视远近酌情而定。然后,一人持着炮弹,另二人分别同时点燃小孔和炮弹上的导火绳后,持炮弹的人才把炮弹从炮口放进炮筒,大家火速跑到二十多公尺外的隐蔽坑趴下,随它去骇人地一响,就把燃着火绳的炮弹喷射到小河对岸的联派阵地上去了。在山头上观察弹落点的人,只见一个黑点从头上高空飞过,一会儿,对岸田野上倏地出现一团黄光,并腾起烟柱,随后就是一个炸雷声扑过河来。
点导火绳得有个小技术:为保证它的点火端头新鲜干燥,在插入小孔前一刻,才把端头削成斜面,充分暴露出绳心火药。点火时,将两三根火柴并贴在斜面上,用火柴盒的药皮去擦燃它们,这样才能既及时又可靠'点炮弹上的火绳也这样办'。
由于它只能打个大方向,而且炮弹往往在空中就“天女散花”'因导火绳燃时不精准',一切该挨打的和不该挨打的,都可能遭它的殃,连农民房后的粪坑,也曾被它瞧上找到了,瞬时间变得一片狼藉。所以,与其说它杀伤敌人,还不如说它是恶作剧。
“六O ”、“八二”炮当然比它有用而好使得多,可是连里没有,即便有,炮弹也极珍贵。而它,虽猥琐无能,被蔑称为“土地雷”,但有一篮又一篮的炮弹可供随便打,人们不在乎它的对敌杀伤力,只图个像放大花炮般的快活。
于是,旷野成了面巨鼓,常被它擂得使人心尖战栗,尤其是在它射程内的男女老少农民们。
好景不长,谁也没想到它会自我爆炸。
那天早晨,清凉的空气沁人心脾。蜿蜒在两派阵地之间的碧绿小河,仍像往日那样玉带般地美丽。河边的竹林,把长长的竹梢像渔杆似的垂向河面,明亮而静静的河面上,映着可爱的蓝天白云。朝阳照耀下的白亮的公路石桥,雄健地横跨两岸。在那大好晴天的诱人早晨,谁也不会料到要出事。
当天带队的,是刚从一营调回来的老朋友“二排长”,不过现在他是副连长了'所以二排长得加引号'。打下纳溪城后,他在本连独挡一面地当了两个月的代理连长,实在蹬打不开,便被调到一营当副连长去了。好几个月过去了,那儿的人们还是适应不了他的本分和古板,老劳模也习惯不了他们,便与这个连的副连长对换了回来。
在一营时,他就听说这儿把“土地雷”玩得很漂亮,调回来的第二天早上,他就早早地率领着一帮战士进入了阵地,要见识见识这门英雄炮。
他专注地看着大家的操作,并积极帮忙。人们点燃导火绳后飞速奔向隐蔽坑时,他却急急地往前面的小山顶上爬,要去看炮弹怎样在敌人阵地上开花。远处的战士看见了,连忙大叫他快趴下,他反而更加快了手脚。
他成功了,亲眼看见了英雄炮大大出乎他意外的威力。只见对岸一茅屋前的晒坝上,蓦地闪现出一大团黄光,腾起一股浓烟,两只在晒坝边散步的白鹅,大概是一对正聊着天的神气夫妻,猛地双双跌入池塘,狂舞双翅贴着水皮冲过池面,窜上对面塘坎后,“嘎嘎嘎嘎”地大骂起来。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开门出来,站在门口望望房前不远的弹落点,又望望自家愤慨的大鹅,返身进屋又关上了门。茅屋顶上,正冒着轻柔的晨炊烟。
面对这有趣的场面,“二排长”瞪圆了双眼。他想了想,转身躬腰跑下山坡。
他向空中挥动着手里的半自动步枪,大声吼叫:
“你们真敢干唉,打老百姓的房子!造孽!”
看着这发疯的小老头,大家有点惭愧,水平确实是臭了点。一战士讷讷地说:“可能发射药填少了。”
“药填少了?”“二排长”几乎跳了起来,“再多点,再多点就把房子给炸球了!后面还有房子没看见?人家连早饭都没吃。”
好象吃了早饭的农民就可以打。
人们笑了。有人认为:“炮口该往左边再偏一点。”
“二排长”咬着牙,觉得这战士说得对。但根据刚才的情况,这样就真的要多装火药了,因为是打更远的斜线。索性将炮往下游搬么?那可不行,再搬一点就没山丘的掩护了。
“二排长”亲自动手帮着调整支架和炮筒,最后大家还是连炮盘也稍微挪了挪,又重新调整。打炮时,“二排长”要负责点发射药的导火绳,他认为自己刚才已看懂学会了。往炮筒里装炮弹的还是汪三,这是最危险的活。
汪三将点燃了火绳的炮弹装进炮筒后,边转身飞奔,边叫“二排长”快跑。“二排长”不理他,犹豫着不愿立即离去。不知他是在担心自己点的导火绳,还是在显示当官的比当兵的更沉得住气,直到远处的人们又齐声喊他,他才不慌不忙地走开,口里说:“来得及。”
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真如“二排长”所说,慢慢地离开也完全来得及!
也许是点发射药的导火绳出了毛病而自己熄灭,也或许是“二排长”压根儿就没把它真正点燃。不管什么原因,反正十五秒已过去好几秒了,土炮还是一声不吭地蹲在那儿。又等了仿佛一个世纪,要是炮弹打过去了的话,早都该炸了,但土炮还是执拗地不言语!
完全可以断定,两根导火绳都奇迹般地熄灭了。
隐蔽坑仅两尺左右深。“二排长”趴在坑里一个劲地看手表。后来,他缓缓撑起上身引颈探望,最后一跃而起。就在他迈上坑沿准备拍打身上泥土的那一瞬间,鬼炮好象终于等到了他的出现,突然炸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草帽般大的炮盘飞起,在空中砍折一棵比碗口大的松树,又对着他斜切下来,擦断了他的右大腿,然后高兴地在缓坡上跳了跳,摇晃着滚出两三丈远才躺下了。而他,也被撞出去了约一丈远。
土炮不见了,脚架已不知去向,只在地上留了个三尺多大的坑。在七、八丈远处的庄稼地里,斜斜地栽植了一株新品种,它如暖水瓶般粗细、扭曲得像蚯蚓、开裂着肚子,黑黑的大约有一人高,恍惚那就是炮筒。人们的耳朵嗡嗡作响,听不清相互间的喊叫。“二排长”已翻身坐起,脱下上衣慌忙地包裹冒血的残腿。
大概是发射药没被点燃,炮弹没射出去,时间到了就在炮膛里炸了。炮弹壳被炮筒增添了高压,再加上超量的发射药的威力,情况就如此壮观了。但为什么炮弹也熬了这么长的时间才炸呢?谁也不明白。
早已接替了吴玉兰的职务的小伙子,背着药箱飞奔而来。
红派的大金招牌“二排长”,被火速运到团部医疗队,然后又专车送去泸州了。团部怒不可遏,想用手中关着的一个联派坐探,把桥对岸的一位联匪骗过来,那联匪也是个副连长,如不交代对岸情况,也不妨敲断他一条腿!直像“二排长”的腿,是联派恶毒地把炮盘甩过来砍断的。
那联匪副连长是当地人,即三连阵地所在地农村生产大队的支书。他跑到对岸去了之后,还经常泅水或从桥上混过来与这坐探接头,有时还悄悄溜回家。
坐探是被人暗中“点水”'指认检举', 前天早晨才被抓到的。他是那位副连长家不远的邻居、生产小队的会计,二十五、六岁,家住桥头上游很近处的河岸上。据他交待:一旦红派有较多的人进入阵地,他就装着到河边小山坡上放鸭或四处找鸭,用撵鸭长竹竿给对岸指示方位和暗示人数。每天天亮前他都要偷偷地出来侦察,看有拂晓之战一类的严峻情况没有,然后回去,利用竹林的掩护,在家门口用防风煤油灯给对岸打信号汇报。晚上天黑后九、十点钟也要打一次,以便联匪对这方阵地白天黑夜都了如指掌。工钱每天一块。
那位副连长,经常在得到他的安全信号后,过来找他并回家看望,偶尔还斗胆地在家中享受一两天的天伦之乐。
团政委告诉坐探,要他把那副连长联络过来,只要他们愿意暗中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每过来汇报一次,就给副连长十五块钱,而坐探也十块,并绝对替他们保密。“算了,”政委舔了舔嘴唇,大方地对坐探说,“给你也十五块!真的。”
这可是个发横财的天文数字!一个县长的工资也不过每月六十多块钱。
为了把事办成功,除了要物质奖励外,政委还政治挂帅,做起了坐探的思想工作。
他又口若悬河起来。对这一带农村因武斗而蒙受的各种损失,他十分痛心,诅咒这场该死的战争。坐探竟参与了破坏自己家园的战事,他不胜惊讶极其遗憾,说小伙子太不了解国内外的大好形势,和那个副连长一道,完全走错了路!于是,全世界反美帝反苏修的革命怒潮,都在他口中变成唾沫星子,没完没了地喷射而出。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中东,哪儿的战斗他都了如指掌。小小的古巴,带头挖掉了美帝的心脏,我们的好老弟越南,又咬断了他的腿,全世界人民在烧它的毛!
政委很惊讶自己这个天才的比喻,昂起头,用手慢慢地抚理头上的长发,察觉头上已出了亢奋的汗,不过,天气本来就有点热。……至于苏联,这个社会帝国主义,在共产国际里早就成了臭狗屎了,连老牌的修正主义南斯拉夫都不理它,日本也搞反对它的示威*了。还有……
最后,政委终于满头大汗地、费劲地从全世界各大文武战场跑回来,咽了咽口水,断言眼前这场由联匪一手挑起的武斗,必将以红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他唏叹小伙子幸好有了这个回头是岸的好机会,否则的话,这一辈子就完了。
政委注意到,坐探像无数四川农民一样,有一双饱经风霜的赤脚,便叫人给坐探取来了一双四十二码的解放鞋。他强迫坐探打开包装纸取出试试,还令通信员打来了洗脚水。一试,正好,政委得意地笑了,猛拍了一下坐探的肩:
“你好好给我干吧,我眼睛准得很,没得错的!”
坐探无声地笑了,自己去倒了洗脚水后,又坐下把鞋脱下,仍用包装纸仔细地包好,双手把它握在手中,洗干净了的脚又坦然踩在地上。
坐探愿意立功赎罪。他被押回三营后,营部将他立功的时间选在当晚九点过,要三连派两名不怕死又有劲儿的老战士带他回家打信号,并叫三连去人将他押回了三连。
连里决定派汪三和“洋狗”押坐探去立功。“洋狗”名杨建国,是与汪三同一战斗小组的战友,由于横蛮好斗而得此外号。他勇敢强健又枪法出众,家庭成分也好,但常常无组织无纪律,此次行动仅当汪三的助手。 汪三家庭成分太差,因而十分驯服可靠,加之精明强悍和英勇,又是老战士,便当二人小组的组长。
于是,汪三和“洋狗”,午睡后就被通知到连部去看守坐探。“洋狗”说他有事情,叫汪三一人先去,他晚饭后再来。
在三连连部,坐探蹲在房檐下,胆怯地若有所思。大家像看怪物似的围观他,男男女女有的沉思、有的小声评议感慨。
坐探于六三年高中毕业回乡,高瘦、微驼而苍白,一眼可知是个农村的落魄读书人。没人想打他,但他自知有罪,满脸的卑怯和歉意,很怕不被信任和很怕挨打的样子。不管谁问他,他都积极地简短回答,一点不像电影上的地下工作者。地下工作者应是有坚定信念和意志的,可他,一副废物懦夫相!
人们好奇而鄙夷地打量他,嘲弄地问他一些有关特工的问题,比如:“你的收发报机呢?藏哪儿去了?”“给我照张像吧。不会?你他妈的特务还不会照像?”“来,我们两个摔一跤。不会摔跤?特务还不会摔跤?别客气了,来,露一手。”等等,大家哈哈笑。
汪三持枪站在旁边,惹不起大家,不吭声,有时也悄悄笑。坐探羞愧内疚自己的无能,含糊其词地不知怎样应付。幸亏连长在屋里听不下去了,出来一顿臭骂,混小子和看热闹的姑娘们才散开了。连长叫人给坐探提了个小凳出来。
开饭时,后勤战士给连部挑来的饭担中,有一份专给坐探办的小灶伙食。它比别人的晚餐高级得多:一碗红烧肉,一碟卤牛肉,还有炒鸡蛋和肉片汤。而其他人的大锅饭,仅炒鸡蛋和肉片汤而已。
大家都担心坐探吃不完,侧眼嫉妒地观察着他。众目暌暌下,他端着大饭碗,不太自然地使着筷子,下巴矜持地蠕动,喉结一滚一滚的。看得出,他在抵御着美食的力量,努力放慢进食速度,以免狼吞虎咽地被人嘲笑。不过,面对着好饭菜,他激动得手微微发颤,不仅因为平生很少吃到这样的盛餐,还由于被抓后的两三天里,人们为了促使他主动地说出一切,虽然还没打他,但对他的睡眠和饮食却是非常地疏忽了的。他以最大的毅力控制着速度,慢慢地把几个碗都羞愧地吃了个干净。
黄昏时,为了配合这次行动,由连长率领,共去了两个排。立功小队也走在稀稀拉拉的队伍中,“洋狗”在前汪三在后,把坐探夹在中间。
半途上,汪三警告坐探:“伙计听着,丑话说在前头啊,你不要逃跑。任何情况下都要跟着我们不要离远了,离远了我们就开枪,真的要开枪。”
坐探低头赶路,左胁夹着新鞋,不知在想什么,自言自语般地回答:“哪个敢哟。”
“洋狗”蓦地转身,用手枪顶住坐探的下巴,笑嘻嘻地边往上戳边问:“妈的,你说甚





![老公,国家包分配的![星际]封面](http://www.8btxt2.com/cover/57/5784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