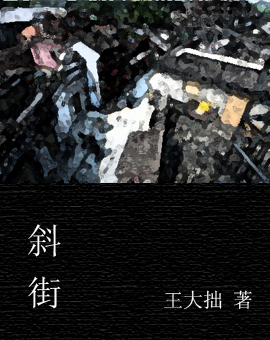斜街-第5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朱洛甫离开书房,去向怀元的母亲询问怀元需要一些什么生活用品时,于化吉已把棋盘摆在自己和宗雪竹的面前。棋盘也是宗静涵获得的馈赠,所有的木件都是鸡翅木,棋盘由四块方方正正的翡翠拼接而成的,宛若碧水的色地和温润内敛的光泽把黑白双方的对弈映衬得格外醒目。朱洛甫回到书房时,他们的对弈刚刚开始。朱洛甫和宗雪竹是一对儿女亲家,这在镇上鲜为人知,但他却已从范嘉言那里了如指掌。他和朱洛甫都是脾气温和的人,但他却不认为自己和朱洛甫气味相投,因为他处事喜欢删繁就简正像基督教的圣事那么简明扼要,而朱洛甫处事不分巨细却像天主教的繁文缛节。
不过,在宗雪竹面前,他们却有共同之处,除了输棋之外,由于宗雪竹是个有妾室的人,从不奢望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为他们心照不宣。即使宗雪竹没有妾室,仅仅因为他是个无神论者,他们也不会和他深谈上帝。他们相信,任何属于经验以外的东西,都会被宗雪竹一笑置之,深谈下去的结果势必会让他指指点点,那样的话,他们自讨没趣反倒无关宏旨,假如他的言论若是损害了他们的信仰,那可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每在宗雪竹面前谈起基督耶稣时,他们都谨小慎微,或叫他明白基督耶稣是个很有人情味的救主,或让他知道基督耶稣诲人不倦的目的和圣人诲人不倦的目的都是为了惩恶扬善,不但浅尝辄止,而且只敢涉及基督耶稣对人类的道德关怀,不敢涉及基督耶稣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于后者,他倒不一定说那是毫无根据的志怪之说,但一定会说基督耶稣治心乏术就装神弄鬼、虚张声势,势必出言相驳。
朱洛甫回到书房的目的,是希望宗雪竹给大女儿或二女儿写一封信,以便于朱玉茹始到省城就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宗雪竹索性写了两封信,分别告诉大女儿和二女儿,她们既然都这么重视朱玉茹去省城读书这件事情,不妨商量个办法,使她们都有机会照顾玉茹。这时,推枰认输的于化吉一边喝着茶,一边面对着棋盘回忆着自己和宗雪竹行棋对弈的过程,想弄明白自己明明处于优势的棋何以在最后时刻突然呈现无可挽回的败局。接着,一如往常,他一边喝茶一边和宗雪竹聊天。就像一种习惯,聊着聊着,他又不由自主地谈到了基督耶稣。不过与往常不同,他没有强调耶稣的神性,侃侃而谈的几乎都是耶稣的人性。而且,他郑重其事的样子与其说是聊天,不如说是探讨学问。果然,当他谈起耶稣和圣人的关系时,朱洛甫终于听出来了,他试图使宗雪竹相信:耶稣和圣人非但不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由于他们劝人为善的言行如出一辙,他们彼此之间其实还能够相互兼容,融为一体。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向宗雪竹叙述了利玛窦神父如何由穿僧服而改穿儒服,如何使人相信耶稣是圣人的朋友而非圣人的仇敌,如何苦读四书五经又如何成为声名显赫的“西儒”,如何用耶稣的言行解释圣人的言行又如何用圣人的言行解释耶稣的言行,如何体现高尚的品格又如何打动了徐光启、李之藻那样的高官显贵,徐光启如何皈依了基督又如何不失儒家本色,李之藻如何认为耶稣和圣人水乳交融又如何主张合二为一。
“所以,”他说,“耶稣基督和圣人并非水火不容。利玛窦神父穿儒服读儒书固然出于谋略,但他犹如圣人的品格和言行却表明:基督耶稣虽是异族,但异族之异绝非匪夷所思,其内心外行与我族并无格格不入的地方,如果和圣人融为一体,则不足为怪。”
宗雪竹很不以为然,听完他的话,甚至都笑出了声。
“异族终归是异族。利玛窦以圣人的言行彰显耶稣基督,其内心外行与我族相比,确实不曾水火不容,但那毕竟是利玛窦的谋略,而非利玛窦的目的。异族之异,显然只在于归化,不在于求同存异、入乡随俗。徐光启皈依了耶稣基督,但出于儒士本色,他对耶稣基督寄以厚望的事情,也只不过是驱佛补儒罢了。至于李之藻,他想叫耶稣基督和圣人彼此兼容而融为一体,如果不是异想天开,那便是一厢情愿。异族未必容纳我族,而我族却足以容纳异族。”
于化吉和朱洛甫面面相觑的时候,宗雪竹突然指了指棋盘,接着又指了指于化吉的戒指。这使他们更加迷惑。宗雪竹轻轻笑起来的时候,他们恍然大悟,这才知道宗雪竹打算借物喻事。
“翡翠就是翡翠,钻石就是钻石。我族的中和之德犹如翡翠,异族的纯粹之性仿佛钻石,孰优孰劣暂且不论,但孰大孰小却由此可见一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嘛!”
他们离开不久,宗家大院又来了一个客人。客人是县署派来的信使,来到宗家大院的目的是为了把孟知事的一封信交给宗雪竹。孟知事在信中说,鉴于鸦片正在宁城全境特别在雍阳迅速蔓延的严重局面,县署确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用以禁绝鸦片,而作为这个机构的首倡者,宗雪竹应当受到嘉奖。信中还说,三天后,孟知事将到警察局会见宗雪竹及商会和中原公司的首脑人物,以便于大家共同商量设立禁烟机构的事情。
“这等小事何须嘉奖,”宗雪竹对信使说,“我届时去镇上议事就是了。”
第七章(1)
三天后,宗雪竹如约来到了镇上。没去警察局之前,他在裕民粮行停留了一会儿,和花柳先生不期而遇。这时,镇上将要设立禁烟机构的传闻尚在街谈巷议中忽隐忽现,而一家妓院将在包工院张灯结彩的消息却已经确凿无疑了。这个消息说,一个名叫宝裕德的包工因病暴毙之后,他的一妻一妾为了争夺遗产差点打起来,妾室宝文氏因无子嗣相助落败后,索性利用寓所重操旧业,甚至连她当*时的名字——水芙蓉,也恢复如初了。这个消息还说,一些包工认为水芙蓉在包工院重操旧业势必会把包工院变成花街柳巷,因而对水芙蓉颇有微词;而另外一些包工却认为水芙蓉在包工院重操旧业尽管会让包工院失去往日的体面,但考虑到所谓的体面比起不必涉足翠云楼便可望寻花问柳的便利,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事,于是就对即将张灯结彩的妓院持以默许和期待的态度。
花柳先生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刚从招商客栈搬倒斜街,就住在宗四原先租居的房子里。不过,宗四当初付给陈泰和的是租金,他付给陈泰和的却是一笔转移产权的积蓄。他买了家具和生活用品,请吴翠花缝制了被子和褥子。他拎着一条口袋去裕民粮行买粮之前,所有的暗娼都为他定居雍阳的举动感到欢欣鼓舞,但他却在为来自包工院的消息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一切都表明雍阳确实需要一个花柳先生。他把口袋交给粮行的伙计,伙计把二十斤玉米面倒入口袋,然后用细麻绳把土布口袋拦腰系住,又把二十斤白面倒入口袋。当伙计十分娴熟地做完这桩生意,他已经走到后院,出现在宗雪竹面前。
他从不认为宗雪竹是一个平易近人却又难以接近的人,他之所以现在才和宗雪竹近在咫尺,完全在于宗雪竹深居简出的生活和神出鬼没的行踪,绝非自己畏惧鸿儒巨绅的缘故。当他知道宗雪竹来到裕民粮行的目的是打算和宗四一起去警察局会见孟知事,他对镇上将要设立禁烟机构的传闻始信不疑,同时对宗四并不总是口若悬河的秉性也始信不疑。因为对诸如此类尚未践行的政务,宗四虽然已经了如指掌,却总能做到守口如瓶。
正像他所有怪异的言行一样,他和宗雪竹非亲非故,却一上来就把宗雪竹称为“先生”,称自己为“学生”。通过宗四,宗雪竹对他怪异的言行已有耳闻,因而不惊不怪,刚聊了几句就把话题引向了他的来历和身世。
他是一个遗腹子,在黄河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出生时,喜欢打猎的父亲因在一片沼泽地的中央地带陷入泥潭,刚刚死去不久。他原本是一个可怜的遗腹子,而母亲生下他不久又十分痛苦地死于产后风这一事实,又险些使他的性命朝不保夕。一个好心的邻居把他送到一个刚刚坐过月子的女人那里时,那个女人尚未从女儿夭折的痛苦中摆脱出来。女人的丈夫用一副草药追回了女人的奶水,女人用追回的奶水救活了他的性命,女人的丈夫和那个女人就成了他的养父和养母。养父养母不但养活了他,他刚刚懂事,还不顾亲戚们的反对,设立家塾予以教育。养父养母视若己出的庇护曾使他无忧无虑,养父养母相继去世而他们的亲戚把他视为外人的隐患终于也暴露无遗时,他才终于察觉到自己孤独无助的困境,始知人心险恶。所有值钱的家产被养父的亲戚们以种种借口霸占后,面对空荡荡的院子,他虽无性命之忧,日子却已经难以为继。于是,他离开了故土,只身一人游荡于黄河北岸,靠医治花柳病维持生计。发现雍阳镇是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就停住脚步,不再漂泊。
宗雪竹对他的身世流露着同情时,还对他家塾启蒙的经历暗暗吃惊。兴办学堂前,黄河北岸的办学场所除了书院便是私塾。私塾有三种形式,一是村塾,一般为人口众多的村子所设,使村里的孩子有一个公共的读书场所;二是馆塾,一般为宿儒所设,学生前往宿儒的家里就读;三是家塾,均系官绅人家重金聘请宿儒于官绅家中,学生足不出户便可望获得启蒙。就连宗雪竹,小时候读的也只是馆塾。所以让宗雪竹感到吃惊的是,他出身寒门,居然启蒙于家塾,足见其养父养母对他的厚爱和期望。
“虽非生身父母,其心又何尝异哉!可是,你家塾发蒙,所学非浅,为何半途而废,转而研习歧黄之术?”
“让先生见笑了。学生虽发蒙于家塾,却生性愚钝,终不长进而空负其名,辜负了养父养母的苦心。至于……”
见他面露难色,宗雪竹善解人意地摆了摆手。
“怪我多问,不说也罢。”
“学生……学生的养母原是青楼*,养父原是走方郎中,养父治愈了养母的横痃隐疾,养母心存感激即自赎其身,嫁给了养父。不过,养父养母对这一缘故一直讳莫如深,学生成人后虽有耳闻,终没敢问。养母临终前谈及此事,学生才知详情。那时,学生的养父已经去世,养母把他行医时的医案悉数交给学生,嘱咐学生今后若是以此为生,必先以养父为师,师承养父的医德品行,宽厚待人,积善行德。养父的医案积累盈尺,每桩医案都记载着详尽的用药之道。学生仔细研读,一一熟记于心,才敢离家行走;行走之中又屡有医学心悟,才敢于树帜行医,走南闯北。”
当宗四插嘴说由于花柳先生品德高尚,连黑蛋那么浑浑浑噩噩的莽汉都快被花柳先生调教成正人君子时,宗雪竹却已经心不在焉,心中另有所想。
“不治自愈的病,”宗雪竹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不治也罢。”
“不治自愈?”宗四首先奇怪起来,“脏病能不治自愈?”
宗雪竹意识到自己走了神儿,就笑了一笑。
“早年偷读闲书读过一个故事,当时未作揣摩,现在想来才觉得这个故事颇有深意。唐朝盛世,男欢女爱,人欲横流,市镇之上娼肆林立,但凡男人无不趋之若鹜,沉湎其中,乐此不疲。观音菩萨见此情形十分忧虑,但她忧虑过后却举步下凡,变作娼妓纵身欲壑,人皆可夫……”
宗四的心里突然腻歪起来,心思直往家里跑。因为家里有一个佛龛,佛龛里端坐着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一天到晚要享受妻子供奉的两炷香火。
“坏啦!”宗四几乎惊叫着说,“怀礼他妈供了这么多年,原来供了个婊子!”
他说完这话,宗雪竹和花柳先生不约而同地看了看他,但谁也没有理他。这时,从铺面传来了宗怀礼吵架的声音。宗四起身走向铺面,去那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子在跟什么人吵架。
“观音菩萨法力无边,”花柳先生说,“足可去势灭欲,可她偏偏混迹于青楼娼肆,推波助澜,用意何在?”
“食色性也,”宗雪竹说,“观音菩萨纵然法力无边,那也不能逆天而行,去势灭欲,断绝芸芸众生繁衍之路。推波助澜也好,超度也罢,把人欲推至巅峰之日,便是人欲逆转之时。世人咎由自取,必痛定思痛,复归伦理纲常。观音菩萨纵身欲壑,意欲何为?欲擒故纵是也。所谓不治自愈,便是这个道理。”
“原来如此。”花柳先生说,“先生不以青楼娼肆为虑,却以鸦片为忧,所以就力倡专事禁烟的政所。”
“鸦片损身伤志。吸食成瘾者,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危害乡里,一旦相袭成风,非但不会不治自愈,倘若视而不见,放任自流,必成不治之症而万劫不复。”
第七章(2)
宗雪竹不以娼肆为虑,却以鸦片为忧,这是因为鸦片这时已从矿区和雍阳镇蔓延到了宁城的每一个角落,富人吸食鸦片时往往以此为荣,而穷人吸食鸦片时则显然打算以此果腹,宁肯短缺了粮食,也不肯短缺了鸦片,似乎鸦片是可以取代粮食的东西。可是,宗雪竹首先建议孟知事设立一个机构专门用以禁绝鸦片时,孟知事却认为个别人吸食鸦片的现象不值得政府兴师动众,而且作为政府的一项政务,禁烟工作虽然时张时弛,可也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如果因为这点小事就如临大敌,稀里糊涂地设立一个什么专门机构的话,他落个无的放矢的庸名倒无关紧要,一旦劳民伤财而惹起民愤民怨,那可就要自取其辱了。后来,当他意识到宗雪竹一向出言谨慎,一旦出言势必持之有故,就命令几个幕僚深入民间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宗雪竹绝非危言耸听,个别村子的情况甚至还要糟糕,几乎家家都有吸食鸦片的人。于是,他派人给宗雪竹送了一封信,决定和宗雪竹等人一起商量设立禁烟机构的事情。
宗雪竹准备去警察局时才知道铺面里确实发生了吵架事件,起因是一个前来买粮的铁路职员用英语辱骂一个跟他发生摩擦的顾客是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