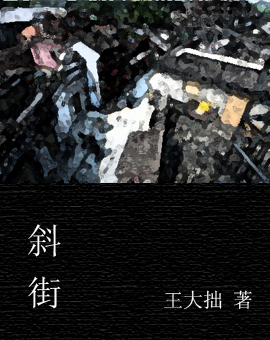斜街-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爱吃饺子就自己吃个够,给我留什么!”
崔六六的怒斥又把她吓坏了,连头都不敢抬了。她转过身,向隅而立,没有一点声息,唯有浑圆的肩膀微微耸动。崔六六知道她在悄悄流泪正像知道自己的怒火从何而来一样。过了很长时间,崔六六才舒了一口气。
“你爱吃就吃,别给我留。他们确实认错了人。再说了,一点皮肉伤,又死不了人。”
崔六六说这话时,口气已经恢复如常。但她转过身来重新面对丈夫时,却又一次哭出了声。
“我怕,”她试图搂住丈夫的肩膀时,边哭边说,“我怕啊!”
“你怕什么?”崔六六说,“怕我丢了?怕我死了?你牵挂我我知道,可我也牵挂你你知道不知道?我牵挂你是怕你受委屈受欺负,只要我不死,就一直这么牵挂你。”
“你死我也死,你死哪儿我也死哪儿!”
“你别傻了,我不会随随便便地就被什么人打死的。我把你领回阳世,不是叫你和我一起死的,是打算跟你一起过日子的,过一百年也不嫌长。”
她破泣为笑。她紧紧搂抱着丈夫宽厚的肩膀,一往情深的样子就像搂抱着自己因祸得福的命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六章(1)
在崔六六养伤的日子里,刘长风愧疚地告诉崔六六,尽管他穷追不舍,但那三个男人却还是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得无影无踪。但刘长风并不甘心,一再询问崔六六有没有与人结冤成仇的事情,以便找出元凶绳之以法。崔六六尽管认为此事与宗怀仁有关,因为宗怀仁当年就曾使用雇凶伤人的手段报复过一个工人,时至今日必会故伎重施,但他却抱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态度息事宁人,一再说那三个男人肯定是寻仇认错了人。
在养伤的日子里,崔六六没有发现彤云的饮食变化,却发现曾在她眼睛里忽隐忽现的东西已经无影无踪,眸子里透着轻松和惬意,仿佛上帝没能让她养儿育女,却改变了她的心灵。和瘸子程制止妻子的理由不同,崔六六当初制止她皈依上帝的时候,并没有保家仙和洋神仙水火不容之类的理由,只认为信奉上帝和信奉佛祖既然都为女人所热衷,她与其信奉了初来乍到的上帝,还不如信奉了早已入乡随俗的佛祖。他后来尽管没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任由她信奉了上帝,却不知道她为什么信奉了上帝。当他意识到她眼睛里忽隐忽现的东西是忧虑时,他才明白她所忧虑的事情正是他所忧虑的事情,但他仅仅做到了深藏不露,她则不仅做到了深藏不露,而且在深藏不露的情况下试图使自己变得无忧无虑。
伤愈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感谢胡四孩。出事那天晚上,胡四孩机智的举动不但解救了他,还保全了他的黄包车。一天傍晚,彤云炒了四个菜,他去酒铺买了一壶酒,然后把胡四孩邀到家里。他和胡四孩都不胜酒力,所以喝了很长时间才把一壶酒喝完。摇摇晃晃的他把同样摇摇晃晃的胡四孩送走后,在妻子的帮助下才找到床。躺倒前,彤云帮他*服是怕他和衣而睡会着凉,但他却认为妻子要和自己干那种事。
“睡也白睡,”他说,“你又不会生孩子。”
第二天,他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已日上三竿。他急忙穿衣下床,既埋怨彤云,也埋怨自己:
“怎么不早点叫醒我?喝酒果然耽误工夫!”
穿好衣服,他抬头一看,看见彤云托着腰部站在自己面前,不只姿势十分奇怪,连笑盈盈的表情也异乎寻常。
“昨晚你说了什么,你还记不记得?”
“说了什么?四孩是什么时候走的?”
他边说边把趿拉着的鞋提上脚根,脸也顾不上洗,趴到桌上就去吃彤云早已准备好的早饭。
“谁说我不会生孩子?”
彤云走到他面前追问的时候,他起初充耳不闻,扒拉了几口饭之后才猛然抬起头来。
“你说什么?!”他吃惊地说,“我昨晚说了什么?”
彤云笑而不答,充盈着泪水的眼睛里不但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忧虑,反倒闪耀着幸福的光芒。不过,使她无忧无虑的却不是上帝,而是花柳先生。
那是彤云和花柳先生不期而遇的结果。一天中午,彤云站在胡同口一边等候丈夫,一边逗着宝贵玩的时候,花柳先生恰巧从她的面前走过。原以为自己的病人是一个染上横痃隐疾的单身汉,没想到自己最终治愈的病人却是被翠云楼逐出门外的一个楚楚可怜的*,这一奇人奇事不但使得花柳先生对崔六六刮目相看,还使得花柳先生格外关注彤云,暗暗认为焕然一新的彤云是一个注定要做贤妻良母的女人。看见彤云逗着宝贵玩耍,花柳先生就笑着对她说,她这么喜欢孩子,为什么不自己生养一个。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花柳先生说罢这话便径直而去,她却后发先至,在基督教堂门前拦住花柳先生,吞吞吐吐地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花柳先生。花柳先生先是笑了几声,然后就凿凿有据地说,横痃隐疾尚无殃及生育的先例,无论男人或女人,一经治愈,便与正常男女毫无区别,反倒是一种名叫白浊的脏病祸害女人,从而使女人罕有生育现象。她对花柳先生的话半信半疑。在丈夫养伤的日子里,当她发现自己想吐想吃酸东西时,就悄悄请教了温玉枝;当她确信自己已有身孕,丈夫却在酒后埋怨她不会生孩子。
“谁说我不会生孩子?”
她追问丈夫时,已经泪流满面。崔六六这才发现她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同时发现她用双手托着腰部的动作分明是告诉他,她正在给他们孕育着儿女。可是,他却没有因此而显得心花怒放,呈现在脸上的东西更多的是惊奇。他从街上给她买回来两串冰糖葫芦之后,呈现在脸上的东西依然是惊奇。
“洋神仙真有这么邪门儿,不信不灵,一信就灵?”
“上帝才不邪门儿呢!不过,叫我明白我还能养儿育女的却不是上帝,偏偏是那不信上帝的花柳先生。”
尽管彤云认为自己的生育能力和上帝毫无关系,花柳先生的经验也证实了横痃隐疾并不妨害生育能力,但是,关于一个*从万能的上帝那里获得生育能力的神话故事却不胫而走。谁也不知道这个神话故事的始作俑者是谁,同时由于这个神话故事没有指名点姓,甚至连主人公究竟是基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语焉不详,因此谁也不敢确信主人公就是皈依了上帝之后才有了身孕的彤云。大家只知道,津津乐道并把这个神话故事广为传播的人是姚秀珍。不过,姚秀珍说起主人公的真名实姓和宗教身份时也语焉不详,好像主人公的真名实姓和宗教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人公获得生育能力的奇迹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
第六章(2)
姚秀珍至死也没弄明白自己皈依上帝出于怎样一种动机,因为她皈依上帝的结果显而易见,她至少不会再从纳妾娶小的富人那里挣到补贴家用的钱了。她接受领洗时,鲁斯姆特尔神父只给了她一个信仰,并没有赋予她任何义务。然而她从此便深信不疑的是,如果拯救生命是善行的话,叫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上帝就也是善行。怀着这一信念,她能说会道的嘴又有了用武之地,这便是不失时机地在女人中间宣扬上帝的存在。在斜街,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不屑于谈论上帝,倒是女人们经常漫不经心地把上帝挂在嘴边,一边讨论着上帝一边纳着鞋底。她们首先争论的问题是上帝究竟是一个好神仙还是一个坏神仙,接着为上帝究竟是万能还是一无所能这个问题各抒己见。后来,就连上帝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也成了她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尽管她们的讨论总是叫她啼笑皆非,但她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说起上帝诸多不可思议的能耐时依然喋喋不休。可是,她一方面在婚姻市场上撮合着一夫一妻的婚姻,另一方面又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宣扬上帝,两相兼顾的结果难免顾此失彼,不是因为钱财冷落了上帝,就是因为上帝疏远了钱财。当她的丈夫认为前者和后者对女人而言都是不务正业时,就又把炒凉粉的铁铲摔到了炒凉粉的铁锅里。
“滚回家做饭去!”胡兆春怒气冲冲地说,“做好了饭就老老实实地给老子停在床上,看老子是你的上帝还是洋神仙是你的上帝!”
鲁斯姆特尔神父曾经不断地告诉信徒们,除了撒旦,真正的信徒是无所畏惧的。可是,除了畏惧撒旦,她还畏惧丈夫。
“瞧你说的,”她小声嘟囔道,“上帝可没叫女人动不动就停在床上。”
“放屁!”胡兆春把刚刚拾到手里的铁铲又摔到了铁锅里。“上帝难道叫男人动不动就停在床上,女人想和一把就和一把,叫他妈的女人来当上帝?”
她逃也似地离开了丈夫的摊子,一方面出于畏惧,另一方面防止丈夫继续当众倾吐污言秽语。她就这样过日子,在别人面前舌如巧簧,无拘无束,在丈夫面前却笨嘴笨舌,噤若寒蝉。她舌如巧簧似能说透人间的一切玄机,可一到丈夫面前,舌头便神使鬼差似地僵硬起来,木木讷讷犹如稚童。因为即使面对复杂的信仰问题,丈夫也能以最简单的道理和最粗鲁的言辞一言以蔽之,她纵有满腹斯文也无以辩驳,好像丈夫一下子就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不容置疑。
她生养了一双儿女,儿子叫桐豆,女儿叫桐花。她从丈夫的摊子回到家,桐豆正拿着一根又细又长的木棍,有一下没一下,一如既往地敲着妹妹的脑袋,桐花则一如既往地蹲在地上玩着一种谁也看不懂的游戏。她对粗鲁的丈夫无可奈何,对顽皮的儿子也无可奈何,不光无法使儿子相信上帝的存在,甚至还无法使儿子放弃恶作剧似的游戏:每当桐花蹲在地上玩着一种谁也看不懂的游戏时,他就像寺庙里的和尚似的,把妹妹的脑袋当木鱼敲。桐豆和桐花虽是一母同胞,却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地方,桐豆神情活泼显得聪明伶俐,桐花神情呆滞却分明就是一个笨蛋。不过,她从不认为后者是丢人的事情,因为斜街经历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生育高峰之后,孩子中的愚人愚相就不再是某一个家庭独有的不幸,而是斜街的一道风景。她起初只有一点担忧,害怕桐花跟斜街的傻人厮混到一起,从而变得更加愚笨。当她发现傻人无一例外地都是自得其乐的孤独者而桐花显然不是那种只会独自玩耍的孩子时,她才知道自己的担忧毫无道理。她后来还发现,和桐豆相比,桐花顶多算一个缺心眼儿的孩子;但要和傻孩儿陈亦贵相比,桐花简直就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神童。
她说起上帝诸多不可思议的能耐时尽管喋喋不休,俨然播撒上帝种子的使者,但她却是一个几乎一无所获的使者。相比之下,真正在斜街播撒上帝的种子并且有所收获的人是于化吉。
于化吉是一个名医,留学英国期间就皈依了上帝,成为一个虔诚的新教教徒。他从烟台应聘来到福记公司医院不久,就在镇上的基督教教徒中间成立了一个名叫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教会组织,开始了播撒上帝种子的事业。鲁斯姆特尔神父还没产生在别墅区建造天主教堂的念头时,他就已在教徒中间募集到了足以建造一座圣殿的钱了。广益局还在朱洛甫的胸中运筹帷幄时,基督教堂就已在斜街落成了。不过,基督教堂兴建之初,他并没有意识到地址的重要性,只觉得斜街的地价低廉,可以给教会省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当教堂的第一批建筑即一座圣殿和三间男用礼拜堂相继竣工之后,面对形形色色、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他发现教堂恰巧建在了一个既不疏远富人也不冷落穷人的街区,他才知道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多么英明,仿佛上帝的启示正是如此。
他呆在教堂时的身份是代理牧师,访贫问苦时的身份既是代理牧师,也是医生。他施舍给人们的几乎都是用以止泻、止痛、止咳的药片或药丸。由于他常年戴着一枚镶着一粒石头的戒指,他向人们伸出援手时,人们不仅从他的施舍中看到了基督耶稣,也看到了那粒石头的光芒。零乱而耀眼的光芒笼罩着那粒石头,使那粒石头看上去很像一块破碎的冰。然而,起初谁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一粒什么石头,只为它复杂的形状和零乱的光芒感到惊奇。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站在胡兆春的摊位前吃着炒凉粉时,不约而同,胡兆春的一家人都被它奇异的光芒吸引住了。
“这是冰,” 桐花说,“怎么也晒不化的冰。”
“这是盐,” 桐豆说,“怎么也吃不完的盐。”
“这是玻璃,” 姚秀珍说,“一看见太阳就头晕目眩的玻璃。”
“全是胡说八道!” 胡兆春说,“天底下没有晒不化的冰,也没有吃不完的盐,一看见太阳就头晕目眩的是他妈的猫头鹰,——这是白玉!”
他没有马上纠正胡兆春,不紧不慢地吃完炒凉粉,才冲着胡兆春笑了一笑。
“这不是白玉,” 他说,“这是钻石。”
他戴着闪耀着奇异光芒的钻石戒指出入斜街,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乐善好施的口碑。正像水到渠成,耶稣教堂的三间女用礼拜堂正式启用之后,他乐善好施的口碑果然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又有一些女人做了基督耶稣的信徒。每逢圣事,各处一室的男人和女人,无论有着怎样的心思,其虔诚庄重的神情毫无二致,就连出于忏悔的哭泣也如出一辙,抹在衣襟上的不是泪水就是鼻涕。男人的忏悔几乎悄无声息,女人的忏悔则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抽抽搭搭的哭声,有的女人甚至当众嚎啕大哭起来,而且越哭越离谱,到了后来,居然哭起了已经去世一百多年的亲人。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徒,因为她们总是怀着五花八门的心思而来,又总是带着五花八门的满足而去,把教堂当成了应有尽有的贸易市场,而非救赎原罪的精神家园。不过,他并不生气,因为她们相信上帝的存在毕竟是好的开端。
他只对出自她们并在斜街流传的神话故事感到啼笑皆非。最令他啼笑皆非的是这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