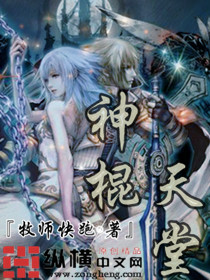墓碑天堂-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很普通的一名战士,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火热的革命斗争使他逐渐成熟了。在全身即将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创作出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1947年,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读到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它使我心灵为之震撼,生活受到鼓舞。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人生,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了。我把剧本译成了汉文,很快就在兆麟书店出版。翌年,哈尔滨市教联文工团将这戏搬上舞台。连演多日,场场爆满,成为哈尔滨市解放初期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值得重视的活动。建国以后,该剧又在北京等大城市演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孙维世导演,金山、张瑞芳等主演,这部话剧发挥了更大的教育作用。保尔成了新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1956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赖莎应邀来到我国访问。她为我国青年做过几场报告,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我为她担任过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女工出身,朴素、诚恳、热情,平常她像拉家常似的跟我们谈天说地,讲了很多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她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尼古拉可关心形势的发展了。他听广播,还让我在墙上挂了一张中国地图,自己看不见,让我告诉他中国红军行进的路线……”
赖莎得知我译过剧本《保尔·柯察金》,而当时的教员孙杰参加过该剧的演出,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时,她很高兴。她说:“你把你的妻子带来让我见一见……”1957年春节前夕,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她。她拉着我们的手戏谑地说:“记住,我是你们的媒人!”她送给我们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她和躺在病床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她在照片的背面写了一句话:“祝你们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
1987年我又来到莫斯科。中苏两国都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我专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去拜见我的“媒人”,她当时担任该馆馆长。她那深棕色的头发已经变得银白。我们又谈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谈到他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情况,并回忆了她访问中国时留下的美好印象。那天,我为她画了一张速写像,她签名时仍然冠以“媒人”二字。
那次,我又凭吊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墓。墓碑——庄严雄伟。
奥斯特洛夫斯基是1936年12月22日逝世的。25日火化后,他的骨灰盒先是嵌在新圣母公墓的墙里。1953年,苏联政府决定将他的骨灰入土安葬。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曾表示过,他死后希望能长眠在他敬爱的作家、小说《恰帕耶夫》的作者富尔曼诺夫的墓旁。他的墓上树立了一座墓碑,碑上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半身浮雕像。雕像作者齐加里。奥斯特洛夫斯基斜身靠着枕头,侧脸面向远方。一只手放在书稿上,另一只手搭在胸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表情安详深沉。这是一位不向敌人、不向疾病、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人。墓碑的下端雕有军帽与马刀,表明他少年时代英勇无畏地驰骋沙场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2007年秋,我再次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墓前,在他的墓碑上增加了赖莎的名字和她的生卒年代是“1906—1992”。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使我浮想联翩。我背诵他留在人间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的斗争!”
我早已告别了青年时代,越过了古稀之年。同龄的妻子突然双目失明,我护理她的时候,常常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想到他的夫人赖莎和她赠给我们的照片,还有照片上的那句话:“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我每每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夫妇,这时我身上不由得会涌起一股热爱生活的暖流。
1998—2008
。 想看书来
长眠在橡树下(1)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
橡树——在俄国象征永恒,象征不朽,象征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知道特瓦尔多夫斯基安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里。我知道他的墓碑是一块大石头。我见过朋友们拍摄的照片,见过拥抱着巨石的那棵大橡树。但我还是想亲眼看一看这位诗人的墓碑。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墓在七区,靠高墙的路边上。一段矮围栏将它与人行道隔开。一棵橡树伸出很多枝杈,在风中响动着硕大的叶子,像帐篷一般覆盖在墓碑的上边,为墓主遮风挡雨。墓碑左右是两块横卧的石板,分别刻着诗人和他夫人玛丽娅的姓名及生卒年代“1908—1991”。
浓郁的橡叶好像沉吟着墓主沉浮的一生。我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情况,想和知情人接触一下,谈一谈。说来也巧,几天后,俄罗斯作家协会的朋友们邀我到斯摩棱斯克州的后山村去,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诗歌奖颁发大会。
“那儿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出生地,那儿有诗人的故居纪念馆……”老友巴维金说:“那儿有他的乡亲乡民,也许他们会向你提供一些有用的材料。”
1999年6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我们经过两天的旅途来到了后山村。
后山村一派节日气象。从莫斯科等地来了不少文化界人士。我是嘉宾中唯一的外国人。
主席台设在一个露天平台上,那里耸立着一座特瓦尔多夫斯基故居纪念碑,也是一块大石头,旁边摆着他的一幅巨像,一对灵活的眼睛凝视着前来出席大会的群众。
大会主席宣布获奖人名单,颁奖,献花,奏乐。然后一个又一个人上台祝贺、发言、朗诵,致答谢词。主人请我也讲几句话,盛情难却。
我祝贺了三位获奖诗人,然后介绍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和流传的情况。在场的俄罗斯人没有想到中国人是那么熟悉他们家乡的诗人,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会后,很多人围住我,提出许许多多他们关心的问题。我从他们的提问中同样感到惊讶。惊讶的是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今日中国那么不理解,甚至误解。但他们的赤诚和坦率让我感动。
一位白发苍苍白须飘逸的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长时间不放,眼睛里闪着泪花,用喑哑的声音表示感谢。主人替我们作了介绍:“这位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胞弟伊万·特里丰诺维奇。”
他告诉我:他们的父亲是从外地搬到这个村子来的铁匠,身体强壮,善于经营,读书识字,渐渐富裕了。母亲操持家务,抚养七个儿女,十分辛苦。农业集体化时,他家被定为“富农”。按联共(布)党的政策,富农属于被消灭的阶级。1931年特瓦尔多夫斯基全家被扫地出门,从富饶的俄罗斯腹地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那时,小特瓦尔多夫斯基经常给报刊写些通讯稿件,已离开了农村,到城里去工作了,所以他成了家中唯一幸免那场危难的人。有人认为他逃避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有人说他对父母兄弟姐妹绝情,甚至不愿和自己的父亲握手。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阶段,每个人思想变化都有些异乎寻常。年纪轻轻的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了保护自己,也许就采取了这种划清界限办法。我想,这是入世不久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早年的一种表现。
特瓦尔多夫斯基自幼喜欢诗歌,十三岁时,他拿着自己的诗请教语文老师。老师指出他的诗的缺陷是:“一看就明白”,而“新诗”要求人人看不懂。把当时的,即20年代初期的文学杂志拿给他看,让他当做学习的样板。于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练习写看不懂的“诗”,他写不出来,怀疑自己没有写作的才能。“后来,我终于写成了一首。它令人看不懂,我自己也记不得其中的任何一行,也记不得诗中写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写过这样一首‘诗’。”特瓦尔多夫斯基晚年在《自传》中这么写道。后来,在文艺创作的另一股风的影响下,他开始用粗俗的语言写谁都会说谁都能看懂的“诗”。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写成长诗《通往社会主义的路》。诗发表了,甚至受到了表扬,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那不是诗,那是政治口号。特瓦尔多夫斯基正是在这种左右摇摆和求索中踏上了自己的路。 。。
长眠在橡树下(2)
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在苏维埃国家推行农业集体化、全家被流放到荒凉的北方时期登上诗坛的。1934—1936年,他完成了长诗《春草国》,讴歌农民只有在集体化中才能找到幸福的生活。此诗符合当时的政策,使他一举成名。
苏德战争期间,特瓦尔多夫斯基写成长诗《瓦西里·焦尔金》。诗人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塑造出一位可亲可爱的士兵的艺术形象。长诗在前线报刊上分章发表时,受到指战员们普遍的欢迎。长诗传到国外,流亡法国的俄罗斯作家布宁读毕倍加赞赏。后来,特瓦尔多夫斯基又写了一部长诗《路旁的人家》,它受到饱尝战争灾难的士兵的喜爱,却遭到某些批评家的抨击,认为他写了战争的痛苦而未表现欢乐。
50年代,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北方严峻的山川、丰富的自然资源、光辉的远景都使诗人神往。他访问了那个地区,写出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
1950年特瓦尔多夫斯基被委任为苏联最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在任四年,发表了不少提倡“*实”的理论文章和暴*暗面的作品。苏联领导集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意识形态的斗争激烈,在*中,他作为一个筹码,被撤掉主编职务。
社会在变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思想也在变化。1958年苏联领导集团中否定历史过去的思想重占上风时,他再次被委任《新世界》杂志主编,发表了一批清算个人崇拜时的作品。
1963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长诗《焦尔金游地府》。这部作品一反《瓦西里·焦尔金》的基调,把过去的苏联的官僚制度比作“地府”,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新的长诗中让战时受伤的焦尔金来到地府,受尽磨难。长诗不待发表已经在知识界传开,此事又引起政界激烈的争论,褒者贬者尖锐对立。赫鲁晓夫予以肯定,反对者认为作者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立场,说:“焦尔金在反对焦尔金”。特瓦尔多夫斯基公开声明:《焦尔金游地府》“不是《瓦西里·焦尔金》的‘续篇’”。他说这部长诗的出现负有另一种使命,主要是讽刺。
1966年,特瓦尔多夫斯基完成叙事诗《凭借记忆的权利》,揭露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1968年在他主编的《新世界》杂志上刊出汉学家热洛霍夫采夫纪实作品《近看“*”》,记述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期间的所见所闻。
在错综复杂的*中,特瓦尔多夫斯基感到难以工作下去,1970年初他离开了《新世界》主编的岗位,一年以后逝世。索尔仁尼琴认为剥夺他的刊物,是使他致命的原因。
如今,他所歌颂的、诅咒的代表人物,还有那些支持他和反对他的当权者,都已成了历史的尘埃。他,正像横卧在这里的顽石,一声不响;而关于他的评论如同那棵橡树絮絮低语。
2006
。 想看书来
喊冤的碑(1)
——弗·梅耶荷德(1874—1940)
1995年,为纪念梅兰芳诞辰100周年,我画了一幅《赞梅图》。画中二十二个人物,除梅先生之外,还有二十一位30年代外国著名艺术家和学者,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洛维奇…丹钦柯、梅耶荷德、卓别林、萧伯纳、布莱希特等人。其中有一位苏联女演员季娜伊达·赖赫(1894—1939)。记得那一年的6月,从莫斯科来了三十多位“人民艺术家”和“功勋艺术家”。他们在梅兰芳故居纪念馆观赏过那幅作品。他们问我:为什么把赖赫画在其中。赖赫与画中其他人物相比,知名度低些,但她的命运令我同情,她对梅先生一片真情使我感动。我作了解释,他们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梅兰芳先生曾对我说过,苏联戏剧家中真正懂得中国戏曲艺术的是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即赖赫的丈夫。他的话使我认真研究了这位杰出的导演的生平。在研究梅耶荷德时必然就联系到他的夫人赖赫。梅兰芳1935年在莫斯科演出时,这对夫妇每场必到,细心观摩,促膝谈心,双方都受益匪浅。
赖赫原是诗人叶赛宁的夫人,后与梅耶荷德结婚。梅耶荷德认为她潜藏着表演艺术才能,如同埋在地里的宝石,只需经过琢磨,即可发出灿烂的光芒。果然,几年之后,她成为舞台上的一颗璀灿的明星。
1935年3月,冬寒正在消退,梅先生率剧团来到莫斯科进行演出。这期间他与梅耶荷德相识。梅耶荷德和赖赫一起欣赏过梅先生演出的《打渔杀家》、《霓虹关》、《汾河湾》和《剑舞》等。还几次出席各方为梅先生举行的招待会。
梅先生则观摩过梅耶荷德剧院演出的《茶花女》和《三十三次发昏》等。
梅先生在世时,我曾听他深情地提过比他年长二十岁的梅耶荷德,称赞梅耶荷德是戏剧界有胆识的改革大家。他很想写篇文章纪念梅耶荷德,可惜未能实现。
有一帧二梅合影,我们从中不难察觉到他们的深厚感情:苍发蓬松的梅耶荷德把头贴向梅兰芳先生,而梅先生含着微笑,热情地握着梅耶荷德的手。
梅耶荷德看过梅先生的戏之后,感慨万千,讲出一段触动人心的话:“梅兰芳博士的剧团来我国演出,它的作用要比我们预料的大得多。我们目前仅仅处于惊讶或是赞不绝口的状态。我们,创建新的戏路的人,之所以激动不已,因为我们相信,梅兰芳博士离开我们之后,我们所有人都会感觉到他对我们产生的不同寻常的影响。”他认为有些导演只知道模仿一些表面的东西,如跨越不存在的门坎,在一个地方既表现室内又表现室外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