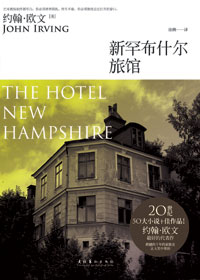白门三代-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少了什么?”
“别装糊涂,少一把手枪!”
这一刀又狠狠地从父亲的背后插入,被捅了个透心凉!他顿时没话可说,一点辩解的余地都没有了。他那两片苍白的嘴唇上下抽搐着,想说些什么,但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哇!”又是半腔子的热血喷涌而出,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两位来人也被吓坏了,她们可能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血,而且是从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嘴里吐出来的,居然就愣住了。
我赶紧将父亲扶起来放到床上,找出云南白药,抠出里边的“保险子”塞进他的嘴里,然后用我那红红的小眼睛狠狠地瞪着那两个操蛋娘儿们。
那俩人也发憷了,战战兢兢地说:“白纪元同志呀,你冷静点,这可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是组织上的建议,你先养病,再好好地考虑考虑,我们过几天再来……”话没说完撒腿就往外跑。
跑到了门口,俩人似乎又觉得不太对劲,其中一个把我叫过去悻悻地说:“你——给我听好喽!回去给你爸好好读读‘八一社论’,让他看清楚形势。别动不动就拿吐血吓唬人!”
那时我还不足十三岁,望着那两个女人远去的背影,我拿把菜刀砍了她们丫的心都有。
对着黑糊糊、空荡荡的楼道,我扯着嗓子带着哭腔地喊了一句:“操你们个姥姥!”
这一次对纪元的打击太大了,也是他吐血最多的一次,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才抢救过来。
在这一年的9月13日发生了“九。一三林彪事件”,晴空里一声霹雳,人们天天祝福“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竟然是谋害伟大领袖的罪魁!就好像天使大声地向众生宣布:如来佛祖最忠诚的弟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刺杀佛陀的元凶”!
人们被惊得目瞪口呆,不要说平民百姓,就是久经沙场的将军们恐怕也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据说曾有人闻此当场惊疯,更有人一下便长病不起。
接下来是“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新一轮的政治运动急风暴雨般地袭来,于是没人顾得上再为逼着纪元“退休”的事情光顾我们家了,老天爷“开恩”,又给了父亲生命中一次喘息的机会。
但是父亲的脑子也彻底混乱了,他感到了一阵阵的迷茫。血还是哩哩啦啦地吐着,从这个时候起,十多年的时间他再也没能正经地工作上班,没人去关照他,也听不到组织上的任何“召唤”,完全蜗居在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直到有一天他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
他仰天长叹:自己的政治生命被自己耽误了,是被这恼人的吐血给耽误了……
我不禁想问:在父亲经历的那些个“杜鹃啼血”的岁月里,我们家为什么怎么总是忧郁?总是不安?总是分离?总是身不由己?
四十岁以后我认识到;父亲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在当时他方方面面都是弱者。健康状况像一根枯萎的小草,政治面貌似一张揉皱的白纸,生命之中充满了无奈和孤寂。
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大声地向人夸耀;夸耀我那羸弱不堪的父亲。不知人们是否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弱者才是值得夸耀的,因为他们有着异乎寻常的坚忍和执著。
。。
最后的遗言:关于党旗
久病的人,就像一只熟透了的瓜果,总有一天是要从枝蔓上跌落下来,被摔得七零八落,最后化为一撮净土,回归大地。这是自然规律,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欢庆九十年代的钟声刚刚敲过,父亲的大限之日就快要到了。
元宵节的那天,也就是五十多年前那位“二大爷”和人打赌险些被元宵撑死的日子,父亲用筷子夹着半个元宵,本想给我们再讲一遍这个让人发笑的故事,以缓和一下家里因为他久病而长年过于压抑的气氛。突然,他沉疴骤犯,大口地吐血不止,他忙用手捂住嘴,血就从他的指缝间淌了出来。他异常镇静地看了我一眼,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在医院的急救室里,父亲一直是昏睡不醒,我片刻不离地守在他的身边。
子夜时分他醒过来了,欠起身子,精神头挺好,血也不吐了,让人看了不禁感到高兴,认为这一关他可能又闯过去了。
父亲饶有兴致地跟大夫搭话,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小儿子,在出版社里当编辑……我还有个大儿子,是党员呢。对,还有女儿,他们都很孝顺。”
那大夫就乐呵呵地说:“老白,您好福气!把病养好喽,回家享清福去吧……”
父亲面色红润,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他抱拳给大夫作揖说:“谢谢您啦,让您费心了。”
说完了他就躺下身来,对我说有点冷,于是我就将被子给他往上拉了拉。
父亲抓着我的手说:“这回病好了以后,你到我的单位去报销的时候,我有个信封你替我交给××,是这些年来在家里学习的‘心得体会’,人离休了,思想不能落后。人家顾不上我,还不兴咱们主动点儿?”
“老爷子,快歇着吧您哪,为这点屁事儿您这辈子的苦还少受啦?”我就狠狠地说。
父亲伸出一根手指头杵着我的脑门儿说:“浑小子!现在是打不动你了,净胡说八道。你爸爸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死的时候能盖上面党旗……”然后他又苦笑着说:“盖上党旗,我就不怕死了。”
我打趣地说:“盖着党旗您可就死不了啦,为什么呀?暖和呗!”
父亲就笑了,在微笑中他又睡着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父亲之死
和以往一样,“大难”即将过去的时候,带来是无限的轻松。我常常想:只要爸爸活着,自己便无欲无求。在医院的楼道里,我来回地踱步,使劲伸了个懒腰,算计着哥哥是不是该来换班了。
忽然大夫把我叫过去,轻声地说:“目前不太乐观,你爸爸的情况可不好啊。他现在不吐血了,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吐了,血都憋在胸腔里,看来我们是回天无力了,你得作好思想准备,凌晨可是个鬼门关呀……”
那刚才呢?是回光返照?!
我不禁悲从中来,抱住大夫号啕大哭,记不住说了多少哀求他的话。但我也知道这已经是无济于事了,所以必须冷静,必须临危不乱,这是父亲教给我的。
家人都到齐了,看着昏睡中的父亲,默默流泪,束手无策。那个大夫的话真不是耸人听闻,的确是医学上的经验,凌晨四点左右,父亲的血压和心电图都开始出现异常,大夫们准备做最后的抢救。这时候我成了“一家之主”,便吩咐家人再最后看一眼父亲,就“命令”哥哥、姐姐将母亲搀了出去,余下来的事情我要一个人打点。
不久,父亲的心电图就完全变成了一条直线——他的呼吸停止了。
大夫把一种叫“心率三联”的强心针给他打进去,父亲的心脏在心电图上“抖动”几下,很快就又没有了任何动静。接下来是最后一招,大夫们给他做人工呼吸,我忽然觉得这样做不好,既然父亲的胸腔里都是淤血,这种“程序”还有什么意义?这不是给他平添痛苦吗?如果他还能有知觉的话。
我把大夫手拦住了,深深地向他们鞠了个躬,泪流满面地说:“谢谢诸位了,你们已经尽到了职责。请让我父亲安静地走吧……”
主治医生似乎为这种通情达理而感动,他摘下口罩,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父亲和你都很坚强,节哀顺变吧,伙计!”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今日得闲
按照回族的习俗,父亲是要土葬的。
他被停放在朝阳门外南下坡的“回族殡葬所”里,那入葬前的最后一夜,仍旧是由我来陪伴着他。
说来也奇怪,1990年的初春,有那么几天是大雪纷飞,雪片大得像纸钱似的漫空飞舞,落到地上就迅速化掉了。望着窗外的雪花,我不大相信会有“天人感应”,但确实体验到了“悲天悯人”。
父亲就这么走了?永远地不再搭理我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哪怕是骂我一句或者是一声让人揪心的咳嗽。父亲生于腊月而卒于正月,才六十岁出头,刚好走完了一个人生的甲子。
雪白的布单罩住了他的躯体,按照习俗我要一根一根地为父亲点香,望着袅袅上升的烟柱,我不可遏止地产生了一种“宿命”感,爷俩昨天关于“党旗”的谈话,竟然就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遗言,可终究也没能享受到这份他盼望了一生的“殊荣”,想来现实竟是如此的残酷,这大概就是“命”吧。
忽然间,我看见灵房里有一块墨绿色的帏帐,那是用来罩在逝者灵柩上的,上边赫然绣着四个金黄色的大字:“今日得闲!”
这四个字让我惊骇不已,这分明是淳朴而又勇敢的穆斯林民众对死亡的豁达见解,甚至是一种赞美,有点像藏族同胞在###的时候赞美那“应召而来天的神鹰”一样……
我这时乖命蹇的父亲,您的一生不能说是活得没有价值,但实在太累太累了,今日方才真正落得清闲。
我被这四个大字感动了。
父亲“入土为安”的时候,来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墓地周围黑压压一片。
我根本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头,只是和哥哥、姐姐一起,不停地向前来为父亲“送行”的人们鞠躬,替我们的父亲向人们道谢。
按照习俗,亡者下葬的时候亲人们是不能哭泣的,人们就轮流着,将一锹一锹纯净的黄土撒向深深的墓穴,呼唤着父亲那已经远去了的灵魂。
就在墓穴即将被填平的时候,大家终于忍不住了,像开闸放水,亲朋好友们顿时哭声四起。这哭声告诉我:从此以后,父亲将永远和我们阴阳两界,天人永诀。
这时在我的脑海里,反反复复地浮现出墨绿色灵帏上的四个大字:“今——日——得——闲”!
于是,心情竟异乎寻常地平静了下来。
记忆西山
就在纪元咳着鲜血,拖着病躯,日夜奔波在北京旧宫公社的农村水利改造工程;就在文英腆着大肚子,坐在老式打字机前,为大跃进时代繁忙的机要工作汗流浃背的日子里,我出生了,那是1958年流火的7月。
火热的年代、火热的激情、火热的天气搅和在了一起。我妈说,一生下来我就长了满身的痱子。
有人问:这孩子应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我爸妈可就费心思了。
按说应该叫“跃进”或“超英”、“赶美”什么的,偏偏姓白的不好这么起名,陈跃进、张超英、王赶美都好,可“白跃进”、“白……”不成,那不是把大家伙的功劳就全都给抹杀了吗?唉!这小东西刚生下来就跟“第二个五年计划”不合辙。
父亲纪元指着襁褓中的我说:看来这孩子没有在大跃进年代里争先进的福分,生就是块白丁的料儿,既然是天亮时分出生,就叫白明吧,这辈子他能活得明明白白就算不错。
另外,我生下来的时候又瘦又小,说不清像一种什么长着四肢的爬行动物。正好有人送给父亲一个偏方,用蛤蚧泡酒据说专治肺病。于是,我爸又给我起了个“别号”——蛤蚧!说完了,他看都不看“蛤蚧”就甩手走了。
据说这时候我睁开了一只粘满眵目糊的小眼睛,偷着瞥了父亲一眼。
按说名字这玩意儿,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符号,自打被书写进户口本儿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这个人具有法律意义的“商标”了。在这“商标”上爹妈要是肯下点子工夫,保不齐日后就能给您家里创造出个品牌儿来呢。
可我爸我妈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不可能有什么“品牌意识”,他们带着某种偏见给我“注册”了这么个平庸的“商标”,于是就注定让我大半辈子,活得是白不呲咧的,还谈得上什么品牌?
每天下午,我母亲这个“超龄团员”都偷着跑回家给我喂奶吃,久而久之就成了不能克服家庭困难的“落后”表现,在入党问题上轻而易举地让别人抢了先。我父亲不干了,两口子心一狠,就把我给扔进了一个街道幼儿园。
那时候的幼儿园可比不了现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一个阿姨带百十个孩子,跟放羊差不多。那个破幼儿园里有个倒霉阿姨,见天儿的把我给捆在床枨上,吃喝拉撒都在眼巴前屁大点的一块地界儿,俩眼睛哭得跟烂桃似的。幸亏我当时不懂人事儿,要不然,非告她虐待祖国的花骨朵儿不可!
还就仗着姥姥每天接送,看着我那“惨相”,老太太急了,跺着脚说:“没人看我看!”便把我打“虎口”里救了出来。
于是,本人这一生的记忆,就从拽着我姥姥的衣襟儿起,一步步地伸展开来……
我们家就住在长安街的边上,姥姥买菜、串门都要带着我。后来可能是因为不方便,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架竹编的破童车,把我往竹车里一搁,再把竹车往马路旁的树干上一绑,老人家就该干吗干吗去了。
嘿,我姥姥个纂儿的!她可真放心,就不怕我被“拍花子”的给拍走喽?
其实您不知道,五十年代的北京,那可真称得上是“黄金时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和人的亲和力还特强。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在开国的头十年,用计划经济打造出了一个让所有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们“回味无穷”的和谐社会。但也有遗憾,就是家里头的早餐,永远是烤在炉台儿上的那几块红瓤白薯。
姥姥每天带我到长安街的边上玩,哄我看马路上的大汽车,她就一边择菜一边和小脚老太太们聊大天儿。
长安街上的那些刷着红蓝两色油漆,努着大鼻子,“突突”冒着青烟的柴油汽车,老半天才过去一辆,我就没了耐心,倒是趴在破竹车里,每每长街西望,但见蓝天如洗,群山延绵。那山近得,仿佛就在我们家的后院,最多是我住的这条胡同的西口儿。层峦叠嶂,郁郁葱葱,迈腿即往,举手可及。
那雄峰百仞,去天一握的西山,让我的小脑袋里浮想联翩:大汽车开到那儿该怎么走?飞过去?我特别想知道是不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于是就闹着要进山,我姥姥自然是不答应,于是祖孙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