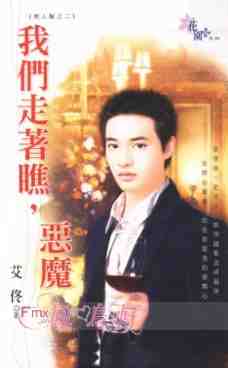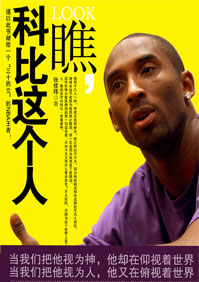瞧,这人-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告诉他我近来的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作番事业。”他的原信也
附在此册里,以记吾过,并记吾悔。
记过、记悔,这悔过是否与“gay”有关呢?看来,胡适的性情还颇不易测。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 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1)
还是在19世纪中叶,美国为了扩张自己的疆土,发动了美国墨西哥之间的战争。1835年,墨西哥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两地的美国移民发动武装叛乱,墨西哥政府出兵镇压,美国则直接出兵干涉,并支持得克萨斯于次年宣布独立。1845年7月,美国正式宣布把独立后的得克萨斯并入自己的版图。次年,美国政府又正式向墨西哥宣战,顿时美国军队犹如闯入墨西哥玉米地里的一头黑熊,只不过这头黑熊看重的不是玉米,而是大片生长着玉米的肥沃土地。战争结束后,美墨两国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和约,该和约将大片墨西哥土地割让给美国。它包括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犹他等州,以及亚利桑那、怀俄明、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的部分地区。五年后,美国又从墨西哥购买了一块带状的位于现在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土地,于是便完成了现在的西南部边界。
“自美墨交衅以来,本城之‘Ithaca Journal’揭一名言:‘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言意但论国界,不论是非也。”这段话的英语表述约略是“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简直就像格言一样。原来,70多年后,美墨之间,争端又起。那边毁了美国星条旗,这边美国就派遣水兵在墨西哥上了岸。这时康大所在小城的“绮色佳杂志”把上面的“My country”一直印在社论篇首,它当然不止表示了这家杂志的态度:不管自己国家行为的是非,它总是自己的国家。这样一种明显的“国家主义”言论,在杂志上“已逾旬日,亦无人置辩”。胡适自大二开始就居住在康大新盖的世界学生会的宿舍,对这句话,宿舍里面的各国学生倒是议论纷扬,有人认同,有人反对。胡适“聆其议论,有所感触”,便写了一篇文章投给这家杂志,杂志最初不敢登,后由某女士的坚请,始在新闻栏以报道形式出现。胡适拿着自己的文章去见康大前校长白博士(夫妇)。白博士(Aadrew Dickson White)六十年前读耶鲁时和中国第一个留美幼童容闳(纯甫)是同学,至今他还记得容闳异服异俗的样子是如何颇受人笑,但那一年容闳两次获得全班中英文一等奖,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揶揄他了。白博士夫妇都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很讨厌那种不论是非的狭隘国家主义,因此,读毕文章后,白夫人称赞了胡适,认为他说出了自己正要说却还未及说的话。
那么,胡适在文章中到底表达了什么看法呢?
我以为此谬见“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之所以为然,是因为有两个道德标准。人人都不反对万事皆有一个对错及正义与否的标准,至少文明国家应如此。假如吾国违宪向吾征税,或非法将吾之产业充公,或未经审判即将吾入狱,吾誓必力争,不管其是否以“吾国”法律之名义行此事。
然而涉及国际间事,吾即放弃那个对错和正义与否之标准,且颇自得地宣称“是耶,非耶,终吾国耳”。以此观之,余以为吾人奉行道德的双重标准,其一用之于国人,另一用之于他国,或“化外之民”,余此说不亦对乎?余以为吾人不管国内国外只应奉行一个是非标准,否则无法争论此事。
以上是胡适1914年5月15日的日记记述。
插:今天国人中常有批评美国“双重标准”者,岂不知,早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胡适就揭橥了这个问题,也使用了这个词汇,那时他还是个学生。作为学生的胡适,他对自己率先提出的这个词也很自得。次年他赴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出席世界学生总会,会上,一位著名演说家的讲演颇唤起他的共鸣。这位“时彦”讲演的是“论全球政治”,其中也谈到“双重标准”的问题,胡适在日记中惺惺相惜:这位博士声称“今世国际交涉之无道德,以为对内对外乃有两种道德,两种标准。其所用名词‘双料的标准’(Double Standard),与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词以为独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几欲自夸‘智者所见略同’矣。”
十 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2)
胡适是个世界主义者,同时也爱自己的祖国。他的世界主义也就是他前此一个多月在演说中表达过的: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这次他亮出了对美国人的批评的旗帜。两个月后,他在又一次讲演中再次表达了自己对那种狭隘爱国的批评,演说后,有两位听众对胡适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一位夫人认为:这句话(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的真实意思不是“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而是“无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这位夫人的解读不可谓无道理,也能理解她对自己国家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不顾国之是非,而仅仅就因为它是“My country”,我也只能说,这是旧农业文明时代的感情了。然而,这种感情同样表现在下面这位美国教授的身上,他耐心地给胡适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兄弟一道出行,弟弟因为醉酒而有辱于路人,对方如果拔剑而起,那么,做哥哥的是保卫喝醉的弟弟呢,还是置之不顾呢,抑或帮助受辱者?这个教授其实也是在表达他对“My country”的理解,他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但,无论这个并不伦类的例子,还是他的结论,都难让人苟同。兄弟是血缘,而个人与国家并无这种关系,这个比喻是跛脚的。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出生地并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国而论,任何人如果在美国出生,就可以是美国人,而他的父母却可能不是。同样,一对美国夫妇也可以收养一个他国儿童,只要儿童的父母或国家同意。因此,把“My country”视为“父母之邦”,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状况。何况,即使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古老的《诗经》还有“适彼乐土,誓将去汝”的意识。更何况,依这两位北美人士的说法,又何以解释他们的先辈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本邦而来北美?这分明是“誓将去汝”的跨国现代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用脚投票”。它的精神内涵应当这样表述:“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可是,胡适似乎被侃晕了,听了这两位先生女士的开讲,便在7月26日的日记中做了自我检讨:“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
其实胡适是对的。他反对的不是爱国,而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隐含是:对内,它把国家凌驾在个人之上;对外,它把国家凌驾在他国之上(这种国家主义经常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相当能迷惑人,是当今世界中最为可怕的力量)。至于那句“My country”,既可以做爱国的解释,也可以用作国家主义的表达,端视语境而定。由于胡适放不下这个困扰他的问题,就在当天,思考之中,又写下了第二篇日记。日记中,胡适虽然声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这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反过来,爱国之心又能否胜是非之心呢,这又是一个问题。胡适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态度却可以从下面的内容看出:“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 一个“拳匪”,表明了胡适对义和团的态度,也是胡适是非之心的表现。从胡适这一段曲折来看,他固然爱他那个国家,但终究是非之心大于国家之心。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者。
毋庸讳言,笔者欣赏胡适的,便是他作为一个具有人道之念的世界主义者。成为一个国家主义者也许不难,它很可能是一种自然;而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则需要超越这种自然,更需要超越那种可怕的国家主义。四个月后,胡适就此问题又写了一篇日记,名为“大同主义之先哲名言”,日记中胡适除了抄录先哲关于“世界公民”的名言,并无一句自己的话:
亚里斯提卜说过智者的祖国就是世界。——第欧根尼·拉尔修:《亚里斯提卜》第十三章
当有人问及他是何国之人时,第欧根尼回答道:“我是世界之公民。”——第欧根尼·拉尔修:《亚里斯提卜》第十三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 世界公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3)
苏格拉底说他既不是一个雅典人也不是一个希腊人,只不过是一个世界公民。——普卢塔:《流放论》
我的祖国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T·潘恩:《人类的权利》第五章
世界是我的祖国,人类是我的同胞。——W·L·加里森(1805…1879):《解放者简介》(1830)
“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我是世界公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响亮的声音之一,这样的声音穿越时间的隧道而经久不衰,放在今天,则更见它的现实意义。
十一 “自由政治者之大枢纽”(1)
1912年大选时,胡适的支持者是老罗斯福,当选的却是威尔逊。后来威尔逊的进步主义和理想主义打动了胡适,还没等到1916年大选,胡适就已经改从威氏了。
这是1914年7月12日的日记,胡适扼要记述了一前一现两位总统的演说:
“下所记威尔逊与罗斯福二氏本月演说大旨,寥寥二言,实今日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枢纽,不可不察。威尔逊氏所持以为政府之职在于破除自由之阻力,令国民人人皆得自由生活,此威尔逊所谓‘新自由’者是也。罗氏则欲以政府为国民之监督,维持左右之,如保赤子。二者之中,吾从威氏。”在日记的最后,胡适把抄录下来的两位演说大旨作了翻译:“你到底赞成谁?罗斯福先生在匹兹堡演说:政府要监督和指导国民事务。威尔逊先生在斐城演说:政府应为国民创设条件,使之自由生活。”
这是一篇有关自由的日记,胡适对自由学说的涉及,最早是在上海的澄衷学堂,那时14、5岁的他接触了由严复翻译的密尔的《论自由》,尽管书是看了,但估计那时的他不容易理解到底什么叫“群己之权界”。来美后的胡适自然不难于再度接触这部自由主义的经典,我们看到,这期间胡适不止一篇日记留下他阅读密尔的痕迹。1914年10月,胡适先后和韦莲司及康大的讷博士谈及伦理问题时,胡适的观点是“一致”。当讷博士问胡适:“今治伦理,小之至于个人,大之至于国际,亦有一以贯之之术乎?”胡适对曰:“其唯一致乎?一致者,不独个人之言行一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孔子所谓‘恕’也,耶氏所谓‘金律’也,康德(Kant)所谓‘无条件之命令’也。”胡适和讷博士讨论的问题不意竟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繁难对付的问题,或者,这个问题早在百十年前就困扰美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固然是“恕”的一种表达,可是在孔子那里,它还有另外一种表达,即“己欲立而立人”。这是不是说,自己站了起来,也一定要使别人站起来,假如别人想蹲着呢?比如美国是自由国家,它可以不可以哪怕是用战争手段逼那些不自由的国家也自由,是所谓输出自由。这是一个极为麻烦的问题,谅年轻的胡适虽然有兴趣,这个问题也行之无远。日记最后,胡适继续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排比为“斯宾塞所谓‘公道之律’也,密尔所谓‘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也。”
打住一下,不妨把胡适和鲁迅对自由的表述放在一起比对,这或许是一件有意味的事:
“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
“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第一种自由姓胡,它是自由主义的;后一种自由姓鲁,它是反自由主义的。天下自由不一家,于此可见,以后切勿一见自由就亲亲热热地说是自由主义。要而言,自由主义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权界”的(即权利的界限),一位美国###官说得形象:你有挥舞手臂的自由,但必须止于别人的鼻梁之前。鲁迅的自由是随心所欲的,绝对的,它没有任何权界的自律。其后果,是你有了挥舞手臂的自由,但别人的鼻梁却不免遭殃。因此,在比较的意义上,胡适的自由是“每个人”的自由,而鲁迅的自由是“一个人”的自由。1914年胡适对自由进行表达时是23岁,1907年鲁迅表达此一自由时是26岁,都是年轻人,但留学背景不同,汲取资源有异,所以以后,胡适成了个自由主义者不奇怪,就像鲁迅走上反自由主义的道路也不奇怪。
以上是个插曲,如果回到胡适当时语境,他把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解释为密尔的“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为界”,毕竟有所差池。一个是叫你不要做什么,一个是要你做什么时需要注意什么,两者论述的情况不一样,也对不上。
稍前于此,胡适另有过一次大谈自由的机会。那是胡适往游哈佛时,哈大留学生孙恒来访,两人谈兴正浓。孙恒认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国人“不知自由平等之益”,而这是“救国金丹”。但胡适听了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病不在于无自由平等之所说,乃在不知诸字之真谛。”这层意思固然好,很显然,以上胡鲁各论自由,其中一个就不明自由的真谛所在。但,哈佛的孙君却未必不明白,毕竟人在美国,自由主义是感同身受。胡适是否自我发挥了。在胡适看来,今人所持的自由平等,已不同于18世纪学者所持的自由平等了。比如平等,18世纪只是“人生而平等”,但,“人生有贤愚能否,有生而癫狂者,神经钝废者,有生具慧资者,又安得谓为平等也?”因此,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