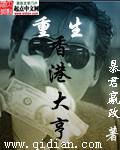香港电影夜与雾-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晰可寻。尽量选取生活细节片段,回避简化的立场选取,对白不多,却统统指向一致的世界观,由主观的视觉效果到外在的环境建构,想带出的讯息始终离不开无奈羁困。是的,那不仅因小嫣的背景设定而生——综援家庭,一室小孩,猪朋狗友满街,吸毒堕胎等,当然都可以成为想当然的基本框架。但导演所选择的表现手法,基本上正好是以错位的反讽来增添无奈的气息。《墨绿嫣红》的青绿色调当然人尽可见,那也可以看作小嫣的主观视觉,在她眼中一切环境均离不开惨绿色调基础,而且同时亦以刺耳的杂音作为另一提示的指引,以便观众可以投入到小嫣的身体及精神状态中去,呼应吸毒的物理效果设定。但以上扭曲强化了的感官表达手法,显然与外在漠然的人事气氛出现明显的对倒,周遭的一切“正常”不已,简言之可谓完全不把小嫣心中的起伏波浪看成一回事,生命自然而来人为而去,仿佛也不过是循环安排的一部分,两者对照之一反讽的张力当下立即构成。
此所以惨绿世界的瞩目景观,固然为小嫣对绿胎儿的包袱投射心影,但更重要的,是身边没有任何人对小生命有相若的心债。友人只顾插科打诨,较投契的亦只会协助张罗堕胎药物;老师连小嫣珠胎暗结也懵然不知,关心的只是母亲的来校与否;外祖母以两粒橙六根香为两小亡魂引路西归;楼下公园继续代有青春孽障,下一位小嫣子已极速成形残酷流逝。导演对刻下现世的无奈,大体上都是记录手法呈现,尽量避免主观角度的介入,不过有时偶尔也糅渗一鳞半爪的蛛丝马迹。我觉得最明显的点墨在夜静的两场戏——前者为小嫣与一众友人在楼下公园高谈阔论共度时光,友人嘲讽即使找到售货员的工作,最终亦会陷入滥药迟到失职的窠臼,然后被解雇再求职不断重复,未来人生早在眼前。后者是小嫣同校学妹补习后回家,在大堂楼下与小嫣开始共处,结果由升降机到走廊继续一起,最终开门前学妹与门后的母亲简单应对两句,两人才告分手作结。学妹作为全片中几近唯一的“正面”人物(有镜头交代她认真应付考试,而且也会补习到夜晚),俨然作为密封环境中另一出路的象征符号,但导演所下的界线正是母亲的一声照应,从而分隔了左右上下的区别。现实的无奈困惑,正好在背后的稀薄空气,存在感之丧失构成了眼前的失距。没有人紧张小嫣,小嫣选择不让孩子出现来折射出她所紧张的,什么来什么去,世界照常运作,太阳继续东升,痛后不死就仍要活下去。
我当然明白导演的谨小慎微,是他一贯的稳重作风。而我冀求导演的“介入”探究,也可能仅属一厢情愿的期盼——原因很简单,其实《墨绿嫣红》连青春的躁动激情也收敛了。它没有《香港制品》的坟前起舞,也没有《烈日当空》暴烈奔驰,连小嫣也成熟“守规”到令人心寒——是的,由开始的更衣上学,到熟练地买药上电,乃至回校应试,即使精神涣散而撑不下去,也没有麻烦到身边人事。最终更自觉地回家面对堕胎的抉择,我们其实应该可喜——因为社会成功地育成了如此尽责守规的不良少女。她从一开始就连任何反抗叛逆的激情也没有,那是非常不青春电影的表现手法,但却是非常香港的地道青春心境——未尝青春早老死。如果这是导演的世界观,则才是最残酷的青春物语。
第54章 如何理解“视觉过剩”?
——以黄精甫为案例分析
看《复仇者之死》,不禁想起彭丽君近著《黄昏未晚——后九七香港电影》中,以“视觉过剩”的概念来分析黄精甫的专文。我相信由黄精甫的短片开始,大抵没有什么人会反对黄精甫的作品,视觉效果一向大于人物的感觉,此所以彭文分析《江湖》及《阿嫂》均以出现人物为视觉附庸倾向,也确属中肯之见。只不过对作者为黄精甫“失败”作寻找美学上的解说,从而表达个人独有钟情的感受,我又觉得不妨延伸来一次对话。
彭文为黄精甫重“视觉”弃“叙事”的创作策略,尝试提出背后可能的美学基础,而且以录像艺术家的例子为证,反映出叙事性已跟意识形态挂钩,“故事”则被视作为表达情感及建立价值的工具,于是主攻视觉以用作反对叙事性,也可成为抗衡全球文化霸权的策略之一。录像艺术家对叙事性抗拒的风气固是实情,但我认为不宜作为铺陈背景去引导读者循此方向去解读,最重要的原因是黄精甫即使由实验性的短片开始,其实从来都没有呈现出抗拒叙事的倾向。而他迄今被一致认为最成功的代表作《福伯》(与李公乐合导,2003),更是视觉形式与叙事内容(父子由对立到同体的复杂探究)精准结合的上佳示范(黎德坚编剧)——他其后作品的“视觉过剩”,不过说明在叙事元素掌控上的力有不逮,而非一种自觉的美学探求。叙事上的苍白贫乏,彭文通过《江湖》及《阿嫂》的例子早已书之甚详。事实上,在日后的《十分钟情之清芳》(2008)及《复仇者之死》(2010),我们反复看到的都是叙事元素与视觉形式的错配。前者的南丫岛爱情小品,导演一直以唯美的摄影去回避发展人物的叙事性关系,于是开始时的亦幻亦真,又以充满疑团来告终,观众共同经历了一场在原地踏步的影像之旅。后者更放肆地无视一切现实上的叙事逻辑,然而又渴望通过不断互相杀戮及报复的安排,从而带出人性及神性的讽喻,那显然就是自我作弄的矛盾演绎,破腹取子的血腥镜头俨然在自我嘲笑以上不成形的概念早已胎死夭折。
彭文通过对《江湖》中Turbo被人毒打甚至强迫与狗性交的场面,来说明黄精甫不惜违犯观众的视觉原则,来建构一个不可能的镜头位置——“电影中所强烈显示的作者在场,跟任何类型片标准或观众认知的欲望都不会妥协。”我想借此指出,黄精甫的“视觉过剩”先建基于无力平衡叙事性及视觉风格的失衡,复陷于对“作者在场”的视觉风格误判偏差,于是才处于现在的尴尬处境——既无力在艺术层次杀出一条血路,也未能融入商业市场扩展存活空间。彭文所指出的一幕,揭示了导演企图通过破坏现实上的视觉常轨,来强调自己的存在价值。这一种以片段式及场面式的标签理解,反过来恰好说明创作人无力统御全体,贯彻风格的缺憾。讽刺的是,以上所谓“视觉过剩”的创作风格,其实在香港电影的系谱上从来不算新鲜,由桂治洪的愤怒至死到黄志强的火气迫人,全都鲜活地明示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的本土特性。然而值得反省的是,以上导演呈现于视觉风格的癫狂表现,其实均以统一风格及意象来贯彻实践,而当中的叙事元素容或单薄粗疏,却坚守相辅而非相乖的原则来建构。当今天影迷对冢本晋也《铁男》(1988)的金属科幻美学趋之若鹜,黄志强早已在《打擂台》(1983)示范了拳脚武侠与烂铁烂铁科幻crossover创意惊人的尝试。桂治洪对暴力、色情乃至灵幻的“视觉过剩”表现,几至俯拾皆是的地步,但背后贯彻的仍是对宿命观的展现,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无政府主义狂态反悖,从而去成就一个又一个挑战宿命的愤怒英雄面貌。简言之,视觉风格从来不用与叙事元素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尤其在商业类型片的范畴下,“有前无后”差不多属一条自杀的不归路。更重要的是,视觉风格的审定,从来以全片整体作统一环视,“有句无篇”也不可能成为褒词。
回过头来,我其实也是对黄精甫情有独钟的一分子。不过我选择否定他对“视觉过剩”的影像诠释,从而去召唤《福伯》中精魂重生的黄精甫——这大抵就是本文的目的。
第55章 cult film的前世今生
——由《维多利亚壹号》或《复仇者之死》谈起一、“纯真cult”与“故意cult”
2010年有两出摆明车马以cult film包装的香港电影面世,分别为彭浩翔的《维多利亚壹号》及黄精甫的《复仇者之死》,凑巧2011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又以桂治洪为焦点导演,我想起若从cult film的本土脉络出发加以并观,或许可带出另一重分析趣味来。
今天的观众入场观看《维多利亚壹号》或《复仇者之死》,我相信与欣赏桂治洪的任何一出作品,均会有截然不同的感觉。是的,它们同属cult film大家庭内的产物,洋溢着B级片的风格趣味,造作及夸张的影像美学,对性与暴力的执迷等,的确主宰了整体面貌。当然,我自然明白cult film的特色,从来就难以划定固有的疆界,也正因为此,它才可以在一个又一个小圈子中被推崇出来成为热捧对象。从方法学来说,cult film的建构形成,本来就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定性判断,指涉评价层次,此所以今天把过去的电影审定为cult film,举动自身已属美学归类上的审美活动——换句话说,旧片中的cult性是被“发掘”出来的,而非“创造”出来的。但随着时日的推移,创作人亦已把无意识而成的cult性,转化为因应cult film类型化特质而成的前设考虑,也即是衍化为一种后设的美学。从这种更易变化而言,cult film本来已逐步“发展”成为类型片之一,与武侠片、动作片又或是喜剧等相若,同样拥有类型片的特质而存在。
二、由camp到cult
在此我想借用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名篇《坎普札记》(“Notes on Camp”)中的一组观念,来延伸以上的讨论。她把坎普区分成两类,一为“纯真坎普”(naive camp)与“故意坎普”(deliberate camp)——前者指涉天然而发,无意识之下所营造出来的坎普美学;后者则是有意为之,蓄意而成的坎普美学。那正好与上文提及的cult片的建构进程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我甚至打算挪用划分出“纯真cult”与“故意cult”的两端。在桑塔格的分析中,她不讳然认为“故意坎普”难以取得“纯真坎普”的相同力度,乃因为坎普而坎普的举动,通常结果都难以令人满意。当然,我并非打算盲目地以信奉权威的方式,把她的判断移植过来奉为圭臬,但也想趁机指出“故意cult”较“纯真cult”,的确会有较大的约制及局限在内,令到为cult而cult的创作人,所面对的挑战及难度委实更大。
回到文首所提及的例子。桂治洪、彭浩翔及黄精甫的作品,明显地都具备相若的表面特征,从主题上出发,彼此的反社会性本质均昭然若揭。桂治洪则可谓逢权力必反,无论是警方又或是黑帮也不例外(可参阅拙文:《宿命背后的泄愤历程》);彭浩翔反击地产霸权;黄精甫则对警权及神权加以批判。由影像风格而论,大家对暴力及色情的镜头均毫不吝啬,桂治洪在《愤怒青年》的鱼枪贯腹又或是飞车搏击均看得人血脉沸腾,至于女性肉体横陈的场面差不多无片无之;彭浩翔就曾国祥及周俊伟的室内戏,也大洒盐花及血浆;至于黄精甫的剖腹报复乃至苍井空的被强暴场面,同样毫不留手。此所以的确容易方便地通过既定的cult性来把他们分类归档。然而我想指出的,以反社会作为焦点导向的cult片,始终与纯粹环绕二手文本出发的后设游戏有所不同——就以“搞乜鬼夺命杂作”(scary movie)系列为例,它可以纯粹在一个自设的密封世界里,让观众投入其中享受自我圆足的乐趣。然而在以反社会为主题的cult片中,虽然电影仍属一密封的世界,但戏院以外的现实氛围,其实也左右及影响了观众的期待视野,从而令人产生不同层次及程度上的快感。
三、时代环境的“人为”以外要素
大抵没有人怀疑用过火及巅狂来形容桂治洪的作品,会有任何偏颇的地方,甚至以“火气四溢”来定性也毫不夸张。然而在导演极力夸张渲染至令人几近难以接受的影像背后(我偏爱的《香港奇案之二:凶杀之临村凶杀案》中,韩国才饰演的哑巴被反复欺凌的场面,差不多以挑战观众的忍耐极限为拍摄目标;至于片末出现以死人之瞳孔视角,去环视麻木不仁的周遭反应,导演更钟情至把源自《愤怒青年》的设计来一次自我复制),观众能够在电影院内“忍受”文本的折磨,其实与影像生成的社会时代不无关系。1966年九龙骚动及1967年的本土暴动后,踏入70年代的香港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转折期。1973年出现大股灾,而1972年至1975年又是香港商业大萧条的时期;社会上黑白难分,此所以1974年廉政公署的成立才得以被视为本土大事。桂治洪的《愤怒青年》、《蛇杀手》、《成记茶楼》及《大哥成》等一系列反社会的cult片代表作,背后其实有浓厚的社会气息,去支撑文本虚拟世界中的巅狂演绎。此所以作为“纯真cult”的片目,文本世界中的一切,其实有源自影像以外的现实氛围去导引我们投入当中。
由此而省思,上文提出“故意cult”的难为之处,乃创作人即使可以完全控制文本内的世界,但影像以外的一切很明显并非可“故意”为之。当然,《维多利亚壹号》提出的地产控诉,以及《复仇者之死》对警权的不信任(2008年也曾发生警员在旺角警署强奸市民的严重罪行),固然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支持。但电影中为丰富电影的cult味,而设计出来的巅狂情节及影像,与现实中对地产霸权的憎恶以及警权的反感,显然仍有一段感知距离。更重要的是,桂治洪在影像中所提倡的以暴易暴伦理,的确击中并勾起了观众的民粹快感。然而反过来,在千禧年后的今天,利用以暴易暴作为“故意cult”化的一种手段,就似乎反过来受“类型”制约所限制,多于可以汇通时代气息,而去寻找出一种属于今时今日的反社会“故意cult”化伎俩来。
第56章 《一国双城》的擦边球美学
张经纬的作品,常予我有擦边球的感觉。《音乐人生》由精英到反精英,《墨绿嫣红》由反吸毒到展示远远更复杂的青春物语,都是一种借力打力的摄制方法。我们都明白于今时今日,没有一个特定的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