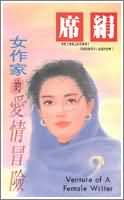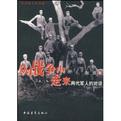对话著名作家-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邓一光(3)
我的成长期处于变革和动荡之中。我在少年时代几乎没有看到过安静的微笑,身边的人总是忧心忡忡,互相攻讦,包裹在厚厚的面具里,让人无法接近和信任。书本给我带来了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故事是虚拟的,小说旨在想象,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知道人有幻想的要求和能力,那些幻想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命与生俱来的权利,但书中世界的丰富和暖意对冷漠的现实世界的间离效果是起到了。从此我相信了一件事——看到的一切不是一切,还有另一个一切、若干的一切在不知道的地方,它们可以从书本中找到,可以在放下书本之后靠着想象找到。
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当了知青。那个年代,书本已经遭到过浩大的清扫,几乎已经无书可读。我从城里带到乡下的书,除了一本没头没尾的《牛虻》和几本《星火燎原》,就是知青办发的一套马列经典著作。那本《牛虻》为我带来了很大的名气,不断有知青来借,甚至有不认识我的知青,只知道我是“那本《牛虻》”的主人,大老远地跑来借,借去了也都准时还回来了。因为书没头没尾,我自己给书做了封面,有两三次,书还回来时换了新的封面,还给画上了人物肖像画。那段时间我开始生吞活剥地读马列著作,《资本论》和《反杜林论》我读了好几遍,根本没有读懂,能背一些文字激烈的段落,每逢和人辩论时就拿出来用,常常很管用,一招置对手于死地。
有一次,我发现大队榨面房里收了一些农民家里的旧书,用来包挂面,我就拿马列著作换回旧书,等“马列”换完了,就拿麦子换。我下乡的地方是山区,土地稀缺,粮食匮乏,吃不饱饭,一年分六七十斤麦子、一二十斤谷子,剩下的就是红薯土豆了。拿麦子换旧书时很心疼,还委屈,肚子里咕噜噜地叫。那段时间最恨的就是挂面,觉得要没它们书就没人要了,我能白得。
有一次,一个农民告诉我,生产队付会计家中有“古书”,我知道后就找付会计。付会计是我在队里最尊敬的人,他和他家里人很善良,还斯文,衣裳补丁摞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说话笑眯眯的,从不说粗话。付会计带我去他家,从箱子里翻出十几册书。书是线装本的,纸页焦黄,有《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庄子南华经解》,还有《又玄集》。我一本本地找付会计借,看完还去再借别的。后来付会计把那些书全都送给了我。那些书在煤油灯下伴我度过了四年,从农村回城时我什么也没带,就带上了那些书,如今它们仍在我的书柜里。
我当工人那几年,“*”结束了,图书逐渐解禁,新华书店里偶尔会有一些新书卖。新售的书品种少而又少,每出一种,人们奔走相告,连报纸都提前登载新书出版的消息,用很显眼的字号。新华书店比总理府热闹,谁认识书店员工比认识外星人还不得了。每当新书首发当日,我就和同事约好,谁当天不上白班谁起早,凌晨去书店门口排队。我排过两次,买的什么书忘了,有一次凌晨两三点钟去,前面已经排了几十个人,到天亮后书店开门,一个挨着一个往前挪,挤出一身臭汗。第二次不到两点去,仍未排到头十名。售书数有限制,好像每人不得超过三册。书店员工大声呵斥,比宪兵还厉害。有人在书店门口打架,有人当场生病,有人因排队买书恋爱上。现在想起来十分荒唐,可那个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荒唐,觉得挺正常的。
邓一光(4)
那时的书价便宜,我手中一套《契诃夫小说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每册定价在四毛二到五毛五,二十册没超过十块钱。
手抄本是早些年就流行开了,我读过一些,《第二次握手》之类。印象最深的是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字抄得娟秀,工工整整,老厚一摞,读时老怕把纸翻破了,要小心翼翼。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手抄的《飞鸟集》,我一直珍藏着。
那个时候读书很疯狂,每到手一本书,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说贪婪一点儿也不为过。书读得很快,不快不行,每本书后面排好几个人等着,要想得罪人,不用向人借钱或借钱给人,超期两天不还书,下辈子都是仇人。读书读到凌晨这种事常有,读乏了用冷水冲头,还写读书笔记,那叫饿急了,撑死都满足。
以后的读书经历就没有这么激烈了,书越来越多,自己也挑剔了,反倒觉得少了一些什么。说不清。我的读书习惯
书是生活必需品之一,如果不是旅途在外,基本上每天都会读,但不像一日三餐那么刻板,什么时候想读了,抓起来就读,有时读到打盹儿,也不硬把眼皮子支起来,书丢下就睡,或者起来去干点儿别的,把书忘掉。
到手的书未必读完。大多数书读不完。没兴趣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读书从不在书房里。曾经在书房里放了一把躺椅,读过几次,没意思,而且老分心,觉得书房里别的书都在骚动,它们挺不耐烦的。以后就把躺椅搬出书房,也不在书房里读书了。
只在一种情况下坐着读书,旅途中,否则一定会躺着读。我主要读哪些书
这是世界上最傻的问题。读什么书,视阶段而言。基本由着性子。比如前些日子,对心理问题感兴趣,读了班克特的《东西方心理治疗的历史》、罗杰斯的《个人形成论》、恩普森的《眨眼与做梦》。比如再前些日子,看法布尔的《昆虫记》在书柜里歪着,替它整理齐,随手抽出一册,是说红蚂蚱的,站在书柜边随手翻,读得开心,又抽了两册放到枕边,那几天连读了好几册。
书读得很杂,难以归类。小说反而不似十年前那样热衷,少量的国外小说会看下去,最近读过的有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普鲁的《船汛》,施林克的《朗诵者》。遇到曾经读过的旧小说,读进去了,也会再读一遍。读书生活对我的启示
说不上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吧。除了生命,没有什么事情会是一辈子的,或者一辈子意义不变。读书也是这样。但相信一点,有的书你读过了一辈子不会忘,但不等于它不变,再读一遍,会发现它变了,不是老朋友了,是新朋友。我不喜欢的书
图书种类中的大部分基本没有涉猎或者完全没有涉猎,喜欢的方向窄,由此导致不喜欢的方向也窄。就我读到的有限种类中,传记是不大喜欢的。可能有不错的传记,比如传主自己所作。大多数传记作者远离传主,自说自话,内容取自传主,却让人觉得那是在写作者,读这一类书实在是受戕害。
对话邓一光
仰望星空,放飞心灵
杨建兵 邓一光
杨建兵(以下简称杨):您在当代文坛已耕耘二十余年,在多种题材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提起您,读者首先想到的可能还是《我是太阳》和《父亲是个兵》,把您归入军旅作家之列。我们的话题也先从军旅开始。首先想请您谈谈您为什么以军旅或者说战争为背景来展开您的文学之旅?
邓一光(5)
邓一光(以下简称邓):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访谈者头一个就会提到的问题。我感到奇怪,这个奇怪不在于访谈者们关心的问题为什么那么一致,而是我对访谈者们“军旅作家”的界定弄不明白。“军旅”这个词我明白,《辞海》上的注释很简单,就是军队,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军旅作家”这个提法我一直没弄懂,是指身为军人的作家呢,还是指以“军队”或“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如果“军旅作家”指的是身为军人的作家,这种说法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但我不是军人,自然不在之列。如果指的是以“军队”或“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为题材进行写作的作家,问题就出来了。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罗贯中、施耐庵,他们的作品写的是“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苏轼这些诗人词人都写过军队和战争,连鲁迅的写作都涉及过军队和战争的事。西方作家包括塞万提斯、歌德、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你把文学史上所有熟悉的作家名单排出来,好像没有哪个作家的作品没有涉及过“军队及作战之事”,连罗琳的哈利?波特都在进行另类的魔法战争。是不是他们这些作家,包括《诗经》、《左传》、《史记》作者在内的所有作家都属于“军旅作家”?
“军旅作家”是狭隘的体制规定下带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界定,存在严重的概念模糊和混淆错误,你的问题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无法回答。我只能这么说,战争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姿态,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灾难和原动力。战争情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我的重要构成之一,它让我充满了个人述说的欲望。
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林海雪原》、《红旗谱》、《红日》、《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一大批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代表着当时文坛的最高成就,有评论家认为它们是后代作家难以企及的现实主义创作高峰。我想知道这些作品是否对您的创作产生过一定影响?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的?
邓:我在少年时代读过《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另两部书没读过,但看过同名电影。我被这些小说和电影深深地打动过,为小说和电影中的人物遭遇流过泪,不光创作,就连我最初的世界观都受到过这一类小说和电影的影响。
这一类作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是单线的,主张二元对立的善恶观,无一不张扬对信仰的追求、真理的坚守、道德的完善、人类大同世界的赞美,与一个多数人赢得生存权的变革时代形成互文,适合那个年代渴望世界具有透明度和热情的读者比如我的阅读。在缺乏其他题材作品的年代,它们占有着文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有一种阶级立场指导下特有的神秘感、颠覆动力、苦难意识和担当精神。关于神秘感,我想到了上世纪中叶从事大型计算机运作的那些程序员,他们试图以机器的符号演算方式代替人的认知方式,创造了二进位制的语言。这些人在当时被人们看做怪物。关于颠覆动力,这是阅读最有力量的元素之一。关于苦难意识和担当精神,这是中国文化长期缺失的高贵品质。你说的这些作品也是一种充满力量的二进位制语言方式,以及用这种方式书写的时代叙事,它们在一元化时代建立了一种全民的文学观。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邓一光(6)
我在这里对你有一个小建议,不必把这些作品硬拉进“军事题材文学”的小圈子里,这样的视角无益于你的研究工作,譬如不必蹲在树木里观察一群鸟儿,你也可以去溪流旁、山峦上、大海边,甚至天空中,你在那里也能看到它们,而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才是它们真实的生活。
杨:塑造悲剧英雄是您战争题材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也将您的作品与《林海雪原》等区别开来。不管是《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还是《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他们都是英雄,又都是悲剧英雄。您如何看待英雄主义?又如何理解英雄的悲剧?是否可以说英雄本身就是悲剧?
邓:英雄(hero)这个词最早源于古希腊神话,它含有三个意思:一是半人半神或非凡的人,一是悲剧和史诗的主角,一是统治者。英雄的悲剧性不是由“英雄”的词根决定的,而是由英雄自身的构成以及与时代的冲突这一性质决定的。具有天赋才能、卓越超群、代表着神的意志的英雄,他们始终处在颠覆旧文明和建构新文明的历史选择上,也处在如何把握自己颠覆旧文明和建构新文明的双重能力上。英雄具有警示时代、创造时代和奴役公众的几重欲望,以及在这些欲望推动下永远不会放弃的行动能力。不是他们不想做到,而是他们做不到在破坏旧秩序的时候不以暴力恃强凌弱,做不到在自己成为新的秩序的维护者之后不成为新产生的那个秩序的代言人,悲剧由此注定。但这个悲剧是有意义的。人类的文明需要创伤,需要递进和更替,总得有人出来颠覆前文明,总得有人对现有秩序提出疑问,总得有人用智慧、力量或别的什么权力来提出一种更新文明的理想诉求,并且为了建立新的文明和秩序而付诸行动,这是一轮轮文明递进的前提。英雄的悲剧是注定的,这一悲剧的注定在于英雄的承担是孤独的、不自由的、不被当下文明秩序接纳的,甚至是不自主的,具有同一力量中破坏和建设双向选择后的悖论结局。没有悲剧性结局的英雄一定演变了,异化成新的体制权力,也就不再是英雄了。
杨: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文学也开始发生全面转型,突出表现在传统的“崇高”、“英雄”、“理想”、“价值”等观念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遭受唾弃。您如何看待英雄主义和崇高精神等在当下的命运?您是不是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呼唤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崇高精神的回归?
邓:我不呼唤什么。我的小说中的人物也不担负呼唤的责任。他们只是生活在他们的时代里,被时代压抑和决定,而又不甘心这种压抑和决定;被他们自我内心的冲突压抑和决定,而又不妥协于这种压抑和决定,他们恰好给了我想象中经历一次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虚拟旅程,我个人需要这样的旅程,我在这样的旅途中能够找到快乐,找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一次次心灵的皈依。
对“崇高”、“理想”、“价值”和“英雄”的质疑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一战结束后,被人类和人类文明在战争中的异端表现吓坏了的人们就开始质疑自身传统能量的前认定,甚至质疑科学这个人类桂冠产生的真正动因。哲学、宗教、文学和科学都参与了这场大质疑,这一质疑思潮到二战结束后更甚。普罗运动、工人运动和社区革命主义都以颠覆传统的“崇高理想”为宗旨,这当然也是一种权力再分配的诉求。这种人类对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