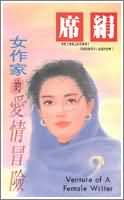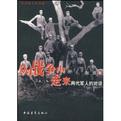对话著名作家-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胡:你有一篇和你的许多作品不同的小说《痛苦比赛》,讲仇饼为了赢得征婚而迎合必须拥有最大的痛苦这样一个征婚条件不断虚构、编撰痛苦的故事。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故事想法?
东:这也是一个有关身体的小说,我想追问一下“痛苦”。今天,我们的许多媒体都在展示别人的“痛”,但是他们是面无表情的展示,是不带感情的展示,仿佛在看一场表演。人们对痛苦已经麻木,所以我就想按按这个穴位,让那些没有痛感、合并痛苦、寻找痛苦的人最后都有了切肤之痛。
胡:你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文学创作了。在二十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你是否觉得有些阶段性的不同呢?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东:肯定有阶段性的不同,开始主要是练笔,写得很少,每年一个短篇加几篇散文,偶尔写诗,这个时期没有目标,没有定法,多是些小感觉;之后,对先锋小说着迷;再之后,直到1995年写了《没有语言的生活》才找到自己,才开始真正地对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二十年来,我的小说里一直坚持“荒诞和幽默”、“夸张和妄想”,从不背叛自己的内心。
胡:我注意到你有几部作品都出现了作家的形象。比如《耳光响亮》中的牛翠柏,《睡觉》中的“东西”,《嫖村》中的秋雨。他们的创作观多少有些不同。牛翠柏是希望借创作以体味在纸上操纵他人命运的快乐。“东西”的创作则被《睡觉》中的“我”认为是游戏和*。秋雨也沉湎于将它看做是意淫自己欲望对象以及想象中复仇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一些创作观只是文本表达的需要吗?它们是否和你在特定时段对自身的创作或者对他人创作的旁观得来的感触有关系?
东:其实我的内心把写作看得比天还高,甚至把这职业排在人生的第一条,否则我不会二十多年对它不变心。是因为高看这一职业,我才去调侃它,从里面找点小快意。调侃的对象强大才能称之为调侃,否则就是瞧不起人。但这种调侃又恰恰说出了真相。
胡:你觉得,在现在文学已经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一个作家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创作理念才是好的呢?
东:文学不可避免地已经边缘化了,作为写作者有时甚至找不到写作的强劲理由。所以,这几年我的小说写得相对少了,大多数时间都在写剧本和读书。小说的需求量在逐年减少,好作品或者我心目中的好作品流行的可能几乎等于不可能,小说如果畅销已经不是小说本身质量能决定的,它必须借助外部因素,比如炒作,或骂人或成为偶像或靠媒体“放卫星”等。文学的形势越严峻,作家就越不能急躁,越要下工夫,当大家都卖假货的时候,真品才会放电。但是作家们各怀心事,写作的目的也不统一,彼此的心态和理念就像北方与南方的差别。就我而言,写作是心灵的产物,是替忙碌的读者去发现和体验。我只对有心者供货,却做不到对大众的普及,所以,我写得慢,写得少,反正写多也没用,能做到写一个算一个那才叫不浪费自己和读者的时间。因为能写剧本挣钱生活,所以我写小说可以写得从容一些,精致一些,出人意料一些……我不为文学的边缘化着急,那是因为我从来也没有中心过,早习惯了。
胡:在民院当驻校作家,要给学生上课吗?讲些什么呢?
东:我在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工作,主要是写作,其次是为学生们上大课,讲些创作和阅读的感想,传递一些新信息,刺激一下学生们的创作神经。
胡:近期内有些什么样的写作计划吗?
东:最近在读书,在构思中短篇小说,在为突破自己皱眉头,在为小说找读者而咬紧牙关。
胡:希望你能有所突破。也希望你的剧本能赚钱。
魏微(1)
魏微简介
原名魏丽丽。
1970年生。江苏人。
2003年,短篇小说《大老郑的女人》获人民文学奖,后获鲁迅文学奖。
2004年,小说《化妆》获中国作家红鹰文学奖。
现为广东文学院一级作家。
魏微自述:我们的生活是一场骇人的现实
魏微
这是凡?高的一句话,我在这里引用一下,简略谈谈我这些年的创作心得。
有一年我在武汉,跟几个朋友聊天,听来这么一件事——据说上了《南方都市报》的社会新闻版——广西一个小山村的村民们,集资买了一辆卡车,往广州贩卖水果蔬菜。因路上关卡林立,所挣无几;又听说沿途关卡只对军车放行,他们情急之下,便把卡车漆成绿色,村民们也穿上军服,戴上军帽,是否配备了枪支弹药不得而知。两年间,他们慢慢认同了自己身份的转变,全村实行军事化管理,村长成了团长。事情的败露起源于一件小事儿,一个村民犯上,村长一怒之下,喝令手下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我确信,这故事一定能迷倒很多人。我把它转述给父母和妹妹听过,他们喜欢;我把它讲给作家朋友们听,他们的反应则是激动。是啊,生活原比小说精彩,村民们也远比作家有想象力;但凡我们聊起文学,总会涉及以下一些概念:现实、想象力、荒诞、时代精神……都是些大而无当的词汇,多年来,我们的文学在这些词汇面前变得小了,被压倒了;而广西的村民们只是灵机一动,已代“文学”走出了一大步。
我确信我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疯狂的,即便我偏居陋室,从每天呆坐着的书房窗口,能看见广州灰色的天,一群鸽子从低空飞过;对面小区的高楼大厦,阳台的晾杆上有各色衣衫在飘飞……即便我身处日常,也能感知我周围有一股奇怪的力量在蠢蠢欲动,就如含苞待放的花,或如破土而出的笋,总有一天,它孕育成的传奇会使我们惊叹不安!
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有传奇发生,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或有一些小的欢乐和伤悲,都可以视为我们时代的注脚。我喜欢“时代”这个词,也喜欢自己身处其中,就像一个观众,或是一个跑龙套演员,单是一旁看着,也自惊心动魄。某种程度上,我正在经历的生活——看到或听到的——确实像一部小说,它里头的悲欢,那一波三折,那出人意料的一转弯,简直超出凡人想象。而我们的小说则更像“生活”,乏味、寡淡,有如日常。
我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一味指责我们的文学缺乏想象力、表现力,或是指责小说家不深入生活,我想并不恰当。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其复杂程度就如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麻。在广西的村民们把运输卡车漆成绿色、在中国就连最普通的农民也开始狂想的时候,我们的文学是否也需静下来沉思,即我们的生活到底怎么啦,我们的文学到底怎么啦。
对话魏微
照生活的原貌写不同的文字
魏天真 魏微
魏天真(以下简称魏):当我读《在明孝陵乘凉》、《一个年龄的性意识》、《一个人的写作》以及后来的《化妆》、《大老郑的女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想到、能够理解你为何要写作又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但恐怕不是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所以,很想请你就这个问题谈谈,也就此验证一下自己的感觉。
魏微(以下简称微):嗯,可能是有话要说吧。对过去二十年,1970到1990年,我是真正生活过的。我在其中摸爬滚打,投了很多感情,可能我就是想对那段生活说话。
魏微(2)
魏:在你的写作中,“记忆”很重要吗,关于童年、青春期的记忆?我觉得,想象在你的小说中也很重要,但想象好像都是附着在记忆上的。因为你的许多作品都给我留了一个特别的印象,就是,有一个成年的“我”——二十*岁或者三十岁的女子在回忆,当然有时也可以是一个年龄相当的男子,比如《拐弯的夏天》就是。回忆中的“我”又记取了两个重要的年龄段——十六七岁和四五岁——的事情。半大女孩又站在这个十六七岁的位置,想着五六岁时做小女孩的光景。这个印象的特别之处就是,我看到一个成年的人在这里看她的少年时代,看到的是少年的她在回望她的童年,这很像两面对照的镜子形成了一个无穷的长廊,很清晰也让人觉得有点隔膜。总之,这些与时间有关的年纪、与年纪有关的时间给我印象很深,在《乡村、穷亲戚和爱情》、《大老郑的女人》、《储小宝》、《姊妹》里头。还有一些小说不会同时出现这些时间,或者说没有这么明显完整,但给人的感觉,还是你在回望过去,那个过去的你也在回望过去。你能说说这个话题吗?
微:这个说法有意思,就是我小说里的两面镜子,一个成年人在回忆她的少年时代,这个少年又在回忆她的童年时代,其实她们都是一个人。你说的是这个吗?我没有刻意这样写,要是刻意,我是写不出来的,这个技术难度挺大的,两面镜子对照,这怎么写啊?我写小说,虽然磨得厉害,但基本上还是自然而然流露的,不去考虑章法、结构那些抽象的东西,就是凭直觉。我其实很看重直觉的,虽然这一路写下来,直觉也慢慢消磨殆尽了,挺可惜的。
我是想把小说写得跟生活一样,就是照着生活的原貌写,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的小说也想是什么样的。你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都有这个意思。“回忆”是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天性使然,我从小就恋旧。我也意识到这一点,就是8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回望7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又开始回望七八十年代。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二十年,有点“浓缩人生精华”的意思。
想象力我是不行的,可能有一点,但绝不是天马行空。这是我的一个弱项。我偶尔有点想象力,也仅限于对一个场景的设置,其实这都算不上是想象力。你一个写小说的人,总归要设置一些场景,虚拟一些人物关系吧。我呢,差不多是那种很写实的作家——我希望自己是这样,当然也没做好。
魏:你说的这些其中也有的是我一直在琢磨的,在重读你的小说的时候,我过去曾纠缠不清的问题又冒出来了。比方说你说自己是照着生活的原貌写,写得跟生活一样,可不久以前不是有“新写实”啊、“零度写作”啊、“原生态”啊,等等,人家也是说照着生活的原貌写的,为什么你和他们的大不一样呢?为什么我会怀疑自己对你的小说有偏私的嫌疑呢?我在说服自己的时候就想,那可能是作者看取生活的方式不一样,同是生活原貌,到了他们的笔下也就随物赋形了。一个人可能沉醉于生活中,可能跟生活亲近,亲近到狎昵的程度,也可能自认看破红尘或者天生优越而睥睨众生,那你呢,我感觉你的态度不是这样子的。你说自己想象力不行,但读者可能感到你的小说有浪漫怀旧的诗意;你以为自己在浓缩人生,大家可能读着觉得闲散缥缈得很呢。那么你对生活是什么态度,我只能凭阅读印象,推测生活的原貌为什么成了你笔下的样子。也许,你对过去的生活就好像对待一个站在面前的人。不论是一个熟人还是一个陌生人,还是一个现在陌生了的故人,他那样来到你跟前,你得认真地看他、听他或者回避他,总之是不得不认真对付。是否可以说你在写作中把生活重历了一遍,这一遍你是小心翼翼地、狐疑地,也是虔敬地甚至是感激地,重新经历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魏微(3)
微:可能是这样。我说照着生活的原貌写,其实生活是没有原貌的,因为每个人眼中的生活都不一样,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视角的问题了。我仔细想了一下,大概我跟新写实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用客观视角,我呢,主观性多一些,就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世界,这个孩子比较敏感,也通人情世故,她就想要把她所看到的世界写出来。
说到对生活的态度,我其实也没什么态度的,我不太懂生活。我把我的经历跟你讲一下。我是1994年开始写作,1997年在《小说界》发表作品,后来就辞职写作,一个人住。这十多年来,我差不多就是一个人待在小房间里,偶尔写点东西,写不下去就读点书,其实跟社会是隔离了。我对社会上的事不是很懂,对生活也不懂。这十多年来,我就没生活过,就是度日。我真正的生活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我写作之前,在七八十年代,我的家乡小城,和家人在一起……就是这段时间。到了90年代中期,我就不在生活里了,也不是刻意的,就是感觉渐趋麻木,对一切都不太起劲,好像被什么东西排斥了,就是站在外围,进不去。当然我也没想进去,属于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那种。其实也挺好的,就是你不再投入感情了,不像前二十年,我是把自己放进去的,那不一样。
魏:我觉得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这是句废话,我已经看到不少人说你的与众不同了。我是指你投射在小说里的一种内省的意识,你笔下的人物不论是哪种性格气质,总有一种明显的剖析自我的倾向,包括最近的《家道》里的这个“我”。我想请教你的是,赋予这些人物以不断反省的特点,这是你写作时无意识的习惯还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微:内省我还是有的,另外我对人心也很感兴趣。这个不单在我的小说里,我生活中也是这样。我看人待事没什么是非观念,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人心,就是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怎样的一种性格,你能做出什么事来……你把人心吃透了,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你也不会觉得奇怪。比如一个老实人,他偶尔也会撒谎的,他瞒天过海,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这是人之常情。不能一写到老实人撒谎,动不动就是脸红。他为什么要脸红?你这等于把人给看扁了,你瞧不起人家!你作为写小说的人,必须要具备这样一种素质,就是尊重你笔下的人物,要跟他平等对话,哪怕他是文盲。人心太深不可测了。
魏:是啊,你也说到尊重。我喜欢你的作品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读到了尊重。对人事万物也包括自己的尊重。
微: